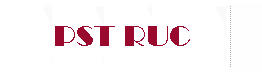2024年10月14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当代科技哲学前沿系列讲座”在腾讯会议线上如期举行。本次讲座题目为《重建生命力:技术时代人的机遇与挑战》,邀请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方向红、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俊就相关主题展开对谈,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王小伟副教授担任主持人。
项飙教授首先尝试为生命力的概念给出现实性的理解:生命力不同于行动力,行动力高涨的忙碌个体可能会感受到自身生命力的消耗;生命力也不同于劳动力,当前的事务性工作不仅需要付出身体上的劳动,更要求人们的注意力、精力和自我劝说的投入。从主观感知出发,我们可以将具有生命力的实践理解为个体自主的使用生命能量去做自视为有意义事情的实践,一种带来满足的实践。就此而言,生命力的英文也就不是一种客体性、外在性的force,而是生成性的power。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如何可能去保全和重构自身的生命力?从马拉松的案例出发,项飙教授认为:对生命力的感知总是在一种有意识的释放过程中获得的,是在世界中构建目标并投入其中,并和相关群体发生共振的实践。我们在展开自我反思的同时,也要小心在过度的反思中封闭自身,应当注意自己的周遭世界,有方向性的将自己投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方向红教授认为,哲学传统经常将生命视为是一种自我生长和演化、并能对世界施加影响的存在。就此而言,生命力可以被理解为是自我生长和演化、并影响周遭世界的能力。从海德格尔和斯蒂格勒对当代技术的理解出发,可以认为技术成为了一种自我发展的有机力量,自身便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形式,也使其有能力攫取和消耗人类的生命力。就此而言,重构生命力的核心并不是寻找某种我们失去的东西,而是构建一个支持人类自我发展和影响世界的体系或环境。从中医对人类身体作为有机系统的理解出发,重构生命力就在于恰当发挥各种器官的作用,理顺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养心养神、回复个体的专注力、洞察力、记忆力、志气等要素。从个人机体内部考虑,这要求我们发展哲学治疗的作用,发挥现象学等资源来重新建构自我的主体感;从系统外部出发,重点就在于洞悉技术的发展方向,对其保持警惕并加以影响,引导技术向与生命契合的方向发展。
王俊教授指出,当代社会生命力流失的问题显然将生命力理解为一种个体和共同体意义上的观念力量,一个有生命力的个体是要求个体自由,努力建构自身意义,并积极参与共同体生活的存在。当代技术倾向于个体生存的原子化、去建制化,造成了个体在城市中的悬浮和无根,互联网所提供的虚拟共同体归属也并没有解决这种悬浮感的问题,也无法促进人们重新走向共同体生活,反而有进一步激化个体间冲撞和对抗的趋势。技术和外部世界的剧烈变化,使我们并未能建立相应的价值系统予以应对,加剧了当代人们的惶恐和脆弱感,技术看似赋予了人们自由,但同时也在用技术化的最优解是我们越来越过上趋同的生活。重构生命力要求我们直面当下,回归附近,这并不意味着对现代社会的逃离,而是要求我们发展一套有解释力的意义系统或者概念系统来应对现存的问题并做出改变,这种改变的可能是多样的,例如一本必须结合生活环境中的实践才可能生效的教科书,例如适量饮酒使我们跳出日常生活的节奏,等等。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四位学者展开了进一步的对谈交流。王小伟老师首先提出了当代技术在生命意义的丢失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的问题:项飙教授认为,技术在当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政治等因素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也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技术绝对不是唯一影响生命力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在很多方面,技术也在构建而非攫取生命力。方向红教授认为,技术思维容易导向割裂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理方式,这种危害是值得警惕的。王俊教授认为,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全新的技术体系时,我们需要的并不只是学习,更是发挥更为系统的理解方式来回应技术,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焦虑。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如何去重构生命力?项飙教授认为艺术、友谊等要素都有利于构建更加投入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贯彻批判意识能够使我们加强对自身生活境况的感知,从而开辟出更多的可能性。方向红教授指出,养心养性的实践可以从自身擅长的领域出发,发扬爱好的作用;重点是主动自觉的去寻找能够让自身投入的生活方式。应当如何理解生命力对自由的追寻和对共同生活的需要?王俊教授回应认为:原子化的自由其实是一种虚假的自由,生命力所寻求的自由总是在具体的环境中,通过与共同体交往实现的,是一种走向和谐的、寻求中道的自由。
最后,对于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人们还能不能够建立自身的附近,过上一种有意义的、自主投入的人生的问题,方向红教授认为:技术确实带来了摧毁附近与生命力的危险,虽然它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了全新的休闲活动和对附近的理解,但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技术对我们的迎合和引导,意识到个人的发展总是或多或少的在挤压与不适的实践中实现的。王俊教授则对技术保持了总体积极的观点:人工智能使我们更容易获得知识、消除了许多重复性的劳动并促进了平等的交流,但其所带来的计算性思维和情绪引导也不容小觑,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构建崭新的意义系统来均衡技术的不利因素,但通过一种生存方式的改变,这种均衡一定是可能的。项飙教授认为:世界的变化不一定能够直接用“变好”或“变坏”的理解予以概括,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反思中对社会发展的方向做出决断,才能区分技术所带来的助力与阻力,并对其做出回应。公共讨论的任务就在于选择一种恰当的回应方式,对于当下的问题,重点可能在于重新弥合越发分散的注意力,使我们重新专注,更加有意识,才能够更有能力选择回应技术的恰当方式,而不是被剥夺回应的能力。(供稿人:金琪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