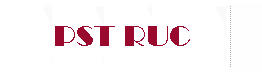2023年12月7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科学逻辑与方法论博士生大讲堂”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226教室如期举行。讲座由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李曈主讲,题目为《人的量化:历史发展与现实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滕菲主持讲座。
讲座一开始,李曈老师首先介绍了量化方法在当下的普遍使用,如医学检测、政府统计和心理测试等。李曈老师提出,将人定量化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科学革命时期。在“哥白尼革命”的影响下,新物理学成为了科学界关注的焦点,自然的量化也为人的量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以笛卡尔、博雷利为代表“医学物理学派”学者将人体类比于精巧的机器,为测量人体提供了合法性。大量对人体的数学测量、定量实验也由此展开。即便是反对机械论的医学化学学派也支持定量实验,量化方法成为了避免主观偏见、保证研究“科学性”的基本思路。
李曈老师进一步指出,很快,对人体的测量扩展到对人群的整体性测量,并由此产生出“人口”的概念。量化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医学中,也延伸至政治领域中。约翰·格兰特对伦敦死亡记录的分析开辟了人口统计学的先河,实现了从量化人体到量化人口的跨越。威廉·配第提出了政治算术思想,认为对统治地区人口数据的收集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随后,人口学、卫生统计学等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量化人口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法。福柯以“生命政治”理论解释了这一历史发展,指出在人口概念产生之后,出现了从死亡政治向生命政治、从规训到调节、从政治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型。不过,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福柯的理论。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就提出,生命政治和死亡政治从来都是一体两面,否则无以解释20世纪的纳粹大屠杀。
接续这个话题,李曈老师指出阿甘本的判断并非毫无依据,这一点同样可以从人的量化史中找到线索。18-19世纪,人口学逐渐发展壮大,产生了后世统称为“公共卫生”的研究及治理领域。而19世纪末的进化论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精神疾病、犯罪等都被贴上“退化”的标签,人体测量开始应用于犯罪管理、身份鉴定,以及强调种族差异方面。弗朗西斯·高尔顿、卡尔·皮尔森等现代统计学的奠基者同样也是优生学的倡导者,人体与人口测量被大量运用于论证种族优劣。精密的统计模型为种族主义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并在20世纪的欧美各国演化为对他者的迫害与屠杀。
最后,李曈老师带领同学们对人的量化现象进行了反思。定量方法被视作科学、客观、中立的象征,但实际上从调查对象的选取、抽样方案的制定、统计模型的选择,到最后对统计结果的解释,各个环节都是价值负载的。这也是为何在优生学的历史中,科学方法非但没有避免科学家群体的主观偏见,反而成为了种族主义最有力的推动者。量化方法不是万能的,也不能完全规避研究者的主观性,在使用时应当谨慎。在当下,人的量化依然是科学研究与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为此,鉴别量化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建立纠偏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在评议和交流环节,有同学提出将复杂性科学的方法纳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是否能够提供一个不同于量化方法的解释。李曈老师回答道,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时常会启发社会科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不过在看此类资料时需要区分: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直接引用,还是类比性的引用。一些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本身是高度量化的,但在应用于社会领域时进行了改造。另一位同学提问为什么认为以基因还原论为主导的优生学将会被发育学为主导的环境主义所取代。李曈老师对此回应:基因还原论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基因结构的不可变更性,而忽略了基因表达为性状的过程复杂性。优生学本身就存在将所有人类属性都归为遗传特质、将相关性混同于因果性的谬误,其所依据的经典遗传学也遭受着诸多挑战。特别是2003年之后,功能基因组学取代结构基因组学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表观遗传学更是动摇了DNA作为遗传物质的唯一性,甚至“基因”概念本身也亟待重新定义。遗传性状必定是在环境之中得以表达,因此关注环境作用的发育学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此外,其他同学也与李曈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本场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供稿:董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