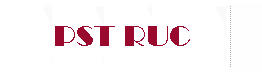国际哲学研究院巴黎会议于2010年9月15-18日隆重举行。法国哲学家组成了组织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并得到了法兰西研究院(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等科学院的联合机构)、法兰西研究院Simone et Cino del Duca 基金会、法国外交和欧盟事务部、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部、法国国民教育部、法兰西学院、法国大学研究院、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以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支持。会议主题是哲学与世界状况(Philosophy and the State of the World)。会议开幕式由法国的著名生物医学哲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Anne Fagot-Largeault主持,闭幕式由西班牙的Tomas Caivo主持。本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筹)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研究员出席大会并做了发言。
会议分研究院的工作会议和学术会议两部分。在学术会议上,学者所做的学术报告依次是:“分配公正和水资源的分享”(摩洛哥的Ali Benmakhiouf)、“人口学与公众健康”(中国的邱仁宗)、“人类是我们星球的管理者”(厄瓜多尔的Francisco Bravo)、“文化多样性与地球世界的统一性”(俄国的Vladislav Lektorsky)、“技术对接、伦理革新与家园伦理”(加拿大的Peter McCormick)、“科学幻想预测未来吗?”(比利时的Gilbert Hottois)、“进行世界新秩序的教育”(丹麦的Peter Kemp)、“伦理学与工业管理”(德国的Hans Lenk)、“昨天的奴隶制、今天的科学家外流:可比拟的结果吗?”(塞内加尔的Souleymane Bachir Diague)、“价值的重要意义:对Daya Krishna论自由的思考”(印度的Bhuvan Chandel)。主持学术会议的先后有:Enrich Berri (意大利)、Ioanna Kucuradi(土耳其)、Jaakko Hintikka(芬兰/美国)、Paul Gochet(比利时), Herra Nagel-Docekal (奥地利)。还有一次圆桌会议讨论:全球well-being(美好生活)的标准(超越DNP)以及其他建设性建议。会议由Athanasia Glycofrydi-Leontsini(希腊)和Evando Agazzi(意大利/墨西哥)支持。发言的有:Emmanuel Picavet (法国)、Caroline Guibet Lafaye(法国)、Guttorm Floistad(挪威)、Juliana Gonzalez Valenzuela(墨西哥)、Bernard Reber(法国)、Pall Skulason(冰岛)、Patrick Suppes(美国)、Daniel Kolak(克鲁地亚/美国)、Jan Wolenski(波兰)、Andrzej Grzegorczyk(波兰)、Nam-In Lee(韩国)。
会议的工作语言是法语和英语,绝大多数与会哲学家都能熟练运用这两种语言,但发言者主要用法语。以下仅根据参会者记忆整理如下:
Ali Benmakhlouf在讨论水资源公正分配的发言中提出的问题是:对于全世界范围内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应如何应对?如何保护生态系统?水资源应如何随城市化程度而增加?
Francisco Bravo在关于人类是我们地球管理者的发言中指出,在面对人类与我们地球关系问题时,2008年厄瓜多尔全民公决通过的宪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承认“大自然(Nature)的权利”。这一概念引起一些问题,但在解决人类与其家园的关系之中,这一概念是有其贡献的。
Bhuvan Chandel在讨论Krishna论自由中指出,Krishna认为在人类追求自由中,既要追求知识,也要追求价值,并处理两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不仅是所有好的和美的东西的来源,也是建构人类关系的网。Krishna认为理解和诠释自由的基本问题有:自由是人的本质存在和意识的结构中固有的吗?如果人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否自然本身赋予人这种罕见的属性?人是否超越他本身的时空存在,提升到超验自由的高度?然而人类行动不能不参照价值来界定。人类能力有限,人类的可能性也有限度。但超验自由的理想可超越这种限度,融入超验领域。在经验层次,人和自由具有多样性,种种经验自由可发生冲突。仅当只有一个自由中心时,才可能有绝对自由。但这在本体论上是不可能的。
Guttorm Floistad在其“自由和民主”的发言中指出,福利社会给人们带来物品、快乐,甚至幸福。市场经济要求的是能使企业和管理成功的知识。但是我们第一位的需要是进入人际关系、归属某个人的知识。一个新生儿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母子关系。成长是进入复杂的关系。我们个人的身份在于一种人际关系的结构。强调市场经济要求的那种知识,就会忽略我们的人际关系,结果容易患有精神障碍和孤独症,在美国和欧洲被称为新的疾病。这是因为自由丧失了与他人互助团结的基础。民主要求自由和互助团结兼有。唯一的办法是培养集体感,强调历史、文学和美学的通识教育,亚当·斯密的四重自由是否仍然有效?只关心个体那就无效,必须考虑集体。不能只考虑手段,必须考虑价值自身。美国一些大学要求学生进入专业知识学习前必须先学1-2年的文科(Liberal Arts),我们知道在商业管理教育和企业活动、管理中,以及一般教育中不进行文科的培养,而通识教育可培养人际关系和员工之间的合作。非洲人说人有两类需要:小的需要和大的需要。小的需要是需要吃、住、钱,大的需要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非洲人在他们的音乐、舞蹈和仪式中找到答案,这是他们的通识教育。我们也需要加强我们的通识教育。
Juliana Gonzalez在他关于阿马蒂尔·森的贡献的发言中指出,阿马蒂尔·森通过对经济的深刻批评,将哲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使人们有希望摆脱目前全球状态中的剥夺、苦难、压迫、贫困和威胁。以经济为中心的福利社会的统治趋势却是突出了大多数人的贫困化以及地球自然资源的贫困化。由于将人类自身存在归结为个人利益和一种不可靠的福利概念,人类自身存在也贫困化了。可以说世界目前状态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经济中心主义或经治主义(econo-cracy)。到处都是经济利益、市场和利润,代替了人的任何其他的非经济利益,或者也把它们归结为效用。似乎唯有经济才是历史的唯一力量,生活的唯一方向,除了经济无限增长,没有其他可能的选择。这种趋势与现代技术性科学及其力量和雄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将理性与工具性等同起来,森一针见血地批评这种工具理性是“理性的蠢人”。结果,这种工具主义的概念和经济发展的现实产生了一种只讲究效率和竞争的市场文化,渗透到个人和社会生活、人类创造和制度、科学、政治、艺术、道德和习俗等所有领域,使人类存在贫困化。这种单维度的文明受两种力量统治:一方面是贫困,另一方面是奢侈和贪婪。这两种力量与一个系统连接,这个系统创造了一种似乎不可放弃的生活方式。
森所建议的改革是改革现代经济的核心。他通过对亚当·斯密的重新诠释,否定了将经济与自私等同,福利(welfare)就是人的经济安康(economic well-being),人的发展就是可用GDP和其他经济指标测量的经济发展等广为流行的观念,即用来界定“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特征的所有东西。森同意亚当·斯密,道德情感也是推动经济的因素,这就有可能克服经济与伦理的分离,反之承认这两者之间必定有内在的协调关系。森说:“现代经济的本性因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分裂而被大大扭曲了。”(1987)因此,经济活动的动机不能被归结为个人的利益,而是应该包括其他动机,有些是利他主义的,如慷慨、忠诚和义务等。这些利益并不一定与产生财富的个人动机相对立。森的批评并没有缩小福利或市场经济、生产物质财富的重要性,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要恢复人类利益的全部范围,扩展到积聚外在物品之外。对于森来说,人类发展的测度和福利的标准不是财富,而是自由的发展。自由发展不是指消极的自由,即不强迫、不干预,而是指使人成为他们自己愿望、他们自己的决定和他们自己的行动的真正行动者的能力。对这种作为行动者的自由的伦理品质必须加以测量,以便评估发展和真正的“福利”。而人的能力并不属于“拥有”(having)的领域内,而是属于“存在”(being)的领域。“贫困必须被认为是剥夺基本能力,而不仅是缺乏收入。”(森)这样,“经济人”的自我中心的壁垒就被消除,经济学的视野将被拓宽,经济学将容纳过去被忽视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有:社会关系、健康、教育、科学、文化以及所有反对贫困和不公正的努力。这种经过改革的经济学将超越仅仅获得财富和权利的自我中心的目标。这种经济具有“理性的使命”,消除贫困以及所有妨碍人类发展的东西。“消除贫困、无知、疾病和机会不平等是我工作的基础。”(森)将重点从财富转移到自由和公正,扩展了和加深了人类活动的动力,这样其目的是全面的、整合的、多维度的发展,包括了范围广泛的人类潜能和能力。森认为作为人类发展关键的自由还有其“构成”性质,具有本体论的和本体-人类学的意义。发展必定被认为是一种本体论范畴,界定“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性质。与传统的形而上学本质相对照,发展是“在过程中(在时空转化中)的存在”(being in process)的构成方面。因此,发展并不是本质的展开,人的历史和社会的实在是一种自由的获得,由于自由是人类的能力(潜能),发展构成了自由的具体实现。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最近文件体现了森的经济哲学理念,尤其是在有关千年发展目标的文件中。人类的希望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人具有物质的和文化的本性。但这不是说,自由和公正的实现不需要艰苦的努力。为此,必须有民主的公共的讨论,公众的争论和理性,森称之为“公共理性”和“社会决策”。
Caroline Guibet Lafaye和Emmauel Picavet的发言也谈到了阿马蒂尔·森关于能力和社会政策伦理学的贡献。他们指出,森的能力有三个成份:选择的能力;个人的繁荣和成就;由自己实现某些事情或行动的能力。森反对仅仅根据主观的美好生活(well-being)或满足感来评价人的社会状态,而应该通过种种功能活动(functionings),那是指美好生活(well-being)的种种实实在在的层面以及能力集(capability set),如人们拥有按照他们的选择达到各种成就和经验的机会。基本的自由具有超文化的价值,因为(1)它们具有内在的重要性;(2)它们在创造经济保障的条件中具有激励作用;(3)它们在阐明价值和轻重缓急的过程中有建设性含义。森参与拟定的“人类发展指标”包括下列因素:健康;教育水平;生活标准。这三个因素具有下列性质:对每个人都具有内在重要性;是生活中种种成就的前提;容易接受客观测量。人类发展指标是森的能力的体现,但也受到怀疑。Thomas Pogge指出,这种指标具有“起平均作用的”特征,可能会有利于对健康差的人持偏见的政策,而看不到能力进路的个体论基础。还有人批评能力进路具有模糊性。
Daniel Kolak在讨论美好生活(well-being)时指出,几千年来人们在我们外部建立统一:种族的统一,社会的统一,国家的统一,宗教的统一,经济的统一,政治的统一等。人们建立的外部统一将秩序强加于来自外部的人。我们很少转向我们自己,也许因为我们向内看会使我们彼此分开。我们应该在主体自身找到共同基础,这种基础不是外部强加的统一,而是内在的统一,从而使外部强加成为多余。他提出一种开放个体论(open individualism),这并没有消除分割我们的壁垒,但它向我们指明如何在我们内部建立更好的生活。
V.A.Lectorsky在讨论文化多样性和世界统一性的发言中指出,在人类全部历史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往往是试图建立不同文化的广泛统一。这往往压制一些文化,支持一些文化。但一种文化的存在必须与其他文化互动。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全球化。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扩展到全世界,世界经济组织、跨国经济公司的重要作用,世界政治体制的存在,以及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密切相关。所以全球化不仅在世界不同地区建立了新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全球文化,成为大众文化。人们原以为新的全球文化可以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补充,实际上不是。人的存在必有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但自我认同依赖于某种群体和文化的认同,单是全球认同是不够的。再者参与全球文化的程度各异,例如一个跨国公司官员与一个非洲农民参与全球文化就不同。全球化并未消灭文化多样性,实际上增加了文化多样性。因此多元文化概念很流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一是容忍,容忍可以是对存在的不同价值、世界观和习俗漠不关心,也可以是尊重其他文化,因为我们对它们不理解也没有互动。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容忍是保留现存的文化和群体的认同,不允许改变和发展它们。二是对话,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在此过程中文化有可能变化。但每个文化中有些是不容许对话的,如宗教信条。对话是可能的,并且可以是富有成果的。如从不同的价值视角来理解我们共同面临的实际问题,并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比较不同的视角有可能的,并且是有用的。文化之间的对话可能有三种结果:不同文化的综合;改变文化认同;拒绝继续对话。
Hans Lank在有关伦理学与企业管理的发言中谈到了法人社团(corporate)的责任。传统的个人责任及其不同形式不能处理现代法人社团及其互动中所有国际的、跨文化的和多地区的问题。可以将法人社团看作为行动和行动者的交错系统,指向一组特定的共同目标,其特征是具有多种角色和行动结构的内在等级系统,还包含着具有体制化的和受控性质的深层结构、职位、计划、问题和视角。法人社团可以是经济的、非经济的,即以国家或政府为基础的机构,或多或少严格组织起来的模式、行动以及目标取向。对法人社团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如社会和法律契约模型、生物或有机体模型,或广义地“人”的模型。后者将法人社团看作行动系统,它们是目标取向的、社会化的、体制化的以及受控的。后一诠释适合于提出责任和责任区分、与法人社团决策结构有关的内部和外部的责任问题。而我们过去则往往谈论个体的理性与机体的非理性(如囚徒悖论)。
Peter McCormick在发言中谈到IIP前院长今道友信在40年内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着重于两个问题。一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全球化是否在实质上改变了人类的环境,二是今天我们已经实质上改变的世界状况是否要求“为我们的新时代”建立“新伦理学”。他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他对这种新伦理学起名为“家园伦理学”(eco-ethics)。但对这种基本诉求是否正确需要进行系统的和批判性的评价。目前已成立了今道友信家园伦理学研究所,由IIP丹麦委员和2009年世界哲学大学主席Peter Kenp任常务副所长。
Pall Skulason用冰岛的经济危机说明,我们过去忽视的我们社会三个基本方面的区分和相互依赖,即政治的、经济的和伦理的(或精神的)方面。有时政治领域统治其他,给人类生活造成巨大伤害,有时经济权力操纵人类生活的政治和精神方面,使之失去一切意义。现在经济逻辑压倒了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政治、伦理和精神价值。最近30年经济价值或经济主义统治了西方思想,这种意识形态可以用4句话概括:一切人类关系,归根结底是经济关系;挣钱是一生最重要的事情;私有化总是要做的正确的事情;竞争总是好的。冰岛政府说,我们面临的是金融危机,银行借的钱是国家年收入的10-20倍,这些钱用来购买国内国外的公司,盖些不需要的建筑物。理应监督经济领域的政治和行政机构对此视而不见,而学术研究机构也不加批评。对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理解十分狭隘,只是集中于物质价值和政治权力,忽视了精神、伦理和教育方面。因此必须建立教育国家(education-state),强调道德价值,培养良好的判断(good judgment)。
Jan Wolenski在他的关于法律的逻辑和社会功能的发言中指出,法律实在论者Jerome Frank对逻辑不很看重,认为法官不是演绎逻辑机器,不是根据逻辑推演计算出法律决定。律师的论证是非形式的,受若干社会因素(如政治观点、宗教、道德、社会地位等)的影响。虽然形式主义者坚持认为,法律推理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合乎逻辑的,但反形式主义者认为,生活与法律必须互相适应。Wolenski认为,虽然司法决定的社会情境是极为重要的,但不应忽视法律的逻辑性质。法律的逻辑往往被理解为支配法律诠释、组织法律条文结构或帮助法律辩护的规则,但这类逻辑不可能完全归结为形式演绎逻辑。我们应该将法律逻辑理解为建立和诠释法律规则的法律思维的艺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是增加法律规则。这引起法律之间的不一致和空白。这对法治和人的自由造成危险。对法律的形式性质要有清醒的意识以及要遵守法律,这对社会的健康十分重要。在现代法律的头脑中不应该将逻辑一笔抹煞。
会上有两位学者的发言讨论人口问题。Patrick Suppes的发言题为:“少点人口是可持续性最可行的进路”。他指出,今后环境的可持续性只能通过集中于主要问题,即污染者,人自身才能得到解决。我们还没有以合理和公平的方式解决减少人口的问题。他说他不反对“所有人有更多的休闲,有更多的财富”,但这有个合理的限制。然而现在还不是“全球人口多少最优”的问题,现在迫切的问题是,选择可行的进路来稳定和减少世界人口规模。他主张,每个现在活着或尚未出生的人都有生育权。但这种生育权只给一个人有一个孩子。这种生育权也可用来领养一个孩子。这无需到生育市场去购买这一个生育权,因为这是你的权利。另一方面,你也有权在市场上出卖你的生育权。生育权的规则是,一对夫妇有权繁殖自己:男人的两个精子在不同时候使女人的两个卵受精,这也适用于孪生子。但如果生三、四、五胞胎,那就必须到自由市场去购买追加的生育权。这种规则要比中国的办法更宽松。但他没有详细介绍如何建立和管理这种生育市场。这样做的一个问题是,新的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但达到人口平衡时,这是一个可持续的人口,不会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再则,现在的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人大为减少,劳动力主要转移到服务行业,那可以大量使用机器人或自动化装置来解决。另一个问题是人口的年龄分布问题。年轻人比例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到达平衡的人口,寿命的延长不是一个严重问题。
邱仁宗研究员的发言“人口学与公众健康”是组织委员会分派的作业,但他在发言时用的题目是“人口学与公众健康和well-being:以中国为例”。他的发言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人口伦理学及其对一个国家所选择的人口政策的可能含义,以及对目前人口伦理学的公理进路和效用论基础的评论;第二部分集中于中国的人口政策,从历史到现在、从鼓励生育到限制生育的演变;第三部分讨论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评价,分析了这种政策对人口增减的影响,以及人口减少对社会经济发展、公众健康和美好生活的影响;第四部分讨论这种政策面临的挑战以及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争论,最后讨论了中国的经验对人口伦理学的含义。
最近30年来,国际哲学界对人口伦理学的兴趣持续不衰。人口伦理学集中于寻找用来判断人口应该多少合适的原则或标准。这种兴趣起源于Derek Parfit在他的《理性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一书中对非同一性问题讨论导致的一个违反道德直觉的“讨厌的结论”(repugnant conclusion),即人口众多而生活质量低的人群反而比人口较少而生活质量高的人群更可取。这个结论蕴含着一种总体效用论(total utilitarianism),即不管其中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如何,人口多的总效用值要大于人口少的总效用值。人口伦理学此后的发展就是围绕如何解决这个“讨厌的结论”开展的。有人提出用平均效用论(average utilitarianism)代替,即应该计算平均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是否高来决定合适的人口规模。但平均效用论虽然避免了“讨厌的结论”,但陷入了另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结论:只有一个人的人群,但其生活质量最高,比任何多的人群要好。为了既避免讨厌的结论,又避免平均效用论的不满意结论,人们提出了临界水平效用论、可变价值效用论等理论,但没有一个理论能够满意地既避免讨厌的结论,又避免其他可能的违反道德直觉的不满意结论。于是,人们觉得也许:(1)对Parfit的“讨厌的结论”不可能有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2)我们的道德直觉误导了我们;(3)Parfit的“讨厌的结论”也许不可避免,也许也不那么“讨厌”;(4)也许效用论不能用来解决类似人口问题那样复杂的问题。邱仁宗指出,用公理方法解决那么复杂的、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的人口问题像是“削足适履”;反之应该在人口政策中考虑所有利益攸关者的价值,并根据优先次序进行权衡;效用是重要考虑之一,但在人口问题上有不同性质的效用,而且效用之外的因素也不能忽视。但人口政策中要考虑总体效用、平均效用、临界水平效用、可变价值效用等,是很重要的。
在第二、三部分,邱仁宗首先指出,三十年来成功地减缓人口增长是世界人口学史上最为伟大的事件之一。中国历史上一直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建国初期也是如此。但自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后,中国政府开始转变态度,主张节育和限制人口增长,尽管有所争论,但需要减少人口才能持续的进行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善公众的健康,提高生活质量,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人口政策曾从二孩政策,到 “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最后定型为现行的政策则是比较多样化的,实际上最多的地区还是一个半孩子,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的地区均属少数,而三个孩子和不加限制是少数民族地区,极为少数。但30年来,种种数据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包括人均GDP的增长、贫困人数的减少、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预期寿命的延长、文盲和半文盲的较少、私人轿车拥有量的增加、私人住宅的增加、旅游人数的增加以及私人投资数的增加是平行的。但值得探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是否必然导致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善公众的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如果没有配套的政策措施会如何);生育率的下降是否是人口政策所导致,没有这样的政策是否也能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以及限制性的生育政策是否或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得到伦理学的辩护等问题。
在第四部分,邱仁宗指出了现行生育政策引起的种种挑战,如婴儿死亡率性别比的不平衡,出生性别比的不平衡,人口老化及劳动力的可能短缺等问题。对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否需要改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在学术界内部也有诸多争论。最后,他指出,人口伦理学必须考虑人类经验,即便不说以证据为基础,很难用一条原则或一个标准来评价人口的大小多寡,更不要说评价人口政策了。总体效用、平均效用、临界水平效用、可变价值效用都必须加以考虑,但仅考虑不同人口政策的效用也是不够的,也要考虑政策本身和政策实施的过程,如是否违反生育权,程序是否公开、公平、公正,知情选择是否坚持,公众是否参与等。
邱仁宗研究员的发言安排在第二个,说明组委会对其发言的重视,发言后进行了热烈讨论,许多与会者,包括组委会、学术委员会一些成员都对这一发言表示赞赏,会议组织者Anne Fagot-Largeault前来表示为邱仁宗研究员感到自豪,这表明组织这一发言是合适的。
大会还讨论了吸收新成员的问题,这次中国有两位候选人,其中一位候选人杜维明获得通过。IIP一般认为在美的中国哲学家如果在美国工作,不能作为中国的委员当选,但因杜维明即将回北京大学教学,因而同意他作为中国委员当选。另一位候选人则有分歧意见,待明年再决定。
国际哲学研究院的年会讨论世界实际问题的情况是不多的,这次的讨论具有象征意义。哲学毕竟不能长期关在象牙塔内,哲学家要走进生活,要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迫切实际问题分忧。
国际哲学研究院(IIP,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是国际哲学界最高的学术组织,成立于1937年。1938年举行第一次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止活动。战后在1947、1949年举行过两次大会。自1955年来每年举行一次大会,每次大会有一个主题,并出版学术著作。
成为国际哲学研究院委员(Member)的是世界顶级哲学家,如德国的Apel, Gadamar, Habermas等;阿根廷的Bunge;澳大利亚的Passmore;奥地利的Haller;加拿大的Kilbansky;丹麦的Kemp;美国的Marcus, Gibbard, Putnam, Searle;芬兰的Hilpinen, Hintikka, von Wright;法国的Bachlard, Ricoeur,Fago-Laugeault;英国的Pears, Strawson, Wiggis;意大利的Agazzi;波兰的Kolakowski;俄罗斯的Lectovsky;塞尔维亚的Markovic;瑞典的Prawitz等。现任院长是西班牙的Tomas Calvo。2001年8月27日全体大会上被选为新委员的有:Pascal Engel (法国), Michael Friedman (英国), Thomas Nagel (美国), Charles Parsons (美国), 邱仁宗 (中国), Bertrand Saint-Sernin (法国), Johan van Bentham (荷兰), Dan Zahavi (丹麦)。
(李伦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