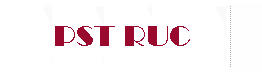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是国际生命伦理学协会的双年度年会。国际生命伦理学协会成立于1993年,2006年第8届大会在北京举行,今年第10届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政府认定,21世纪将是生物医学的世纪,因此对此进行了大量投资,在新加坡大学建立了新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加强了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的建设,聘请了英国的Alastair Campbell教授、菲律宾的Leo de Castro教授、澳大利亚的Paul McNeill教授等加盟,主办第10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2010年7月28-31日)和第11届亚洲生命伦理学会议(2010年8月1-2日)。
本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约有400余人参加,代表来自世界各大洲和不同文化。大会的主题是医疗卫生与全球公正。分主题有:生命伦理学的全球和地区观点,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公正、医疗卫生的可及和医疗卫生改革,全球卫生管治伦理学,国际健康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临床伦理学:本土的关注和国际的视角,全球情境中的公共卫生伦理学,与国际发展、援助和重建有关的伦理问题,生命伦理学、健康与环境,伦理学、增强与人类的未来,利用干细胞、胚胎和新医疗技术进行研究中提出的伦理问题,传染病控制和全球性流行的威胁,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对政策和伦理学的本土、地区和全球的争论,生物医学的全球化和商业化,与脆弱人群和少数民族有关的伦理问题,健康中的不平等和歧视,食品和安全,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伦理学。下面仅仅介绍我们参与的一些会议交流的内容,难免挂一漏万。
在7月28日的开幕式上,澳大利亚前最高法院法官Michael Kirby做了有关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宣言对全球健康中的公正是否有帮助的发言,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Rosemarie Tong对全球经济中老年人照顾的工作进行了女性主义的分析,联合国红色高棉审判助理Silvia Cartwirght法官报告了战争罪犯审判对受害者福利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制度研究中心的杨永强报告了健康中的不平等以及卫生制度对公正的挑战。
题为“将脑与机器绑在一起:脑-机界面的伦理问题”的专题讨论会颇为令人感兴趣。可植入脑的装置使我们对人脑更详细的理解,并有助于开发新的治疗方法。临床上已经确定脑植入物是为了治疗帕金森病晚期病人严重的运动症状。动物实验结果预示可给瘫痪病人提供新的治疗选项。在有关责任、身份和残障问题上伦理评价尤为重要。将这些装置在功能上整合入脑的活动导致责任归属的伦理困难。如果对记录的信号做出错误诠释,那么基于这种错误诠释的假体的行动由谁负责呢?德国透平根大学的Jens Clausen、加拿大达鲁斯大学的Francoise Baylis、加拿大卡尔盖里大学的Gregor Wolbring、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的Bert Gordjin分别就“脑-机界面的伦理问题”、“关系身份对脑-机界面伦理评价的影响”、“作为治疗残障人的辅助装置:这是路的尽头吗?”和“用于增强目的的脑-计算机界面”问题做了发言、讨论。
公共卫生伦理问题是本次大会一个重点。在7月29日“公共卫生中的挑战”大会上,英国哈特福德郡大学的Robyn Martin报告了“公共卫生与全球场景”,比较了东西方公共卫生伦理学和政策(遗憾的是她对东方的理念理解很差);美国纽约耶希瓦大学Ruth Macklin报告了“公共卫生中的挑战:妇女健康不平等”,她在报告最后问道:谁负责采取措施减轻妇女所受伤害,尊重、保护和落实受害妇女的人权?新加坡大学的Paul Tambyah报告了“应对突发传染病中的伦理问题:SARS和H1N1大流行的教训”。在“公共卫生的伦理挑战”的分组会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Belinda Bennett报告了“对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全球准备和应对:法律和伦理的作用”,印度尼西亚大学Ade Sugiharto报告了“开发新的A H1N1流感疫苗以应对2009流感大流行的伦理考虑”;印度理工大学的Rhyddhi Chakrborty报告了“对若干南亚国家应对大流行计划的比较生命伦理学分析”;巴基斯坦人民医学院医院的Inayat Ullah Memon报告了“发展中国家的结核病和伦理问题”;埃塞俄比亚Geremew Tsegaye报告了“男性环割术与艾滋病预防:伦理学分析”;印度特里莎女子大学Hilda Chinnappan报告了“在生活方式疾病中的性别差异”;荷兰乌德勒支大学Andre Krom报告了“传染病控制:如何判定哪些公共卫生干预可得到伦理学辩护?”,他指出三要素:干预的有效性、相称性、干预的方式侵犯个人最小;来自挪威卑尔根大学的中国博士生王春水报告了“公正和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在中国大陆”,她指出,医疗卫生改革需要价值判断,公正是医疗卫生政策的基本性质,它包括两个方面:实质性公正,涉及医疗卫生服务分配标准;程序公正,正当的决策过程,而在医疗卫生服务中公平比效率更重要,决策过程应该具有正当性、透明性、公共参与、公开性。
在“食品、安全和环境伦理学”分组会上,讨论了促进公共和全球健康的营养基因组学及其伦理挑战,食品安全和气候变化:伦理含义和价值冲突,报告人有: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Beatrice Godard和Raphaelle Stenne,以及国立新加坡大学的Lisbeth Nielson。
比尔盖茨基金会资助大会讨论新生儿筛查伦理问题的专题讨论会。在许多国家从所有新生儿采血,测试某些先天疾病,例如PKU(苯丙酮尿症)。这类筛查计划争论较少,即使有些地方是强制性的。现在技术的进步使得有可能用这些血滴测试大量遗传和代谢疾病,许多国家扩展了筛查计划。这就引起了一系列伦理问题,如筛查的目的和标准、假阳性越来越多、使用血样做其他研究以及强制计划的辩护和知情同意的可能或不可能。这次专题讨论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对目前和未来新生儿筛查计划的生命伦理学反思。发言者有: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Marcel Verweij(从伦理学视角看新生儿筛查计划的扩展),荷兰莱顿大学Carolien Boelen(新生儿筛查:是祸是福?),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Niels Nilsingh(新生儿筛查应该成为强制的公共卫生干预吗?)。
在“生命伦理学与动物地位”分组会上,发言题目有:异种移植与公共参与(芬兰图尔库大学Helena Siipi)、从佛教观点看圣猪事件的生命伦理学含义(台湾玄奘大学释昭慧)、缺陷模型及其批评:以遗传工程机体为例(芬兰图尔库大学Marko Ahteensou)、黑猩猩与嵌合体:道德地位增强、物种主义和“人类”尊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伦理学和创新研究所)。
在“遗传学和基因组学新发展:伦理学挑战”的专题讨论会上,英国卡迪夫大学的Ruth Chadwick讨论了个人基因组问题,认为需要考虑具有伦理含义的深层概念问题,例如“个人”、对遗传决定论的可能再诠释,以及如何实现公平问题。英国剑桥大学Martin Bobrow报告了“基因组数据的发表:张力与平衡”,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Bartha Knoppers报告了“数据分享:走向国际行动准则?”。
在“传染病与全球扩散:生命伦理学问题”专题讨论会上,报告的题目有:“传染病的全球挑战:富裕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应做些什么?”(美国犹他大学Leslie Francis)、“传染病和制度疏忽:发展中国家的卫生制度约束”(印度理工学院Chhandra Chakraboti)、传染病与社会决定因素(印度理工学院Sangeeta Das Bhattacharya)、“传染病的全球挑战:贫穷国家对富裕中国家应做些什么?”(美国犹他大学Peggy Battin),Battin指出,发展中国家应做8件事:如实告知疾病发生信息;减少引起疾病的习俗;维持合适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对与疾病控制最为有关的方面进行研究;修改妨碍疾病控制的法律和政策;注意促使疾病流行的社会、工作和居住模式(贫民窟、人口买卖和卖淫);注意就业条件防止医护人员外流;专业人员熟悉现代医学和科学。
在7月30日“人类器官和组织:全球市场?”的大会上,巴基斯坦的生物医学伦理学和文化研究中心的Farhat Moazam报告的题目是“超越礼物:对巴基斯坦肾脏捐赠的反思”,她指出,巴基斯坦人捐赠肾脏时很少提到“礼物”或“权利”,而是看作对亲人的宗教义务,这会让上帝高兴,此后上帝会报答他;在大家庭中捐不捐赠的决定基于对家庭福利的务实考虑。美国海斯汀中心主席Thomas Murray在他题为“器官捐赠者、器官购买者和生命的礼物”的发言中指出,有人建议用金钱刺激,依靠市场来增加可移植的器官供应,对依靠市场解决器官短缺办法的公平评估必须考虑这种市场在实际上如何起作用,必须考虑器官捐赠的意义,最后考虑缩小供求差距的其他办法,包括增加器官供应和减少对器官的需求。英国杜拉姆大学的Marilyn Strathen在其“思考不可思考的:全国调查”的发言中讨论了建立器官市场以及器官捐赠中的利他主义和商业化问题。
在“全球化世界的生命伦理学教育”专题讨论会上,邱仁宗在题为“生命伦理学中国际准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张力”的发言中指出,有关生命伦理学的国际准则已经吸收在我国的条例、规章、办法之中,体现在这些国际准则之中的共同价值已经在中国大陆得到了承认。对这些国际伦理准则和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的普遍可适用性的挑战主要根据对本土文化一种诠释(例如认为与西方重视个人不同,东方重视集体),根据这种诠释国际准则似乎与本土文化是不相容的。而实际上例如儒家的概念“仁”与“不伤害”、“有益”、“尊重”、“公正”是完全相容的。“不相容“命题也不符合中国大陆的现实。接着,他批判了种种反对普世价值的错误论点,指出可以有三种进路处理国际伦理准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张力:即传统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以及协调(reconciliation)的进路。这种协调进路可形成若干生命伦理学的进路或范式,即使在一个国家之内。在这个会上发言的还有:新西兰德尼登大学的聂精葆(“在中国和西方医学中讲真话的实情”)、美国霍华德大学的尼日利亚哲学家Segun Gbadegain(“生命伦理学与约鲁巴价值:走向跨文化的生命伦理学”)、美国纽约耶希瓦大学的Ruth Macklin(“调和伦理学帝国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
7月31日大会的主题是“生命伦理学与文化”。日本恵泉女学園大学校长木村利人报告的题目是“文化与生命伦理学——与自然的和谐在日本”;美国霍华德大学的尼日利亚哲学家Segun Gbadegain报告的题目为“全球生命伦理学中的非洲”,他指出,文化是可变的,并且不断在变化,生命伦理学可以与非洲本土的价值“人类的繁荣”结合起来。
邱仁宗研究员在题为“生命伦理学是创造文化的力量”的发言中指出,生命伦理学不仅受文化约束,而且也可能改变文化,成为创造新文化的力量。他认为,首先生命伦理学要有一个合适的定义,以维护它的理性、规范性的性质。认为“生命伦理学仅是不同学科之间沟通的技能”、“生命伦理学是生命科学和医疗卫生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和政策的研究”、“生命伦理学是对生命的爱”这些定义否认了生命伦理学的学科或领域性质,否认其规范性,否认其是理性事业。合适的生命伦理学定义应该有4个要素:(1)问题(伦理问题)是生命伦理学的逻辑出发点;(2)探究(伦理学探究);(3)行动,将伦理学探究结果转化为行动,并在行动中将接受检验;(4)目的:促进负责任的科学研究、临床和公共卫生干预,维护病人、受试者、公众的权益,动物的福利以及生态环境的平衡。接着,他以目前有争论的干细胞治疗为例说明,在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如何从问题出发,经过伦理学研究,形成有关成体干细胞临床试验和应用的伦理准则。最后,他指出,Snow于1959年指出现代社会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缺乏沟通是解决世界问题是主要障碍。但生命伦理学正在创造一种新文化,其中科学和人文都有其自己的地位,并且越来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在“全球化生命伦理学中的东西方原则”这一专题讨论会中,翟晓梅在她的题为“和而不同”的发言中,以知情同意为例分析了如何正确处理国际伦理准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她指出,当应用国际伦理准则时我们应该尊重本土文化中的信念和价值,努力吸收积极元素于我们研究的程序之中。唯有这种进路使我们能够恰当地处理文化张力,有效地保护受试者的权利和福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把知情同意原则分为两部分:硬核和外周部分。知情同意原则的硬核是:(1) 忠实地告知充分的信息,没有歪曲、掩盖和欺骗,使受试者能够做出决定; (2) 积极帮助他们理解告知的信息;以及 (3) 坚持自由的同意,没有不当的理由和强迫。在所有文化中进行研究,硬核必须坚持,不能放弃。它的外周部分包括:(1)信息告知的方式(用书面材料还是录像带、VCD/DVD);(2)表达同意的方式(书面还是有证人在场的口头同意);(3)同意书使用什么词(是否用“研究”或“实验”这样的术语);(4)家庭或社群是否参与知情同意过程等。外周部分是灵活的,可随不同文化而异。这样的结果将是恰如孔夫子所说的“和而不同”,即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生命伦理学应该是和谐而不同一,或和谐而多样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Richard Cash指出,生命伦理学的准则是保护受试者和病人,东西方任何一种宗教和文化都没有拒绝不伤害和受益最大化原则。我们需要做的是尊重文化差异,不要在法律框架内看伦理学。应该拒绝发展的黄金规则:拥有黄金的人制订规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挪威卑尔根大学的Reidar Lie指出,认为西方强调个人自主性,东方则是社区和家庭决策这种看法缺乏经验证据,主要基于个人的印象;我们应将生命伦理学的争论置于该国更大范围的政策讨论之中,这些政策讨论都要提及规范和价值,而规范和价值是本土文化与外国影响的复杂综合,把生命伦理学与政策分开,就会产生误解;有关跨文化差异的争论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
虽然中国是国际生命伦理学协会的创始国,而且2006年我们成功举办了第8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国际生命伦理学协会曾任会长、哈佛大学教授Daniel Wikler评论说,“你们的大会树立了一个后人难以逾越的标准”,但长期以来在该协会中没有中国的代表。在创立协会时,当时的协会领导人强调协会的代表性,因此,理事会是按照各大洲、主要国家分配理事名额的,中国应在理事会中至少有一个名额,当时邱仁宗是代表中国的理事。但后来的协会领导人取消了这一正确的做法。即使最近几任的会长,例如美国的Alexander Capron和Ruth Macklin都认为这样不妥,但中国代表仍然遭到排斥。这届大会因为主办方新加坡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本届大会主席Alastiar Campbell对中国的生命伦理学学术活动有所了解,才正式邀请邱仁宗和翟晓梅作为特邀发言人(invited speakers)出席大会。我们的报告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
我们认为今后还应该积极参加大会的学术活动,并建议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该协会。
第11届亚洲生命伦理学会议
亚洲生命伦理学协会前身是东亚生命伦理学协会于1997年11月5日在北京建立,当时会长为日本的坂本百大,邱仁宗和韩国的宋相庸为副会长。
后东亚生命伦理学协会改为亚洲生命伦理学协会,2002年改选邱仁宗任会长,宋相庸(韩国)、Leo de Castro(菲律宾)、翟晓梅等任副会长。在当时的理事会上,邱仁宗建议,亚洲生命伦理学协会应该有代表性,因此,除会长外,亚洲重要国家和地区应该由代表担任副会长,例如中国、韩国、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等,而副会长人选应该由本国推举候选人。这个提议在会议上得到理事会的一致认可,并且得到很好的落实,成为一项规定。
本届亚洲生命伦理学协会改选,Leo de Castro(原菲律宾伦理委员会主席,现在新加坡工作)担任会长,由他主持的本届第11届亚洲生命伦理学会议(新加坡大学组织),特邀邱仁宗和翟晓梅参加会议并进行大会发言。我们最终接受了邀请并如期参加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下一届(第12届)亚洲生命伦理学会议将在台湾举办。在本次会议上,台湾方面会议主办方几次主动与我们商量会议召开的组织和学术事宜,台湾主办方希望下次会议能够得到大陆学者在学术上和道义上的全力支持。考虑到两岸合作的积极意义,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会全力支持并积极组织大陆同行参加台湾同行主办的这次会议。我们一贯强调国际学术组织应该有代表性,活动应该有公平性,我们应该有独立性。
在此次亚洲生命伦理学大会上,邱仁宗研究员应邀介绍了他在2009年12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授奖演说中讨论的三个问题: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模型、生命伦理学的体制化,以及国际准则与本土文化的关系。
他指出,探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和医疗卫生中的伦理问题有种进路或两个模型。一个模型是“放风筝”。一些同行喜欢援引过去的哲学家在某一伦理问题说过什么,而从不对这个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他们的谈论或写作类似放在天空中的风筝,不接触地面的现实。有些哲学家认为只要建构一个完美的伦理学理论体系,世界上所有实际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另一些人试图从他们喜爱的伦理学理论演绎出临床和研究实践中伦理问题的解法。然而,绝不存在一种万能的伦理学理论,它能解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伦理问题。一个绕不过去的反例是,知情同意的概念是从哪个伦理学理论推演出来的?它是在总结历史教训中“归纳”出来的。另一种是“骑单车”模型。这一模型要求我们关注在临床、研究和公共卫生实践中涌现的特定伦理问题及其特征。每一个伦理问题都是“定域的”,这是说,每一个伦理问题都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从某一伦理学理论或原则中推导出的伦理要求都是初始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是“划线和权衡”的结果。根据这种骑单车模型,我们必须对尖端技术及其在生物医学中应用中涌现的伦理问题十分敏感。鉴定这些伦理问题,权衡不同的价值,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对这些解法进行论证(反论证)和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按照骑单车的隐喻,我们总是脚踏实地的。
接着,他介绍了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的几次年会讨论的问题,尤其是这次昆明会议的议题。在生命伦理学体制化方面,介绍了我国伦理委员会的三层机构以及卫生部专家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及其成果。在国际准则与本土文化的关系方面他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并介绍我们的国际合作活动,如中英纳米技术伦理学会议(2009)、中荷动物生物技术伦理学会议(2009)、中日韩东亚国家危重病人决策研究(2009)、中美临床试验伦理问题会议(2009)、中法医院伦理学会议(2001)、中欧生殖医学和干细胞研究合作伦理管治项目(2007-2009)以及中德人与动物混合有机体的哲学伦理学研究项目(未来)。
翟晓梅教授应邀在大会上做了“生物特征识别学中的伦理问题”的报告,她指出,1982年一部美国科学幻想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s)描述了2019年11月洛杉矶复制机器人一次暴力反叛后就被禁止呆在地球上,他们仅可用于地球的殖民地,从事危险的、不熟练工作的奴隶。任何复制机器人胆敢违反禁令,回到地球,就会被称作“银翼杀手”的警察追捕。对复制机器人的识别唯有靠一种分析瞳孔收缩和扩展的机器。能够识别复制机器人的机器是一种生物特征识别装置。现在这已不再是科学幻想了,生物特征识别学或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已成为信息技术(IT)最为重要的创新,生物特征识别产业的产值已从2002年的6亿美元激增至2007年的40亿美元。生物特征的识别是根据某人的特征验证其身份,也就是“根据他/她具有什么来鉴别他/她是谁”。有两类生物测定的特征:(1)生理学的特征,与体形有关,例如包括但不限于指纹、面部识别、DNA、手部和掌部的几何形状、瞳孔识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视网膜识别)、气味等。(2)行为的特征,与一个人的行为有关,如包括但不限于打字节奏、步态和声音。可用于生物特征识别学的人类特征必须具备:普遍性、独特性、恒久性、易收集、性能良好、可接受性、可代替性。生物特征识别系统的两种操作模式是验证(verification)和鉴别(identification)。生物特征识别学中的伦理关注首先是隐私的保护。由于身体和心理特征或状态可从生物测定值中推演出来,因此大多数因生物特征识别学提出的重要伦理关注与“功能潜变”(function creep)有关。功能潜变是指获取信息的原来目的被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扩大包括未获得参与者知情和自愿的同意。其他伦理关注有:污名化和歧视、物主的人身安全、身份的丧失等。鉴于在国内的生物识别技术的广泛开发与应用,但隐私保护等伦理学的讨论以及相关政策制定一种滞后的现实。
最后,她提出了9条伦理管治的原则:
原则1:基本目的。生物特征识别学的研发及其应用的基本目的是用更为安全、有效、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人民的安康和提高生活质量,即“以人为本”。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应该仅仅用于合法的、合乎伦理的和非歧视性的目的。生物特征识别学的任何行动应该根据有益和不伤害原则加以评价,这是努力在预料的受益与可预知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的基础。在生物特征识别学的应用中,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必须加以适当的平衡。在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时,这种限制应该是必要的、相称的和最低限度的。
原则2:负责研究。生物特征识别学的研发及其应用应该保持高标准的负责研究,即坚持研究诚信,反对不端和有问题的行为,承诺维护和保护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原则3:利益冲突。在生物特征识别学的研发及其应用中专业人员、公司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应该适当处理。任何情况下人民(尤其是脆弱人群)的利益不能因追求专业人员或公司的利益而受到损害。
原则4:尊重。尊重原则要求尊重人的自主性和自我决定权,必须坚持知情同意原则。在个人信息再使用于另一目的时,必须获得同意。
原则5:隐私。人的尊严要求我们保护隐私、保密和医疗秘密,要求我们不仅不要侵犯个人的隐私/保密权,而且要尽力防治不合适地或非法地泄露私人信息。
原则6:公正。公正原则要求有限资源的公平分配,防止因不适当地泄露个人信息而产生污名和歧视。
原则7:共济。共济原则要求我们维护每个人享有从生物特征识别学的研发及其应用中受益的权利,特别关注社会中的脆弱人群。.
原则8:透明。透明原则使生物特征识别学的研发及其应用对公众(纳税人)成为透明的,帮助他们了解什么是生物特征识别学,能从其应用中得到什么受益和会有什么风险。
原则9:参与。公众参与原则要求我们采取措施来促使公众对生物特征识别学的了解,并引导公众参与生物特征识别学的研发及其应用的决策过程。
会议代表对我们的发言显示了极大兴趣,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代表们表示,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上做了很多工作,颇有成就,可喜可贺。
(翟晓梅 邱仁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