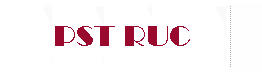摘要:创新方法研究不同于科学方法研究,不以寻找普遍方法为目标,而是旨在指导实际的创新过程。创新方法研究应该坚持“助发现”的方法论指导。在助发现的方法论看来,创新方法不是一种传统科学方法意义上的普遍的、规范的和确定的常则,更多的是一种启发的、帮助的和支持的异质东西,至少包括逻辑上的、心理上的、制度上的和文化上的各种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的“帮助”或“方法”。助发现的创新方法研究可以从正面研究、反面研究和综合研究三个方向推进,包括创新心理、创新制度和创新文化等非逻辑的异质性研究。在远期理想上,可以尝试把创新方法作为横断现象进行普遍化研究,提炼专有核心概念,形成作为横断科学的创新方法论。
关键词:创新方法,方法论,助发现
目前,既有创新方法研究分散在各个学科领域,涉及到科学方法论、科学史、思维科学、创造学、决策学、心理学以及决策科学等诸多领域,十分庞杂、零散,缺乏有效的整合。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创新方法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没有得到厘清,亟需哲学反思。解决创新方法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可以从解决一个前提性问题开始,即有没有普遍意义的创新方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创新方法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方法有什么区别?创新方法论与科学方法论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区别?本文尝试着从这两个问题出发,对创新方法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提出一种“助发现”的研究方法论,不惴浅薄,敬请方家批评。
创新到底有没有方法?所谓创新,就是创造新的、原来没有东西。虽然创新可以是一定程度上的,比如局限于工具上、操作层面、运用领域上的创新,但是,从绝对意义上说,绝对的创新覆盖最深层的认识和方法上的创新。也就是说,一种用于创新的方法第一次算创新,第二次运用就不再是绝对意义上的创新了。那么,绝对意义上的创新应该是没有方法、不可重复和不可追寻的,任何从过去的创新活动总结出来的方法在本质上不能算是创新,而是模仿、重复或者运用,作为常则的创新方法本身就可能是一个悖论。类比强纲领SSK学派著名的反身性悖论,即建构主义主张包含着它本身就是建构的而“没有客观的科学身份”[1],我们称上述悖论为“创新方法的反身性”疑问。一言以蔽之,方法指导下的活动是一定程度上的重复活动,还是不是绝对意义上创新活动?在方法论上,反身性悖论直接就质疑了经验归纳方法在创新方法研究中的合法性:经验归纳本质上是从过去推知未来,属于一定程度上的重复过去。
对反身性疑问的思索,很容易引向科学哲学史上著名科学的发现与辩护的争论。从反身性的角度看,支持发现与辩护两分的人很可能会否认创新方法的存在,或者将这个问题排除在传统的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范围之外。科学发现与辩护的区分,是正统科学哲学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极力主张的经典命题之一。大致来说,这种区分认为,科学研究中的发现情境包括科学假说与科学理论的产生过程,无法进行逻辑分析,属于心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经验化研究的领域;而辩护情境包括对科学假说和科学理论的证明与确认,是可以进行逻辑分析的,属于科学哲学、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进行形式化研究的领域。
最早提出发现与辩护两分命题的波普尔是从科学研究的过程角度来看待这一区分的,即科学工作的最初阶段是发现的过程,是无法逻辑重建的,辩护过程是科学发现之后的新阶段,属于科学哲学研究的范围。[2]因此,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基本没有讨论科学发现的逻辑。逻辑实证主义者接受了这种区分,并把它推向极端。在他们看来,发现与辩护的区分不仅是科学研究过程的问题,还蕴含着经验/逻辑、非理性猜想/理性重建、心理现象/科学方法、非科学哲学/科哲哲学等诸多分立。从发现与辩护的角度看,创新显然属于发现而非辩护的范围,于是对于坚持发现与辩护两分的科学哲学家而言,即使不完全否认创新方法的存在,也会提出这样的质疑:有没有可以逻辑分析的创新方法?如果创新方法不可以逻辑重建,那些创新方法研究应该怎么进行下去?换言之,这种的研究的目标和宗旨何在?
除了发现与辩护两分的哲学质疑外,既有的创新方法研究也存在着类似反身性的质疑,这里列举最常见的三种观点。
很多人认为,创新是态度问题,而不是方法问题。这种观点认为,创新中没有作为常则的范围,或者即便有,也是不可言传的,属于波兰尼所称的意会知识。因此,创新方法研究的重点不是寻找付诸于文字的、可以普遍运用的方法,而是要设法保持人们的创新热情。对于创新态度派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心理状态、情感状态下,人最容易产生创新的冲动、创新的力量?显然,这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围。
创新心理派的思路再前进一步,即从个体创新心理“养护”前进到群体创新心理“激发”,顺理成章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群体情境下,如何保持个体的创新心理状态?在群体状态下,创新个体可能会被压抑,也可能被更好地相互激发。因此,很多人认为,创新首先是制度问题,而不是方法问题。也就是说,创新方法研究的重点是寻找一种最能激发个体创新状态的制度,要产生1+1>2的非线性效果。
沿着创新制度的方向,有人提出,单纯的制度是不能解决群体创新能力的激发问题的,这个目标要靠文化解决,即营造一种适于创新的文化环境,于是创新方法问题转变为创新文化问题。按照企业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解,文化包括精神层、行为层、制度层和物质层四个组成部分。所以,群体创新激励的问题要运用各个反面的文化资源、从多个层面有机地解决。
如何回答创新方法的反身性疑问?可以继续从科学哲学的诸多理论中寻找可借鉴的资源。
波普尔之后,包括汉森、库恩、费耶阿本德在内的诸多科学哲学大家都对发现与辩护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模糊甚至取消这一区分的呼声越来越高。总的来说,反对的理由主要有5个[3]:(1)在实际科学研究中,两者是不断相互交替出现的,区分是暂时的;(2)科学发现有逻辑方法的因素,问题在于是否要坚持逻辑主义对逻辑的狭窄理解,比如皮尔士的“逆推”、波兰尼的“合情推理”可以算作逻辑的范围;(3)科学研究除了发现与辩护之外,还有别的阶段;(4)辩护中包含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因素;(5)心理学及其他的经验科学领域也与认识论有关。实际上,争论的双方对科学发现、科学辩护以及逻辑等范畴理解差异很大,是争论之所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学哲学史上关于科学的发现和辩护的争论,给创新方法研究以极大的启发。最直接的启示有两个:首先,发现领域的创新方法不一定是严格逻辑重建的,而可以是超越传统逻辑主义的,隐喻、想象、合情推理甚至信念等都可以纳入创新方法探讨的范围中。更进一步,创新方法既然不是严格逻辑的,那么创新方法不可能具有逻辑方法那样的普遍性,换言之,创新方法研究必须要放弃严格的普适性,而转向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和一定层面的适用性。其次,发现领域的创新方法研究并不仅仅属于传统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哲学探讨的问题,而是应该把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的经验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纳入其中。更进一步,心理学等非逻辑领域的方法研究不是与创新方法直接相连的,而是启发式、帮助性和间接作用的。比如,社会学研究发现“优先权”对科学创新有极大的刺激作用,那么如何保障、加强对“优先权”的追求就可以帮助创新,属于创新方法的外围问题。
科学哲学家苏珊·哈克提出的“批判常识主义”,对科学与科学方法进行了全新的理解,实际上已经提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方法是普遍的、规范的和确定的,而极端的历史主义者比如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没有什么方法,怎么都行。对此,哈克持一种折中的方案,认为不存在正统科学哲学所理解的科学方法,但存在类似普遍科学方法的“科学帮助”,它不能确保科学走向真理,但可以帮助科学发展。在哈克看来,科学是一种探究,具体地说属于经验探究的一种。“科学探究是与其他类型的经验探究是相连续的。但是,对于我们在最为通常的经验探究中所依靠的东西,科学家进行了许多修改,并以种种方式进行了扩展和精练。”[4]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不完全是独特的,常常会用到其他经验探究所用的方法,因而与日常经验探究紧密相连。但是,这并不代表科学没有自己专门技术和方法,这种专属科学的探究方法即哈克所称的“科学帮助”。
哈克之所以发明属于“科学帮助”来取代科学方法,是表达在认识论上比“科学方法”要弱的意义:科学方法是科学独有的,科学帮助是日常经验探究方法发展而来的;科学方法是普遍的、逻辑的、规范的和确定的,科学帮助是范围更广、更为异质性、局部化,包括了想象、隐喻和概念的创新等非逻辑的因素,甚至包括科学分工、专业化、同行评议、学术公开制度等社会性因素,并且往往专属于某个领域或子学科,而不是普适性的。科学方法确保真理的获得,科学帮助只能保证科学理论一定程度的成功,在经验上变得更为稳固。同时,科学帮助又是属于经验探究方法的范畴,很容易与宣传、宗教、娱乐等非经验探究区分开来。显然,“科学帮助”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科学方法论的范畴,更接近于实际科学发现中的创新方法。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路,它不执着于从认识论上逻辑地重构科学认识,而是寻找能实际起作用的、启发新思想出现从而推进科学发展的实用“帮助”。当然,这样的“科学帮助”能否保证我们朝真理前进就另当别论了。在这个问题上,哈克倾向于在“科学帮助”在实际的科学史上似乎起到了这种作用。
受批判常识主义的启发,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创新方法研究的“助发现的方法论”,可以大致解决创新方法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其核心理念是:创新方法不是一种传统科学方法意义上的普遍的、规范的和确定的常则,更多的是一种启发的、帮助的和支持的异质东西,至少包括逻辑上的、心理上的、制度上的和文化上的各种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的“帮助”或“方法”(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强方法)。
有没有创新方法?在助发现的方法论看来,对方法的理解可以分为强意义上的和弱意义上两种。所谓“强意义”是指达到作为普遍规律、类似传统科学方法的“强度”,“弱意义”是指达到有实用价值的、可帮助创新的、至少可重复一次以上的“强度”。助发现的方法论认为,创新活动不存在也不必需强意义的创新方法,存在的、有价值的也是可以探究的是弱意义的创新方法。实际上,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绝对强意义的科学方法也是不存在的。
创新方法论与科学方法论有什么区别?传统的科学方法论的目标是认识论的,即从逻辑上重构科学研究的逻辑过程,是面向过去的解释理论。助发现的创新方法论是实用主义的,即立足于帮助创新实践的启发过程,是面向未来的指导理论。这种区别抓住了创新方法研究的宗旨,即为什么研究创新方法的问题:创新方法研究的目的是实用,而非认识论地重构创新过程。再完美的创新重构对于未来的创新都可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创新毕竟是新的,而非重复旧的。
助发现的创新方法论追求对未来创新活动的实用主义指导,寻找能在一定程度上可重复、可启发和可操作的“方法”。也就是说,创新方法不等于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属于创新方法的组成部分,不能把创新方法作为认识活动或科学方法来研究。科学方法追求的是普遍性,创新方法追求的是可重复性、可启发性和某种对创新的支持。这种重复性根本不能达到普遍性的高度,往往只能在某个狭窄的领域中或很具体的问题上重复使用,或者仅仅是具有启发意义。
助发现的创新方法论并不指望规范未来的创新活动,相反它恰恰指望在过去轨迹的基础上突破过去。所以,在实际运用中,创新方法必定要出现变形、扭曲甚至倒置的情形,不可能完全地重复。这种不完全重复恰恰是助发现的创新方法论所要求的,即对创新方法的运用不是重复,而是又一次的创新。能够给新的创新以更多帮助的创新方法,就是好的创新方法。
助发现的创新方法坚持扶助、激发和培育的思路,悬置客观性、真理和逻辑的追求,因而不排斥经验归纳法。因为助发现的创新方法论对过去的归纳不是为了重复过去,而是汲取过去的智慧,并以此为基础再创造。所以,这里并不存在经验归纳与未来重复之间的矛盾。并且,从本质上看,助发现的创新方法研究只能走经验研究的道路,而不是走逻辑研究的道路。换言之,就是要在过去与未来类似“解释学循环”的情境中创造全新的东西。经验归纳、总结和一定范围的普遍化是创新方法研究的基本方法,不同于科学方法研究的逻辑重建方法。试图建构一种完全确定的、机械的甚至逻辑演算的创新方法体系是不可能的,科学发现的争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助发现的创新方法更多的是间接的帮助,而不是直接的方法。
在助发现的创新方法论背景下,创新心理研究、创新制度研究和创新文化研究等对创新方法的非逻辑研究当然属于创新方法论的范围。创新心理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体达到最佳的创新心理状态?创新制度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构一种使群体达到最佳的创新心理状态的制度?创新文化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培育一种激发创新的文化环境?因此,创新方法研究是异质性的、复杂性的,各个分支在主旨、视角以及问题域、应答域上差异很大,助发现的方法论不以一个逻辑严整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严守帮助创新的实用主义。
助发现的创新方法研究必须要走跨学科的道路。创新方法研究的产生始于问题即如何提高个体、全体乃至国家的创新能力,因此属于典型的问题研究。围绕一个问题可以产生各种视角、各种层次和各种领域的不同研究,既有的研究现状中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二战以后,横断科学(如系统论、信息论)兴起,人类知识进步的历史进程出现了对学科分化的反动,更多地表现出知识综合的、跨学科的、以问题为中心来组织研究的新趋势。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中,利奥塔认为:“跨学科的观念在本质上属于非合法时代”,也就是说,“跨学科”是他所指的“后现代”最重要的知识生产观念和趋势。[5]作为当代新生的学术前沿问题,创新方法研究单凭一个学科资源根本无法解决,必须要走跨学科的道路。这一点也是助发现的创新方法论主张的异质性帮助思路所要求的。
在助发现的方法论原则之下,至少存在三种研究创新方法的方向,即正面研究、反面破除研究和综合研究。
创新方法的正面经验研究是指从已有的成功创新案例中总结经验,归纳示范性的思想或“方法”(弱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显然,这种经验更多是以智慧而非常则的形式出现,更多着眼于启发而不是灌输。按照归纳的程度的不同,创新方法的经验研究还可以细分。可以总结卓越科学家的创新智慧,这属于纯粹的个案研究。或者总结某一群人或某一专业的创新技巧,也可以对某一类创新案例进行普遍化提炼,比如TRIZ理论就是从大量的专利发明中总结出的一种可操作的技术。总之,经验研究是从具体的成功事例出发摸索有益的路径。
创新方法的反面破除研究,又可称为“反束缚”研究,旨在破除权威迷信、思维定势和陈腐观念。所谓“创新”,反过来说就是“破旧”。破除研究是经验研究必要的补充,在实用价值上甚至大于正面启发。如果细分反面破除研究,起码包括:对反权威、反传统的创新事例中的教益的研究;对失败的创新案例的教训的分析;对常见的思维定势、错误常识的研究;对“另类”思想、观念中创新方法借鉴意义的研究,等等。特别要提到的是“另类”研究,在科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有很多在当时仅为少数人所支持的“另类”,往往对创新很有启发。
创新方法的综合研究,就是要将目前既有的、分布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整合起来,要在跨越整个自然科学方法论、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和思维科学方法论的广泛领域中整合所有创新方法资源,重点包括创造学、科学方法论、思维科学、决策论、领导科学、管理科学、逻辑学、运筹学、博弈论等学科或理论的既有研究成果。
助发现的创新方法综合研究方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将创新方法视为一种横断现象来研究。这也是助发现方法论的远期理想:把创新方法论构建成一种类似系统论、信息论的横断科学。显然,创新方法综合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有机地整合这些资源,而不是简单地拼凑?上述涉及的学科普遍性程度不同、研究对象不同、层次不同,如何整合?从最宏观的意义上看,创新是人类活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时期均存在的普遍现象,可以作为某种横断的因素来考察。作为横断现象的创新活动,存在某种程度或某种视角下共通的东西。对这种共通的东西的研究,存在着建构横断科学的某种可能。把创新方法作为横断现象来研究,创新方法综合研究将不是类似百科全书式的复合,而可能成为横断科学。换言之,助发现的创新方法论在从经验归纳出发的同时,始终关注创新方法研究普遍化的可能。
当然,横断科学理想的实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和天才的哲学反思,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提炼出适用于共通的创新现象的基本概念。从内容上看,助发现的创新方法论包括了科学方法、思维方法、心理学方法、制度方法、文化方法和卓越人物的智慧等等诸多异质性的要素,从中提炼出普适性的专有概念非常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这种提炼的理论建构必须是实用主义的,能在实际的创新活动中给予操作性的指导——这是创新方法论能够存在的根本。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理想,作为横断科学的创新方法论研究是可以尝试的。
参考文献
[1] (美)贝纳德·巴伯.在科学社会学发展中的某些模式和过程[C].载于(美)舍格斯特尔编: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9
[2](英)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M].沈阳:沈阳出版社.7-8
[3]刘大椿主编.“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71-274
[4](美)苏珊·哈克.理性地捍卫科学:在科学主义与犬儒主义之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5-86
[5](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北京:三联书店,1997.110
On Methodology of Innovation Method
Liu Yong-mou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Research on innovation method differs from researching on science method, whose proper is not to seek universal methods, but to instruct actual innovation. Research on innovation should adhere to “discovery-helping” methodology, from which innovation methods is not universal, normative and certain, but heuristic, helpful and heterogeneous, at least consisting of logic, ment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help” or ”method” that can repeats in some degree. Discovery-helping methodology includes frontal research, converse research and synthetic research. In the long term, research on innovation method can be constructed to some kind of transect science.
Keyword: Innovation Method, Methodology, discovery-hel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