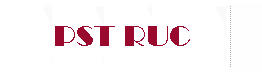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摘要]究竟怎样看待科技,历史上有两种基本取向:第一种是科学主义,试图说明科学为什么是合理的,以对科学进行辩护为标志;第二种是反科学主义,即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指斥科技给当下世界带来巨大风险。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判都是有局限的,应该对科学采取一种审度的态度。马克思对科技的分析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采用了独特的历史实践视角,为科技审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杆。科技审度论倡导一种多元互补的价值选择,在客观性与独特性、普遍性与地方性、理性与非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多元开放的科技哲学,通过科学与宗教、科学与艺术、科学与信仰,也即科学与人文之间所展现出来的互动与融合,致力于实现求真、向善、臻美、达圣之圆融。
【关键词】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科技审度;多元互补;真善美圣
人类历史和当下人类文明离不开科学技术,而且无论从正面还是从负面来看,科技的作用和影响都越来越重要。作为科技反思的科技哲学面临着重大挑战,需要确立一种新的理念、新的视角、新的价值观。这种挑战,既涉及应当怎样看待科技的问题,又涉及应当怎样看待现有科技哲学的问题,当然,更无法回避科技哲学应当如何因应世变以面对科技未来的问题。过去,我们将这些问题通称为对科技的哲学反思;当下,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这种反思的时代特征,我们将其称为对科学技术的审度。
在现代社会,人们与科学技术之间已经形成须臾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然而,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科技,并无太多的共识。哲学界在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间充满了误解和斗争。实际上,关于科学的攻防一刻也未曾停息。
(一)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
怎样看待科技,或者说哲学如何对科学反思,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两种基本取向。
第一种取向是科学主义,以对科学进行辩护为标志。这是哲学对科学反思的一个基本态势,也是传统的主流观点。何谓辩护?就是试图说明为什么科学是合理的,为什么科学知识有精确性、可预见性等特点。
回顾科学技术的成长历程,可以发现,科学在近代欧洲的诞生及其自17世纪以来所取得的大发展,可以归结为科学力量不断壮大、科学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扩张的历史。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与社会力量,科学不仅开启了人类在认知领域的大拓展,也创造了人类在改造自然方面的辉煌成就,确立了科学进步观的基本立场。但是,随着科学主义思潮的泛化,科学的工具主义特征被发挥到极致,其间的负面效应也日渐显著。
第二种取向是反科学主义,即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在对科技满是赞叹和赞扬的同时,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批判声音。这正是当今科学哲学界若干重要流派所大声疾呼的。它们有感于人类发展到现在的许多问题,尖锐地提出正是科技给当下世界带来巨大的风险。
科学主义霸权走向极端,就是反科学主义的兴起与扩张,一种对科学怀疑与否定的思潮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在20世纪末期,对科学的质疑甚至变成对科学的全盘否定,不同领域的“终结论”甚嚣尘上。与此相对应的是正统科学哲学为科学辩护的声音逐渐衰微,科学的传统形象受到严重冲击。
于是,科学合理性不再被视为当然,反而在很多人心中产生了重大疑虑。在反科学主义者心目中,科学不再是对真理的无私而神圣的追寻,而是与政治共谋的权力,是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是听命于赞助人的工具和残酷统治自然的帮凶。
近年来,历经辩护与批判的较量,在科学哲学中出现了一种新取向,笔者称之为“审度”。其基本观点是: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判都是有局限的,应该对科学采取一种审度的态度,用多元、理性、宽容的观点来看待科学。当今对科学的反思,应该实现“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
必须指出,逻辑实证主义极力赞美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之立场固然不完全可取,大多数另类秉持的彻底否定主流科学的理念也只能是另一个极端。在当下的若干争论中,对科学的辩护与对科学的批判两者都不乏真知灼见,它们的澄清对科学未来发展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但客观地说,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都有走极端的倾向,虽然极端带来深刻,但肯定有失公允。思想上的极端给人以启发,行动中的极端却肯定会导致失误甚至灾难。因此,跳出各自在论辩时所持的极端立场,是尤为重要的。
极端的科学主义把科学理想化、纯粹化,很难解释复杂的科学世界;极端的批判又完全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主张真理多元论,取消科学的划界标准,甚至认为科学跟神话、巫术其实是一回事,抹杀了科学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对人类生活的极大贡献,片面地夸大了科技本身在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重要的是既支持科学的发展,又保持对科学的警醒,超越对科学的辩护和批判,而对科学持有一种审度的观点。这就是我们从对科学的多样复杂的反思中得到的基本观点。
在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早已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应当承认,极端的科学反对派虽然偏颇,但能起到矫正盛行的唯科学主义局限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公众对科学的恰当认识,营造社会自由、平等和宽容的氛围。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虽然对科学基本上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但其所起的作用倒是前瞻性的。然而,要特别警惕,一味盲目地批判科学,倡导反科学主义,在我国科学基础和科学精神本来就很薄弱的境况下,不小心会导致回到前科学的愚昧状态。
审度不是折中主义,而是整合对立观点,是执两用中。实际上,辩护者与批判者的激烈辨驳,催生了一种比较宽容的、平和的但不失基本坚持的科学哲学倾向,即所谓科学审度。
笔者在考查各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观点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到马克思的科技思想,不仅发现马克思许多至今闪光的精辟论点,而且从中体会到一种极为宝贵的方法论。
怎样看待科技?运用什么方法论视角去剖析科技?是科技审度最重要的考量之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中极为重视对科技的分析,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并采用了独特的视角。马克思借此直击科技的本质,为科技审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杆。
马克思是怎样看待科技的呢?
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多是就具体科技活动层面言说的,包括对科技史实的记录、转述,对以往科技思想著作的摘录,更不乏对科技问题的多侧面思索。
要言之,马克思虽然没有留下科学技术论方面的专门著作,但他确实探讨了许多科技问题,对科技现象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深入思考,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科技思想材料。马克思的科技审度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方法上去看,都是极其珍贵的遗产。
马克思不是简单地面对科技,而是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对科技加以审视,时而赞赏、时而批判。他以思想家的深刻和睿智对科技进行审度,他的科技审度既有超出常人的理论深度,又总是无比关切现实问题。
对马克思科技思想的研究,切勿因望文生义而被绝对化,更不能离开具体语境而忽视甚至歪曲他的本意。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马克思的学术研究始终着眼于探求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并且总是将它们追溯到矛盾产生的根源。必须弄清楚马克思历史实践视角的深意,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何以会如此看待科技。
下面试举数例来扼要说明,马克思如何从历史实践的视角对科学技术加以审度,以揭示资本对科技的绑架。
为揭示资本化如何强化科学技术与生产发展的关系,马克思论证道,科学发现与生产过程恰好在互相成为手段:“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③]。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科学与技术的资本化使它们沦为资本剥削工人劳动、追求剩余价值的帮凶。“在这里,机器被说成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被说成是生产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或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④]
为说明科学与技术的资本化,改变了科技的原有进程和本来面貌,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⑤]。
以机器为主导的机械化劳动方式,推动了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然而,马克思发现,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产生了一系列对立的社会现象:“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⑥] 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深刻剖析,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绑架”了近现代科学技术,科技则迫于资本的势力而“入伙”。
(二)科技审度的重要标杆
马克思的科技审度,特别是他围绕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科学技术与异化的关系、科学技术与自由的关系所进行的探讨,以及由此展开的对科技的批判,对于如何正确看待现代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正是马克思对科技审度的这些论述,为科技审度论树立了重要标杆。
与自然科学文本含义的确定性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文本的意义生成于读者阅读文本的过程之中,不同的读者甚至同一读者在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时空场合下解读同一个文本,得到的收获或启迪都是有差异的。对于马克思的科技思想,既要从有关经典文本诞生时的语境去理解,又要结合当下的语境去把握。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经典文本常读常新、千古流传的主要原因。要避免脱离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具体历史场景,直接从当代社会文化背景出发解读马克思文本,随意发挥和引申文本原义,把时下对科技的理解简单搬运到马克思身上。
回到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走进马克思的科技世界,重读他的原始文本,还原马克思的科技思想,应当成为当下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马克思审度科技提出的那些观点和方法,过去和现在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马克思强调,科技飞速发展对社会生产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科技进步无疑引起了马克思的浓厚兴趣和深入思考,这不论是在他的相关著述中,还是有关马克思的传记资料和旁证材料中,都不难看到。尤其是在探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更是花费了相当多的心血探讨科技问题,留下了丰富的科技思想文稿。1850—1858年,马克思除了研读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外,还认真阅读了各种有关科学技术、工艺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极大地改善了他的知识结构,开阔了他的理论视野,为日后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分析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做了思想上和资料上的准备。
马克思认为,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与追求效率的技术之间具有同一性。提高认识水平与技术效率,必然会创造出比原先更多的价值,这正是资本所渴求的;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运作,肯定会优先支持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把科学技术纳入自己的运行轨道,这也是科学技术发展所企求的。马克思揭示了科学技术与资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⑦]。基于这种天然的联系,资本与科学技术很快“联姻”,二者的融合与互动促使人类社会迈入资本主义时代。
马克思指出,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已被纳入资本的运行轨道。科学与技术是在资本形成之前早就存在的文化现象。然而,近代以来,在资本的渗透与扩张进程中,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却被逐步纳入资本的运行轨道,受到资本的选择与调制,呈现出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马克思写道:“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被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劳动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⑧]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产业技术处于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最后环节,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也是通过产业技术的形式间接实现的。
马克思认为,应从人类活动方式上理解技术。在马克思看来,人性主要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而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等都是产业技术的具体形态。他认为,对人性的探究应当到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之中去寻找。“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⑨] 产业技术既是形成人性的基础,也是认识人性的重要途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⑩]
可以说,马克思的科技审度论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值得深入开掘。
三、多元互补的价值选择
因应新的视角、新的主题的不断涌现,面对那些与正统进路迥异、旨趣不同的新研究,科技审度论不但将突破传统的局限,而且将极大地改变科学技术论的基本形相,通向一种多元开放的科技哲学。
科技哲学要与时俱进。一方面,一些以往不被认同或尚未成型的科学技术论分支,典型的比如科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人类学、科学文化哲学以及科技伦理学等,正在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新的生长点。另一方面,当代科技世界呈现出一派斑杂景象:传统观点与建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夹杂在一起,未来的科技世界究竟怎样,让人充满想象。无论如何,它应该是自由而开放的,即是要倡导一种多元而互补的价值选择,在客观性与独特性、普遍性与地方性、理性与非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
客观真理的追求曾被视为科学的最终目标,因而科学作为一种真理也就必然地具有客观性与中立性的特征。特别是在经典科学传统下,如何实现并达到真理的客观性与绝对性成为各种科学研究的最终旨向。然而,当科学中的个体性与主观性因素引发人们的关注,当真理的具体性与相对性特征变得突出起来,科学原先的那些追求就变得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了。如何在客观性与独特性、绝对性与相对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成为当前科学探究过程中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一般承认,科学既具有客观性,同时也具有个别性和主观性的特征,两者都是科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并非不可解的矛盾。相反,正是科学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这种结合,使得科学在追求统一性和客观性的同时,具有自身独特的属性。
科学认识活动中主观性因素的存在无可怀疑,但并未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特征。诚然,在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每一项科学研究的成果都与个体的记忆和经验相关,并受到人的生理—心理结构的制约。因此,一个人选择并支持某一个科学假说的原因,可以是纯粹出自科学理性的考量,也可能是对某种理论形式的特殊爱好,或者只是一种简单的直觉,似乎无不由主观决定。然而,当他要提出某一假说时,却必须给出相应的证据支持以说明其真理性。正是这一与“事实”相关的“证据”,确保了科学的客观性。正像奥斯特瓦尔德在分析个体的主观经验与科学客观性之间的关系时所表明的:“概念总是具有依赖于个人的成分,或主观的成分。无论如何,这并不在于个人在经验中未发现的新颖部分做了添加,相反地,而在于在经验中已发现的东西中做了不同的选择。如果每个个人吸收了经验的所有部分,那么个人的或主观的差异便会消失。由于科学的经验努力吸收尽可能完备的经验,它经由尽可能众多和多样的记忆的搭配,通过力图补偿个人记忆的主观不足,把目标越来越接近地对准这一理想,从而尽可能多地填充经验中的主观间隙,使它们变成无害的东西。”[13]
科学的独特性是与个别性和主观性密切相关的。就科学与其他非科学认识活动的比较而言,科学独特性的主要意涵有三:一是科学是具有可检验性和客观真理性的知识体系;二是科学是以观察实验、归纳演绎为基本方法并辅以其他理性方法的;三是科学倡导实事求是、批判怀疑、开拓创新、理性实证、自由开放的精神和态度。就科学自身而言,科学的独特性意味着,科学虽然是以客观性的理想和规律性的探寻为基本追求的,但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是独特的,每一项科学成就也都是个体主观能动性自由充分发挥的创造性成果,都具有不同于其他科学理论的新颖性和创新性。
承认科学具有独特性,并不会因此而影响或排斥科学客观性的存在。个别性、主观性、独特性,在科学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科学的创造性或独创性。波兰尼借由科学的一致性观点将科学的独创性与严谨性结合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不和谐之处。他指出:“独创性是科学的主要德性,科学进步的革命性特征,其实乃是众所周知的东西。与此同时,科学又具有最紧密结合的职业传统;这种传统在学说的连续性方面,在协作精神的力量方面,可以比之于罗马教会和法律的职业。科学的严格,正与科学的激进主义一样地众所周知。科学既培养着最大限度的独创性,又强加着特殊程度的严格批判。”[14] 其实,科学的独创性是在与规律性的结合中实现个别性、主观性。独特性与普遍性、客观性的统一,推进着科学的发展。
巴伯力图表明,“在一切研究中,主观和客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一切领域中,都存在着主体的个人涉入;将具有普遍性的事件与独特的事件对立起来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任何概括都是从具体个人的个别性和整体性中抽象出来的。在客观性和个人涉入、规律性和独特性等问题上,我们既要避免实证主义所犯的错误,又要避免存在主义所犯的错误。“作为主体间可检验性的客观性不排斥个人涉入,而作为对特殊完形关注的独特性也不排斥对规律性模式的承认。主客体都有助于所有领域里的知识,而且所有事件都能看作是独特的或有规律的。”[16]
总之,不论是从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的角度,还是从基本立场来看,多元开放的科技哲学对于科学客观性与独特性的统一,都应持肯定态度。两者的结合,将成为推动科学进一步发展所遵循的重要原则。
在科学的知识特性这一问题上,普遍性与地方性是两个极端。传统观点强调科学是普遍的、统一的、完全的,以普遍性的追求为最终价值指向;当下许多研究却主张科学更具有地方性、个别性,并以地方性特征的探究为主要任务。如何在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科学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再则,由于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嬗变,普遍性与地方性的特征各自都严重影响到科学的文化定位,甚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造成深刻的断裂。
传统科学哲学强调科学的原理和程序是普遍有效的,地方性特征也可以从中演绎出来,地方性仅仅是产生特定结果的偶然因素;与之相反,科学实践哲学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诞生于实验室中的科学知识并不是普遍性的,它们被拓展到实验室之外也并非是对普遍规律的演绎运用,而是将一种地方性情境中的知识适用于新的地方性情境中。前者宣称科学认识的标准化和普遍有效性,拒斥其地方性;后者强调事实建构中必然包含地方性选择,不能排除实验室这一认识发生的环境场所的特殊性。
表面看来,普遍性与地方性这两种特性在科学中似乎是互斥的、不可共存的。但事实却非如此。
首先,科学的普遍性与地方性特征并不是互相冲突的。科学的普遍性只是强调科学规律的非个人性以及社会学层面的公平性。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科学知识,其中的地方性和差异性成分自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普遍性就是建立在地方性基础上的普遍性。这种“地方性的普遍性强调普遍性总是基于实践工作的,并且产生于地方化的协商过程和先前存在的体制的、基础的和物质的联系之中”。同时,“这一地方性的普遍性的实现,依赖于标准如何管理在转化工作实践的同时又以这些实践为基础之间的张力”。[17] 尽管科学的地方性不可避免且对于普遍性意义重大,却不能否认科学所具有的普遍性。因为,最后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的知识,是一种非情境性的理论表征系统,也就是是普遍性知识。科学反映了事实基础上的客观规律性,才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和理解,才能确保其普遍有效性。普遍性仍然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根本特征和内在秉性。
其次,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科学既具有其所产生的地方性,同时又是普遍性的。正如苏珊·哈克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在文化上是特殊的:现代科学在特定时间从世界中的特殊区域兴起,而科学要想繁荣,或者甚至想要持续生存,都需要合适种类的文化环境。然而……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斯宾格勒所想象的以及新犬儒主义者最近再次炒作的那样,仅是众多文化现象中的一种。因为科学仍然是普遍的——在很多意义上都不只是一种:它多多少少是由全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的探究能力的一种展示和放大;而且,恒久重要的科学发现也可以从地方性的、暂时性的文化努力中产生”[18]。这就是说,科学不仅是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产生环境的印迹,具有地域性的文化特征。在普遍性还是地方性间的确存在一种消长,这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而绝不是非此即彼。
而且,多元开放的科技哲学将习惯于正视普遍性与地方性的消长。如西斯蒙多所说:“大部分科学知识既是普遍的,又不是普遍的。人为的、抽象的科学知识并非牢固植根于特定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普遍的。理论知识面对的是理想化的世界;实验室知识的制造要能够祛情境化(decontextualized),能比较容易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科学知识的直接范围仅限于人工的、抽象的领域——它正是来自于这样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知识又不是普遍的,尽管总是有可能拓展。”[19] 普遍性的理想是科学之为科学的重要表征,但它并不否认各个地区和民族在发展科学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地方性及其意义;同样,科学具有地方性和局域性的特征,也不意味着要否认科学所追求的普遍性。
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科学相关领域的一个核心话题。在强调归纳和演绎逻辑的传统科学主义与强调非理性的非理性主义之间,对于理性及非理性二者的关系充满了争论。
从基本内涵来说,所谓科学中的理性,通常可以理解为人类通过自觉的逻辑思维把握客观世界规律的能力(理性思维能力),以及运用这种能力认识世界的活动。非理性则是与理性相反的一种能力和活动。所谓非理性,就一般的理解而言,一是指心理结构上的本能意识或无意识,二是指非逻辑的认识形式。前者如想象、情感、意志、信仰等,后者如直觉、灵感、顿悟等。作为心理现象,非理性既然是一种本能意识或无意识,那就是未经理性驾驭的,或不能进行确定的理性分析的。
从功能发挥的角度来说,理性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往往起着必不可少的、甚至是指导性的关键作用。这一点自然毫无疑问。然而,持非理性主义立场的观点则提出,由于理性只是一种消极的工具性的东西,自身并不具备积极能动的力量。没有情欲、本能和冲动的推动,理性就是一些僵死的形式,理性的活动必须仰仗非理性能量的加持。
对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传统的科学主义观点认为理性高于非理性,并将科学的理性方法绝对化,无条件地推广至各门非自然学科及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事实上却是在否定非理性方法在认识中的积极作用;相反,非理性主义的观点则坚持非理性高于理性,甚至将非理性方法绝对化,声称它是达到人和世界本质的惟一方法,却视理性方法为认识过程中的障碍因素。
事实上,就具体的科学认识过程而言,理性方法与非理性方法各有其特点,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也往往是共同发挥认识作用的。在现实的科学实践活动中,理性与非理性是相互协调、相互契合在一起的。
这种契合性首先表现在,理性与非理性从来就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因此,既没有纯粹的理性,也不可能有纯粹的非理性。在具体的认识过程中,理性因素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非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的形成与发展又有赖于理性因素,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以直觉为例。科学认识中的直觉是认识从事实到经验,从经验到理论的思维方法,与人的感性和人的理性直接相联系,借助于理性而形成。这是一种非神秘性的、与事实及人的现实心理活动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其中包括感性的直觉和理性的直觉。感性的直觉是对理论的直接经验,与理论选择相关;理性的直觉作为理论的创造性活动,是对逻辑元素之间的秩序、关系的直觉,既具逻辑性,又有综合性与有意识性。也正因如此,作为非理性因素的直觉也常常会被归入理性的行列。
此外,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二者的契合还更多表现在具体科学活动中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方面。
一方面,理性因素作用的实现有赖于非理性因素的参与。这不仅体现为信念、激情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为理性保持其方向提供了价值信念的力量和心理支撑作用,更体现为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为理性提供动力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科学家获得新知识,并不单纯靠逻辑性和客观性,巧辩、宣传、个人成见之类的非理性因素也起了作用。科学不应被视为社会中理性的卫士,而只是其文化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21] 。
另一方面,非理性因素的实现也有赖于理性因素的作用发挥。就意志、信仰、信念等非理性因素而言,任何此类因素要在人的活动中有效发挥作用,就必须借助于理性来为其规定目标和方向,并以理性的形式表达出来。
当然,不可否认,“认知,在理性领域和非理性领域会有很大的区别,但我们不应当拒绝对非理性领域的探索,探索非理性领域的学问并不都是非理性的,探索理性的领域的学说倒有不少是非理性的”[22]。理性与非理性从来就不是截然分离的,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常常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二者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科学过程中逻辑与非逻辑、理性与非理性等不同思维方式的契合,共同推进了科学认识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在科学从兴起到成长的过程中,“理性”是贯彻始终的一个概念。从理性精神的觉醒,到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承认、肯定与张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的整个过程,甚至决定着科学未来的命运。然而,当科学的迅猛发展造成的理性分裂导致了工具理性的彰显与价值理性的衰微,非理性主义的思潮也乘机闯了进来,理性就面临极大的考验。因此,科学作为理性的主要表现,它的健康发展首先就是要在理性与非理性、工具与价值、科技与人文之间找寻并保持适当的张力。
所谓“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实践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并以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诉求,以功利作为评判标准的考量。由于科学特别是技术常常能帮助人们实现功利的目标,技术价值也被一些人用作工具理性的代名词。过去两个世纪,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意义的价值观,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
所谓“价值理性”,是指与工具理性对立的某种考量,是有意识地对某个特定行为的固有价值,抱持无条件的纯粹信仰。也就是说,人们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无论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目的,还是责任的、荣誉的、忠诚的目的。 “价值理性”是行为人只注重行为本身所代表的价值,例如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不在意行为的手段和后果。无疑,价值理性是要从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待行为的合理性。
随着启蒙运动所肇始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迅速发展,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并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造成价值理性的衰微和人的价值的失落。“现代人迷惑于实证科学造就的繁荣”,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最终“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人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遮蔽了人本身存在的意义”。[23] 在韦伯看来,“我们,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24]。
理性分裂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以及工具理性相对于价值理性的僭越与遮蔽,使得科学技术成为现代人的一个新的神话,但最终却引发了科学的危机,人们再次陷入精神的困窘之中。
在社会生产领域,人从生产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沦落为可资利用和算计的客体,沦落为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体制中的附属品。人的主体地位丧失了,并逐渐被异化为“单向度的人”;在文化领域,实证主义方法被任意推广为一种普遍方法,人文等学科领域则被排除到“科学”之外。由此,工具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理性的独断导致文化的单一与贫乏。
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化趋势的日益加强,科学价值也更多转向对工具理性的关注,科学渐渐丧失了其人道的传统。于是,对科学理性的种种质疑与批评声浪,就在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对抗中显现出来。
然而,作为人类理性中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工具理性注重“是”,是对现实存在东西的把握,以合规律性为标准,追求的是“真”;价值理性以“应当”为依归,是对理想状态的追求,以合目的性为标准,追求的是“善”和“美”。价值理性确定目的,而工具理性达成目的,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精神动力,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现实支撑,二者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中。
应该明确,不要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当作对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价值观进行调和。关键是要批判工具主义片面张扬的霸权主义价值观,认真防止其可能的风险,寻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联,确立一种足以驾御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将世界引入人性化的发展轨道。
当然,若要从根本上改变工具理性的僭越所带来的人类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实现价值理性的复归与人的意义的回归,就要改变以往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关系上的态度和原则,进而在具体的行为中达到工具性考量与价值性考量的和谐一致。
四、开放的科技哲学的互动目标
人类文化是由多元文化形态共同构成的一个文化整体,而科学是其中现代文化形态的一种。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最富有物质力量的文化形态,科学并非单一地存在于整个社会中,而是与其他各种非科学的文化形态共存。科学审度着眼于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交流与互补,提倡一种开放的科技哲学。通过科学与伦理、科学与艺术、科学与信仰,也即科学与人文之间所展现出来的互动与融合趋势,实现求真、向善、臻美、达圣之圆融。
(一)科学与伦理、艺术、信仰的互动
科学与伦理互动以向善。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原本是用来增进人类健康与福利,促进社会进步并提高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但却并未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总是带来“善”,而是也带来 “恶”。科技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最终还要取决于运用科学的人。科技伦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25]
因此,人类应该有一种道德的自觉,从伦理道德层面对科技活动进行反思。科技的发展应该更多地关注人本身,实现科技的人性化,这是未来的必然方向。
科学伦理体现了科学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批判等科学精神。在这里,宽容是必不可少的,其具体表现为:一是在未知的探索过程中,面对曲折与不可预期的结果,以一种宽容的态度看待难免的错误与失败;二是允许科学研究中不同意见的存在,为不同的学术观点提供自由争鸣的空间,体现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三是尊重科学之外的其他文化,允许不同文化形式并存。诚如萨顿所说:“没有宽容和慈善精神,我们的文明,无论它现在是怎样的,都是非常不稳固的。对于人类文明来说,科学是必需的,但只有它却是很不够的”[26]。
作为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家除了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意识外,还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确保科学在为人类谋福利的同时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科学的向善精神对科学家的基本要求。[27]
科学与艺术互动以臻美。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艺术在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指导下一度完美结合,曾经描绘出一幅壮丽的文化图景。其最佳体现,就是当时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意大利的达·芬奇,他不但以传世名画“蒙娜丽莎”闻名,亦是人体解剖学和建筑工程学的开创者之一;不但是艺术家,还是哲学家和科学家。
文艺复兴以后,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过程的专业化,也导致科学技术的学科越分越细,科学与艺术因而分离为两种不同的人类认知形式,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出现了对立的局面。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当代科学与艺术之间又表现出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统一趋向。不止艺术越来越多利用科技的成果,以更新的含义和内容、更广阔的视野和观点展现自己;科学也日益赋予自身以更多艺术化的美感追求。
科学与艺术走向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们虽然各有特点、各有风格、各有其专门的目标和价值,但二者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严格分立的。如李政道所说:“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是同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相联的。对艺术的美学鉴赏和对科学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随后的感受升华与情感又是分不开的……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的,两者都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普遍性一定植根于自然,而对自然的探索则是人类创造性的最崇高的表现。事实上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科学与艺术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而富有意义”。[28]
在科学与艺术的融合中,科学家将不只用数字、公式,也用隐喻、类比的方法形象地描写自然;艺术家不只偏爱色彩、形态,也会探索由各种信息、公式组成的世界,创造更富有想象力、更美好的生存方式和空间。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艺术与科学的交融,成为新世纪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主流。
科学与信仰互动以达圣。科技与理性极大地提升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明。但另一方面,却是人类在精神领域对自身生存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迷茫,以及在生存领域由于自然生态被破坏、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丛生所带来的危机意识。迫切需要精神上的依托来满足人类的精神追求,为那些迷失在物质盛宴中的孤独旅人找到存在的意义,更为那些难以安身立命、无所依归的人找到安全感。这就为信仰(超越性,包括健康宗教)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科学与宗教之间是存在对话基础的。著名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指出:“当科学与宗教之间发生冲突时,我们应当等待,但却不应当被动地或失望地等待。冲突仅是一种征兆,它说明了还有更宽广的真理和更美好的前景,在那里,更深刻的宗教和更精微的科学将相互调和起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来,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事,可是人们把它强调得过分了。如果仅是逻辑上的冲突,便只要加以调和就够了,可能双方的变化都不会太大。我们必须记住,宗教和科学所处理的事情性质各不相同。科学所从事的是观察某些控制物理现象的一般条件,而宗教则完全沉浸于道德与美学价值的玄思之中。”[29]
可以说,超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走向对话,积极寻求在现代科技背景下的合作,已成为科学与宗教间关系的主要趋向。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并倡导一种新人文主义,也即强调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复兴以及建立人性化的科学。
一些科学家早就认识到科学与人文在观念上的互补性,自觉地对所研究的自然科学进行人文思考,积极推进科学与人文的互动。怀特海就曾积极探究数学与善的内在一致性,并撰文指出,数学和善的追求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追求的是同样一件东西,即理性的完善。爱因斯坦从自己所探索的自然规律的和谐中既看到了最深奥的理性,也体悟了最灿烂的美,由此产生了包括敬畏、谦卑、狂喜和惊奇等在内的丰富感情,达到了类似宗教境界的那种感情。
总的来看,在如何解决两种文化的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达成共识,即通过科学与人文的互动与融合来从根本上解决科学与人文间的对立。让科学与其他文化在一种自由、平等、开放的氛围中和平共处,将是人类文化未来整体性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本要求。
(二)求真向善臻美达圣之圆融
科技审度论认为,在多元开放的科技哲学中,应当确认,真善美圣都是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作为科学价值追求的不同层面,真善美圣分别体现科学的认知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与信仰价值,也表明科学精神的内在统一。求真奠定科学认知方式的知识本性,向善确保科学的道德规定性,臻美提升科学理论在形式上的和谐完美,达圣赋予科学不断升华的超越性。
科学首先是求真的。真理性是科学的根本属性,也是科学首要的基本价值。善是对科技的价值评判。科学最终是要导向善的,科学求真的目的,最终就是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善。美是科学的精神向往,简单与和谐的理念往往指引着科学探索的路径;美的追求又能够推进对真的发现。“一个科学家凭异常高超的审美直觉提出的理论即使起初看起来不对,终究能够证明是真的。”[30]
圣是真善美的统一,是人类在求得科学之真、伦理之善、艺术之美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的精神提升和情感升华。科学家通过探索自然的求真活动,深刻领略到宇宙自然的和谐与秩序;在向善的引导下,体认到生命的意义和科技中的人文关怀;在美的追求中,使人的灵魂与情感得以净化,传达出一种超然的情怀。正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使科学日益趋向达圣的崇高境界。圣乃是一种最高的“完满”,超越俗世而趋向一个理想化的世界。
真善美圣的和谐统一,体现在科学活动中多元价值取向的内在统一性上,也表明科学探索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不同层面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真善美圣的和谐统一,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也是科学充分发挥其文化功能所必需的一种理想境界!
近代科学的发展源于科学的两个历史根源——技术传统与精神传统[31],当时,科学的基本价值趋向主要是求真和功利性追求。然而,当代真正“科学的力量和慰藉在于充满希望地负责任地行使实现和偶尔满足好奇心的能力,在于科学可能为灵魂提供的服务——这多于任何事物”[32]。因而,一种多元开放的科技哲学,不能在科学活动中过分强调功利性追求,更不能忽略科学中向善、臻美与达圣的维度。功利化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造成了人的异化以及科技的非人性化,使科学背离其作为一种先进文化所富有的积极意蕴。
从价值追求的角度来看,求真向善臻美达圣之圆融,乃是多元开放的科技哲学追求的目标。
Reconsid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ding to Pluralism and Openness
LIU Dachun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basic orient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how to tre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first is scientism, which tries to explain why science is reasonable and is marked by a defense of science; the second is anti-scientism, which is a critic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enounces it as posing great risks to the world today. This paper tries to argue that both mere defense and mere criticism have limitations and that a reconsideration attitude toward science should be adopted. The examination of Marx's analysi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s it contains rich content and adopts a unique historical-practical perspective, providing an important benchmark for reconsid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proposed a theory of reconsiderat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ocates a pluralistic and complementary value choice that maintains an appropriate tension between objectivity and uniqueness, universality and locality,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The pluralistic and ope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dedicat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nity of seeking truth, goodness, beauty, and holines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science and art, and science and faith, that is,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Key words: Scientism; Anti-scientism; Reconsid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uralistic and complementary; Unity of seeking truth, goodness, beauty and ho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