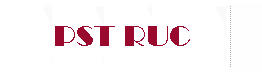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编者按】中国自古就有高度发达的技术文明。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走过了由师夷长技、科学救国、科学报国、科教兴国至科技强国的现代科技发展之路。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技术创新、工程建设和科技应用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为技术哲学带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回望来路,中国的技术哲学秉承了马克思的科技思想与恩格斯开创的自然辩证法传统,又以开放的态度引入了欧美的技术哲学思想;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得整个社会对于技术与工程的哲学、伦理和社会研究的需求空前高涨,技术哲学正在成为科技时代的“第一哲学”。
在此进程中,中国的技术哲学与中国科技一样,曾经将引进和追踪作为非常重要的发展策略,但中国的技术哲学家也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中国特定的制度和文化使其在工程建设和科技应用领域呈现出较先发展国家更高的发展速度。同时,中国社会对科技创新持乐观的态度,这既使中国的技术哲学必然要逐渐形成本土特色,又难免在追踪西方技术哲学的各种转向过程中迷失方向。这种由科技时代的加速度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张力促使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不论是西方的科技反思与批判,还是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与价值转向,都有其文化价值语境和社会实践脉络。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中国的社会环境、文化精神和制度架构,弘扬中国经世致用的思想和执中权衡的智慧,走向对科技时代的实践审度。
卡尔·米切姆是国际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领域的开创者,近三十年来他在推动中外技术哲学交流和技术哲学人才培养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他最初以西方技术哲学权威的身份受邀来中国,但由于他一直对西方技术和西方技术哲学保持着批判的立场,对美国文化持有一贯的反思态度,这使他较其他西方学者更愿意向中国学习,更乐于与中国的技术哲学家和工程哲学家交流思想,也为中国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的成果和人才走向世界作了很多具体的工作。在全球化遭遇地缘政治冲突的当下,米切姆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试图从东西思想相互推参和交相启发的维度出发,由西方“大技术哲学”与批判的技术哲学的式微出发,对东方技术哲学中批判的阙如发出了既委婉又不失焦点的“怀疑”,并以“不确定”表达了东方式的谦虚。
哲学是对时代精神不失时机的捕捉和创构。一个外国同行的提问自然需要由中国的技术哲学家作出回应与思考。王国豫结合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对米切姆有关技术哲学研究的“大问题”和“小问题”的观点作出了解读与回应。陈凡在历史回顾的基础上回应了米切姆关于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特点的评述,探讨了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李伯聪指出,“工程哲学中国学派”在工程哲学这个新学科在国内外兴起的过程中发出了“中国声音”,作出了“中国贡献”,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应走向“哲学的中心区域”。王前指出,在发展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技术哲学时,应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现代中国技术实践的哲学反思”和“与国外技术哲学的对话与融通”等方面入手。刘永谋认为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中国问题、中国语境和中国营养,并以“对技术治理的审度”为例探讨了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问题。王小伟对青年学者在技术哲学领域的国际化努力作了全景式扫描与评价,提出技术哲学应坚持以审度的态度反思技术。段伟文指出,面对深度科技化时代,中国具有引领世界的历史机遇,中国技术哲学必须重新定位,为科技找到一种兼具科技创造与人文观照的稳健智慧之道。
技术时代,哲学何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中国科技日渐走向世界前沿的过程中,既要勇闯无人区,又要善闯无人区,不论是在观念、方法还是价值等层面,都将给中国的技术哲学提出越来越多的难题与挑战,而这也给新时代的技术哲学发展带来了全面进击的大好机遇。
卡尔·米切姆: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应重视批判性
王国豫:技术哲学的“大问题”和“小问题”——对米切姆“怀疑”的回应
陈凡、陈佳:技术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学派的研究纲领
李伯聪:工程哲学:回顾与展望
王前: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
刘永谋:技术治理与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
王小伟:中国技术哲学的国际化思考
段伟文:深度科技化与中国技术哲学的未来之路
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应重视批判性
卡尔·米切姆(中国人民大学、科罗拉多矿业大学)/文
王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与中国同行共同见证了欧美技术哲学进入中国的过程。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在观察由此发展而来的中国特色的西方技术哲学时,实际上对此持有某种难以名状的“怀疑的”态度——当然,将这一态度判释为“怀疑的”可能又未必确切。因为在想到“怀疑的”之前,我曾尝试用过“不满意的”或“不自在的”,但总觉得这些词语都未必完全准确。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亦可说我想表达的是一种“反美”的情绪。总之,我找不到“确定的”正确表达,也许它本身就是“不确定的”。
为了廓清我思虑的出发点和目的,让我先将结论和盘托出:由于对欧美技术哲学感到不满,我倾向于怀疑中国学界是否真正为之所吸引。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技术哲学家有时受到包括我在内的西方技术哲学家之不恰当和不必要的影响,或是对他们太过“恭顺”。因此,我对我此处的观点深感矛盾。我不太确定中国的学者们是否应该认同我的观点,反过来倒是觉得,我应该倾听中国同行的声音,了解他们对此的态度。不仅如此,我还应该告诉其他美国同行,他们同样需要倾听——而这是值得的。概言之,作为一个美国同行,我对中国特色的西方技术哲学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让我来尝试解释一下我何以持有如此立场。反思这一心路历程,我当初来中国工作时所持的并不是这样的观点。当然,我希望我这番自传式的或自省式的哲学自我批评不至于太过“矫情”。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迈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过去的二三千年间,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不计其数且影响深远,包括中国人与印度佛教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展开接触,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传教士出访明朝,以及新文化运动,等等。改革开放则是中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之间展开的更深层次的交流,这种交流领域广泛且持续不断。
反观美国人在接触中国时的态度则显得肤浅得多,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单薄,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美国只有不到三百年历史,致使其本土文化阙如。美国文化要想像中国一样追根溯源,就必须穿越欧洲,回溯到雅典与耶路撒冷,重温理性与启示的对立,以及各种启示之间的激烈冲突。对美国而言,儒释道之间和谐互补的思想是完全陌生的。
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是建立在傲慢与忐忑相杂糅之基础上的:一方面是一种美国“例外论”的傲慢信念,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对“例外论”的忐忑、不确定和质疑。我自身与中国的接触就是属于忐忑与不确定的第二种类型。我认同诗人庞德(Ezra Pound)的观点,尤其是他希望被亚洲改变的朴素愿望,即以亚洲作为方法——尽管他以一种滑稽而典型的美国式失败而收场。现在,我意识到,我不是一个要将基督教义或美国主义带来中国的传教士,我来中国是为了学习。
但起初并非如此。我之所以来中国是因为中国学者先走近我,想从我这里学习。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殷登祥研究员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作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项目的访问学者,恰逢我担任该项目的负责人。1992年,殷登祥邀请我与另一位同事斯蒂芬·卡特克里夫(Stephen Cutcliffe,来自理海大学STS项目)到中国讲学。
可见,我来中国的初衷不是为了学习,而是因为我被“恭维”了。当时我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因为我也是有那么一点自大。一个人想要摆脱源自美式傲慢的无缘由自大,的确不容易。
二
技术哲学是跨学科的STS研究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自己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源于一种对美式世界观的不满,这令我转而依赖并致力于对现代科学、工程和技术进行批判与控诉的世界观。
自18世纪创立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将科学技术作为其自我构想的“例外论”的一部分。1949年1月,在第一次给我留下印象的美国总统就职演讲中,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在与苏联冷战伊始就明确将技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用他的话说,美国(除了支持联合国、欧洲重建以及北约之外)必须着手实施一项大胆的新计划,使(美国的)科学进步与工业发展施惠于不发达地区的改善和发展,以此来替代共产主义。
毋庸置疑,美国技术哲学的创立基于一种激进的亲技术意识形态,与基督教新教、资本主义和军事等方方面面因素相关联,并与激进的个人自由主义互通款曲。正由于此,从我开始意识到它固有的破坏性特征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尝试反对它。对于能读到1946年约翰·何塞(John Hersey)在《纽约客》上关于广岛原子弹爆炸报道的人而言,杜鲁门1949年的演讲所具有的强烈反讽意味暴露无遗——这颗“原子弹”正是杜鲁门下令投掷的。
1992年,当我首次来到中国时,我认为中国比我自己的故土及其文化更善于接受我对工程和技术所提出的批判。正如不止一位中国学者温和地批评我一样,我曾有过将中国浪漫化的倾向。我在体验一种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谓的“东方主义”,将一种不能实现的、从美国式的故意盲目中的逃离,投射于中国这个“他者”之上。然而,我在中国技术哲学领域却发现了一种与“东方主义”相对的“西方主义”,它同样将自己的一些浪漫幻觉投射于美国之上。用混沌理论的语言说,美国主义甚至在特朗普政权的混乱之中,作为复杂的全球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奇异吸引子”发挥着作用。
反观我的浪漫主义与东方主义,其实也无异于一种傲慢。我认为中国可以从一种肤浅的、自我放纵的反文化中学习技术哲学理论,这种文化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西方并且此后我也认同了这种文化。我甚至臆想中国正在通过学习来避免西方的错误,并为技术哲学规划另一条道路。
然而,吊诡的是,我却逐渐地、不情愿地从中国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对技术内在吸引力的欣赏,尤其是为什么在1850—1950年这狂暴而紊乱的一百年间,技术对美国人来说如此有吸引力。诚如中国哲学家李泽厚所言,正是这样一种吸引力在美国文化中沉淀下来;或者用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美国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的话来说,将其希望注入到当代生活的特征之中——我的老师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称之为“适得其反(counterproductivity)”。
来到中国之初,我发现自己仿佛回到了科技的英雄时代,目睹它发挥着各种指挥棒的作用——较之美国英雄时代的情形,这种作用与战争、暴力和破坏有明显区别。美国的技术可谓劣迹斑斑:从屠杀土著居民、奴役非洲人、窃取墨西哥和西班牙领土,到对德国、日本和越南进行地毯式轰炸,污染环境,并率先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在中国,技术在将国家从殖民帝国主义中解救出来并使数亿人民摆脱贫困方面,扮演了一个并不那么咄咄逼人的角色——尽管技术满怀希望的承诺并不能完全摆脱它们自身的阴暗面。
三
我首次到访中国,是作为一个焦躁的、不安的美国人来到这里的。在访问中国之前,20世纪70年代我被西班牙和西班牙天主教文化所吸引,认为这是与美国人的肤浅和消费主义相反的榜样。我曾以为,通过西班牙才能与现代技术出现之前更深厚的文化遗产相联系。因此,在来中国之前,我并不热爱中国,也不那么想访问中国。但是在随后的近三十年中,我逐渐变得越来越挑剔——不仅仅针对天主教,更是对启示和理性的整个亚伯拉罕传统。我渐渐地爱上了中国文化,因为与中国相比,甚至西班牙的过去也很浅薄。回首近三十年与中国的相遇,远者要感谢殷登祥第一次说服我来到中国,近者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在过去五年中为我提供了一个在中国的学术之家。
四
美国的技术哲学可以用简单明了的术语加以描述,即体现了两种传统。我将其称为主流的亲技术传统和非主流的对立(counter)或怀疑的(如果不是“反技术[anti-technology]”)传统。
亲技术立场自身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技术直接明了、大张旗鼓的赞誉;另一种是相对较为间接的、平静的接受技术立场,如同许多分析哲学那样,关注小问题而远离大问题。
自由与知情同意、人权、风险-成本-收益分析、科研诚信、隐私以及利益冲突,涉及这些问题的技术伦理都是技术哲学在细微方面的一个分支,尽管其倾向于保持现状基本不变,但不代表其完全没有价值。只是这种技术哲学进路试图将产生机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设计进机器——甚至可以认为,它为工程与技术创造了框架,这些工程与技术已经改变并正继续改变自然和人类世界。
“批判传统”在文学和诗歌中与在专业哲学中一样多,并且趋向于涉入更大的视野。这正是我所谓的“大的技术哲学”,因为它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观点:现代技术作为一个整体(也许可以用大写的“T”来表示)需要进行反思性和批判性评估。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诸如核武器或计算机等特定技术的文化共建,或者是个人技术如何必须被用于规避风险与公平分配利益,而且包括面对技术日益显现出来的“接管与殖民人类生活世界”的端倪,我们该如何思考和应对技术,将这个世界改造成一个科技-生活世界,用技术-人类条件来替代人的条件,造就“人类世”。我们必须承认,“大的技术哲学”基本上是一种无能的哲学,比其更小(但不是更年轻)的“兄弟姐妹”更无能为力。
美国亲技术传统在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那里找到了它的奠基者,并或多或少地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唐·伊德(Don Ihde)等人的研究中得以延续。
美国批判技术传统则从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经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直到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伊万·伊里奇、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阿尔伯特·伯格曼以及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
我可以举个例子补充说明。在欧洲,曾经如此深厚的批判技术哲学传统,倘若不能减少其修辞的复杂性,最终很可能趋于消亡。究其原因,恰因其无法在实践中取得多少成效,它只能在更具文化和讽刺意味的复述中炫耀自己。
鉴于我对于大的、批判性的技术哲学研究传统的认同,当中国的技术哲学家们似乎对小的、亲技术的哲学进路更感兴趣时,我很自然地生出些许不安。相较于伊里奇或者伯格曼而言,杜威和伊德的作品被更多地翻译成中文。从经典大技术哲学的欧洲版本来看,只有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一篇短文被译为中文。
五
现在到了最困难的部分,即我对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亲技术的技术哲学深感不满的理由是什么?令我对此感到遗憾的是否是它的全球吸引力?若无个人主义的假设,我基于什么理由来质疑它富有魅力的感召——并邀请中国学者和学生也来质疑它?如果说我的人生从根本上被我的“亲华”以及被中国的哲学热情所改变,那么是否应由我去质疑它们给“亲美”或“亲欧”的中国学者带来的潜在利益呢?
况且,在一个拥有超过三千所学院、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国家里,谈论某些诸如“中国特色的西方技术哲学”的事情,难道不是可以推定的吗?就好像在这一学术领域内存在某种统一的、本质主义的中国视角?
对于以上这些难题,我并没有答案,但解惑的工作仍在我的哲学生活中蹒跚前行——目前我可以先承认我的不确定性。不过,至少在“是否可以推定”这一棘手的问题上,我暂时能够采用两种办法来寻求某些更为牢靠的东西。
其一,我将自己的主要受众想象为我生于斯但已疏远的欧美学术共同体。对于这些听众,我尝试去阐释我所学到的与从中国学来的东西——在此之前要承认我没有真正理解中国或者说中国的文化与哲学,很可能对我所学的东西存在误解。除了被我所见之中国哲学好的一面所吸引,我还试图认识它不好的一面,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
其二,针对第二类受众(即中国学者),我与他们分享自己与欧美哲学家的争论,并邀请他们批评和质疑我的解读。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偶尔听闻时显得非常大度,他们只是在特定情境下才反驳我那些经常流于天真的想法和浅见。当然,我也致力于尝试通过向欧美受众传播中国学者研究的方式,来帮助我的中国同事和学生与国外学界保持交流与互动。
六
但真正的难题在于我的判断,即认为小的、亲技术的技术哲学存在根本性的问题。
在美国(以及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持亲技术立场的技术哲学思维的基本错误,在于它完全无视技术生活世界的脆弱性。这很难争辩与辩护,因为它违背了心理-历史的潮流,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星球上人类宜居地迫在眉睫的生存风险的经验性评估。问题不仅是气候变化,还有从核扩散、全球化学污染到生物多样性丧失、疾病与病毒传播、人工智能的算法不透明、经济不平等、社会的无知与不稳定等诸多威胁——以及将创新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普遍方法的草率呼吁。这被我的同事让-皮埃尔·杜普伊(Jean-Pierre Dupuy)称为“启示的末日论(Enlightened Doomsaying)”的做法,和现在一样,它常常招致维特根斯式的批评:它只是言说而不显示(Itonly says instead of shows)。这可能也是错误的。任何末日论不仅属于卡珊德拉[1]的命运,而且是一个悖论——如果它实现了,就被证明是错误的。所有关于历史的信仰都是易错的。
我将“身处其中而重新发现自己的情形(我认为我们在其中都能发现自己)”视为一种“公案(koan)”。技术与可居住世界日益逼近的毁灭是一个“公案”。现在的问题不是“一只手拍出的响声是什么”,而是对于所有引导我们走向悬崖的信念而言,“两只手拍出的响声是什么”。[2]
注释:
[1]译者注:卡珊德拉是古希腊神话人物,能够预见未来和灾难。
[2]译者注:指的是禅宗意义上的“公案”。此处的“公案”为日本临济宗的白隐慧鹤禅师所创,即两手相拍,自然发声,为凡夫所耳闻;然仅扬只手,无声无响,若非心耳,不可得闻。
技术哲学的“大问题”和“小问题”
——对米切姆“怀疑”的回应
王国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是一位真诚的学者。他的真诚不仅体现在他对他人的以诚相待,也体现在他对事业的真诚。他对“中国特色的西方技术哲学”所持的“怀疑”态度就是他真诚的体现。在其近乎反省式的关于技术哲学的思考中,米切姆通过反思自己(包括在中国)从事技术哲学的心路历程,婉转地提出了对中国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研究现状的批评。他指出,一方面,中国的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充满了对美国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的“浪漫主义”想象;另一方面,中国技术哲学“亲技术”的特征表现在其对涉及人类命运的宏大问题缺乏深度思考和回应。他坦率地将自己的疑惑和怀疑表达出来,期待中国学者的回应。本文试图对米切姆的“怀疑”提出一点看法。
一
米切姆将美国的技术哲学传统分为两种:“亲技术”的传统和“反技术”(或怀疑论)的传统。而“亲技术”的传统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技术的直接赞誉,一种是对技术的婉转批评。后者的特点是“关注小问题而远离大问题”。在米切姆看来,要解决现代技术的伦理问题,就必须将现代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和批判性评估”,即从根本上抛弃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在其框架下进行修修补补。因此,他对中国技术哲学热衷于研究“亲技术”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唐·伊德(Don Ihde)感到有点失望,倾向于回到从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到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再到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伊万·伊里奇(Ivan Iuich)、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以及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批判传统。
所谓“小问题”,在米切姆看来是诸如自由与知情同意、人权、风险-成本-收益分析、科研诚信、隐私及利益冲突等问题。米切姆认为,考虑这些问题并非完全没有价值。但这样一种技术哲学只是试图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设计重新注入机器,而恰恰是这些意识形态创造了工程与技术的框架,改变并正继续改变着自然和人类世界。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实现,现代技术所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归根结底也就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米切姆担心“小的、亲技术的”技术哲学忽视了“生活世界的脆弱性”这一根本性问题,因此他主张对技术从整体上进行批判性审思,从根本上思考“技术是如何将人的生存环境改造成技术-人的生存环境”这一大问题的。
米切姆的这一思考凸显了他作为一个关注人类命运的学者的危机感和责任心。这些问题不仅是技术哲学应该反思的,也是技术时代整个哲学应该反思的。当今世界,一方面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已经在某些方面显示了其难以控制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人类对技术未知的探求还在不断打破自然所构建的边界,创新速度在国与国的竞争中不断升级和加快。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样的技术语境中早已经忘记,不是我们在建构技术,而实际上是我们在被技术所规训——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框架。
然而事实上,技术哲学从来未缺失批判传统。由马克思开启的社会批判传统,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已经转化为对技术的工具理性的批判。米切姆特别提到的马尔库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马尔库塞那里,对社会的批判使他转向对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的批判。马尔库塞认为,“技术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作体系,并创造了一些生活(和权力)方式”[1],“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2]。“以技术为中介,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吞没或抵制一切替代品。这个体系的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稳定了这个社会,并把技术的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3]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一样,马尔库塞同样认为,正是启蒙运动以来的技术理性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导致了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对技术从宏观视角进行批判的哲学家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阿伦特从技术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角度,指出了技术本身的内在破坏性。在她看来,制造人工物的活动过程是一种暴力过程。人从自然中“夺取”材料,而“夺取”本身就是对生命过程的“扼杀”,它打断了某个自然的缓慢进程,“如为了夺取木头我们就要砍树”,或者“从地球子宫里夺走铁、石头或大理石”[4]。因此,对技术与自然和谐的任何幻想都是不现实的。在阿伦特看来,“技艺人、人造物的创造者,始终都是一个自然的破坏者”[5]。而京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更进一步认为,人对技术过分乐观,“技术必然带来进步”只是一种幻象,尤其是在核技术出现后,人类彻底无法驾驭自己的产品,科技的进步蕴含着灭绝人类的危险。他把人看不到这一点称为“世界末日失明症”[6]。
值得思考的是,尽管欧洲存在着这么强大的技术批判传统,为什么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欧洲走下去?反而是米切姆所指出的关注“小问题”的技术哲学越来越盛行?无论是近年来以荷兰学派为代表的“道德物化理论”,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技术的“价值设计论”,抑或欧盟提出的“负责任创新”,其实都是试图在自由主义框架下对技术活动及其潜在的负面后果进行校正、调节,或者在源头上进行适当的干预,而没有走向米切姆所推崇的、梭罗所实践的极简的生活方式。梭罗所主张的浪漫主义将技术发明看作“漂亮的玩具”,认为许多“现代化的进步设施”并不总是有肯定的进步,却容易导致人们对它们产生幻想,“使我们离开了严肃的事物”,导致我们忘记了生活的目的[7]。同样是浪漫派的诺瓦利斯(Novalis)甚至认为现代人忘记了自己的内心,疲于追逐外界事物,不但不能认识世界,反使世界物质化和对象化,把活生生的有机体肢解为可利用的材料[8]。因此,他主张回归自然,回到前现代的“黄金时代”。
但我们不仅没有回到“黄金时代”,反而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生活。显然,这一切有更深的根源。如果我们理性地看待技术,就不得不承认技术的“初心”是为了美好生活。而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本能,就像向往自然的生活同样根源于我们与大自然割舍不断的心理联系一样。阿伦特认为,对于人类而言,改造自然的暴力过程不仅可以从其成果的物质稳定性和安全性一面得到辩护,而且还可以帮助人获得一种内心的满足感,并成为人的“整个生活中自信的源泉”[9]。也就是说,技术在人的自我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普莱斯纳(H. Plessner)将人这样的存在形式称为“自然的人工性(natürliche Künstlichkeit)”[10]。“由于人被迫按照它的存在形式生活”,所以“他需要一个非自然的、非生长方式的补充。因此他的人工性是自然的、出于他本身生存形式的需要”。[11]为此,人必须不断地创造。一方面,人借助于自己创造的非自然的人工物品,并非为了从自然中解脱出来,而是为了塑造和获得与自然的平衡;另一方面,人借助于自己创造的人工产品,得以走出自己的中心定位的封闭性,进而面对世界的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技术的根本性否定不仅在现实中没有可能性,在哲学上也缺乏可以辩护的形而上学基础。
二
毋庸讳言,一方面,中国的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受西方影响至深,这也是历史注定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不仅使得中国和世界的经济与科学技术交往加快加深,也打开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看世界的大门。20世纪80年代起,技术伦理学在引入西方现代伦理学及科技哲学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兴起。中国学者开始大量翻译和引进西方原著和理论思潮,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的学科建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这对中国当代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亲技术”的技术哲学也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和文化基础。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人们相信,落后就要挨打,而科学技术可以振兴中国,解决贫困问题。许多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技术的负面效应,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还没有遇到。技术哲学首先面对的是如何营造一个适合于技术创新的文化问题,而不是相反。我们曾经以“纳米技术的公众认知”为题,选取大连为基点进行过调查。调查的结果是,针对纳米技术的潜在风险,虽然也有公众表达过担忧,但98%的公众还是支持纳米技术的发展,这一数字远远高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我们也对其中的原因进行过初步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一结果与公众对科学和技术的信念呈正相关性。我称之为“文化的鲁棒性(culture robustness)”[12]。
随着中国经济和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包括环境问题)逐渐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2000年以来,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公共媒体,关于技术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技术哲学也明显地呈现出伦理转向的趋势。实际上,在技术伦理学的研究路径问题上,中国学界和国际学界一样也存在两种取向:一是追随着批判哲学传统,从理论层面对现代科技采取一种批判和质疑的态度,追问什么是“好的技术”,什么样的技术活动在伦理上是可以得到辩护的,进而探索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原则。另一条路径则是从现有的规范伦理学原则出发,对具体技术比如核技术中的安全与风险、基因工程对人性的干预与物种伦理、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中的隐私问题、数字鸿沟等进行审视,分析其对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等原则发起的挑战。但绝大部分学者在对待技术的态度上采取的还是“中道”,即并不否定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也很少有像米切姆论及的“启示的末日论”的哀叹,而是更强调对技术从研发到应用和后处理的各个环节进行实践层面的规范,呼吁负责任地发展技术和创新技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和从伊德到维贝克(Peter-Paul Vereek)的技术调节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正好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相吻合,因而也比较容易被接受和欢迎。这恐怕也是为什么米切姆感觉中国学者对“亲技术”的“小问题”比较关注的一个原因吧。
事实上,我想强调的是,也许恰恰是这种基于“中庸之道”的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可以使人类摆脱技术困境的一条有效路径。就此而言,之所以“为什么欧洲的强大的技术批判传统没有走下去”这一点令米切姆深感疑惑,其中一个原因,我认为就是忽视了人是一个技术存在物,人不能没有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技术的发展就不是一个应该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怎样发展的问题。从中国哲学出发,我们主张走中庸之道,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将其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反对过与不及,维持事物的稳定性。叩其两端,允执其中,它体现为实践中选择适当的手段,看准适当的时机,掌握适当的分寸。一句话,把握时机,因地制宜,审时度势。
李泽厚认为中庸的思想是实用理性的第一范畴,它的实质是度,强调无过无不及,掌握分寸,恰到好处。中道不是工具意义上的折中,它来自于生活世界,来自于操作,但并不停留在对生存情景的实际处理层面,而是要进入由人类历史所积累形成的对世界、自然与社会的整体把握,不是实用主义。可见,李泽厚先生把它提到了一个人类学本体论的高度。[13]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恰恰是解决技术哲学“大问题”的合适方法。
同样,在我看来,中国哲学的和谐思想也是面向未来的技术伦理学的重要理论路径。和谐与中庸相辅相成。和谐除了适度和考虑语境之外,还包含了兼顾不同价值主体的利益,主张和而不同、团结共生等含义,因此,它从本质上与基于个体主义、自由主义来处理“小问题”的技术哲学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在《纳米伦理的中国视角》[14]《与自然和谐:中国古代的技术发展观》[15]以及《工程技术中的可能性与可接受性》[16]等文章中多次阐发了基于中国哲学的技术哲学思想。
近年来,中国技术哲学越来越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发掘和重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逐年增多,其中最令人欣喜的是一批“80后”学者的学术创见,他们开始尝试将中国古代的技术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与现代西方的现象学相结合。这些探索不仅有利于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技术哲学的深厚资源,使得世界技术哲学的版图更加多元化;更重要的是,它也将为解决米切姆所说的技术哲学“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注释:
[1][2][3]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4页;第7页;第8页。
[4][5]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08页;第108页。
[6]京特·安德斯:《过时的人》,范捷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40页。
[7]参见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沈阳出版社,1999,第48—49页。
[8]参见王国豫、王梦颖:《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生态伦理思想》,《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50—54页。
[9]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第108页。
[10][11]Cf. H. Plessner, “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Einleitung”, inDi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V), Frankfurt am Main, 1981, S.20-41,S.384.
[12]Cf. Zhang Jing , Wang Guoyu, “High Support for nanotechnology in China: A Case Study in Dalian”,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43 (1): (2016), pp.115-127.
[13]参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8—16页。
[14]Cf. Wang Guoyu, “Nanoeth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J. Britt Holbrook(ed. ), Ethic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A Global Resource, 2nd Edition, vol.3.
[15] Cf. Wang Guoyu, “Harmonization with Nature: Ancient Chinese Views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S. Christensen, C. Mitcham, B. Li, Y. An (eds. )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and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vol.11, Springer, 2012,pp.357-377.
[16]Cf. Wang Guoyu, Li Lei, and Cao Xu, “Feasi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in 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Eastand West, 2018, pp.51-61.
技术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学派的研究纲领
陈凡、陈佳(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一
回顾中国技术哲学的创立和发展历程,可为实现技术哲学中国化,进而建立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学派提供理论前提。我们看到,国际技术哲学学会(SPT)自1976年成立后,从欧美中心论开始走向全球化;中国技术哲学学会(CSPT)自1985年成立后,经历了“立足本土化、面向国际化、促进中国化”,进而走向“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学派”的历程。其中,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作为国际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对中国技术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他第一次来华参加“中美科技与社会(STS)讲习会”时,笔者曾将待出版的《技术社会化引论》送给他,米切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较高的评价。近期他对中国技术哲学表现出“亲近技术”而“批判性不强”的质疑也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谋划其未来发展。
技术哲学的中国化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的本土化诉求。当时,以陈昌曙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技术哲学学人展开了关于工程技术的方法论等哲学问题的研究,如陈昌曙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发表了《要注意技术中的方法论问题》(1957年第2期)、关士续等在《红旗》发表了《从“积木式机床”看机床内部的矛盾运动规律》(1960年第24期),成为中国工程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开端。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本土化的重要阶段。陈昌曙倡导从整体上研究技术和技术发展规律,发表《科学与技术的差异和统一》(《光明日报》1982年10月1日、15日)、《技术是哲学的研究对象》(《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3期),认为技术哲学应该成为哲学的一门独立学科,由此中国技术哲学学会成立并走上了建制化轨道。与此同时,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逐渐建立起技术哲学学术联盟,被国内学者称作“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1]。
在中国技术哲学发展初期,我们对以《技术体系的社会建构》(1987)[2]为代表的西方技术哲学理论还不太了解。因此在《技术社会化引论》中,我们基于本土实践提出技术社会化理论,这也是自觉建构技术与社会互动模式的一种有益尝试。陈昌曙在该书“序言”中认为,该书对中国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构成了关于技术社会化相当完整的体系,而且又可以成为中国人的技术社会学专著[3]。
1999年陈昌曙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技术哲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99),尽管作者申明这本书是“土的技术哲学”,是“略接近工程的技术哲学,而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相去较远”,但刘则渊认为,“该书将人工自然作为自然改造论的基本范畴和技术哲学的逻辑起点,体现了东北学派的风格和特色,因此它是中国技术哲学东北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4]。2001年陈昌曙和远德玉还发表了《也谈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阐述了技术价值论导向的研究范式。[5]
在中国技术哲学“立足本土化”的过程中,学界也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的国际化”。陈昌曙1996年发表《美国技术哲学文献简介》,介绍了美国技术哲学1975—1995年20年间的发展状况,提出“要十分重视欧美技术哲学发展动态”[6]。在改革开放推动下,中国学者也开始较多引介西方技术哲学成果,并在2001年首次有中国学者作为会议正式代表受邀参加“第12届国际技术哲学学会(SPT)会议”,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开始了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新路径,中国技术哲学学会和东北大学在2015年还举办了“第19届国际技术哲学学会(SPT)会议”,这也是自SPT成立以来第一次走出欧美来到亚洲,来到中国。
中国技术哲学学会自建立至今已35年了。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技术哲学应成为当代“第一哲学”[7]。那么,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21世纪的中国技术哲学?笔者基于技术社会化理论,参照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双重语境,提出中国技术哲学应该与时俱进、文脉传承,“立足本土化,面向国际化,促进中国化,走向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学派”。
二
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学派的建构过程应坚持“四项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人类社会正从工业社会走向智能社会,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既要结合中国新型工业化的现实需求,深化对“传统技术”改造升级的认识;同时还要与时俱进,形成诉诸“新兴技术”的问题旨趣。国内当下的技术哲学研究仍然存在着“知识完整性”缺失现象,有些人对传统技术的研究多限于工业化时代语境,而对新兴技术知识知之甚少,以致难以深入研究,最终或成为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通晓国外技术哲学与直面当下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技术哲学研究一定要了解国外动态,“洋为中用”有助于中国技术哲学的发展。但通晓国外技术哲学的目的是催生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落入因“西方化倾向”而导致的“中国之缺位”陷阱。所以我们应从“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即中国的技术哲学应以批判性的立场展开对国外技术哲学的研究。既要“论其所是”,也要“论其所非”;既要建设性地批判,也要否定性地批判;既要弘扬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正功能,也要警觉科学技术破坏力的负能量;既要构建走向问题导向的技术哲学,更要将技术哲学研究融入中国伟大的变革实践中。[8]
第三,坚持经验转向与理论升华相结合的原则。中国技术哲学始于实践,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经验”特征,走了从技术进入哲学的研究路径。随着研究视域的拓展,从哲学进入技术的路径愈益成为中国技术哲学发展的重要方式。当今人文的技术哲学确实需要实现“经验转向”,以避免陷入对技术的抽象批判;工程的技术哲学则需要实现“理论升华”,即加强学理分析,将“形而下”的经验传统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四,坚持专一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的原则。现代技术哲学自产生之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便具有不同的研究特色,在不同学者身上亦体现出不同的哲学传统。弗里德里希·拉普(Friedrich Rapp)区分了工程科学、文化哲学、社会批判主义、系统论四种技术哲学;米切姆划分了技术哲学中工程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传统;唐·伊德(Don Ihde)将技术哲学分为实用主义、技术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人文批判四种流派。[9]由此可见,学派林立、方法各异成为现代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因此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单一化方法。诚然,有关技术的“亲疏、质疑、追问、反对”等各派之言都有某种合理性,应允许“多元化”的路径选择。但面对技术哲学的多元化现状和现实,中国技术哲学工作者应始终坚持自己的专一化道路,不能随波逐流,迷失方向。
三
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学派的建构路径应采取“三化方针”。
首先,“立足本土化”是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的实践根基。其中最为重要的路径是技术哲学与STS研究的紧密结合,在本土化研究实践中要深刻认识两者“一体两面”的关系。早在1992年,学界便提出要注意“STS研究与中国国情问题”。陈昌曙教授指出,STS问题有它的普遍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又有它的特殊性。中国的STS研究应当重视这两个方面,尤其要注意结合当今中国的国情。[10]改革开放后,中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既为技术哲学研究创造了“攀高峰”的环境,也提供了“接地气”的土壤,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中国技术哲学应在面向世界学术前沿的同时,更需要基于国民经济和国家重大需求的“中国国情”形成新的问题旨趣。例如“技术进步与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技术创新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都是中国技术哲学本土化研究应关注的重要问题。当前,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国家战略,因此如何立足本土化,将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与中国“创新驱动”的建设实践相结合,促进中国技术与社会和谐发展,是中国技术哲学理论工作者的职责之所在。
其次,“面向国际化”是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学派的理论视域。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技术哲学都有其国际性、地域性或民族性视域。如果说关注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研究是为了体现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地域性或民族性的话,那么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就体现了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国际化视野。对于当前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而言,没有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就没有前途,没有开放就没有发展。所谓开放,就需要有国际化的理论视域,新时代的中国技术哲学尤其需要国际化的理论视域。我们要实现“双向度的国际化”,即中国技术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国际化;以基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引起世界重视和借鉴的国际化。我们不能仅仅按照西方的问题意识、研究范式进行思考和研究,而是要在国际化过程中不断强化中国的主体意识,从外在驱动向内在自觉转变,以中国技术哲学的创新成果,作出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贡献。
最后,“促进中国化”是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学派的未来目标。技术哲学中国化就是使中国的技术哲学逐渐成为具有哲学主体自信、思想理论自觉,并体现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这一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具体而言,就是学习借鉴国外技术哲学理论,分析解决中国的技术问题;分析研究中国的技术现状,创生中国的技术哲学理论;运用发展中外的技术哲学理论,分析研究全球的技术问题等。技术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应该始终贯穿“中国逻辑”,即与中国实践、中国理论、中国价值直接统一的研究范式和立场观点,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相互关联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品格。[11]
四
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学派的建构方向要体现“四个目标”。
首先,要建构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技术哲学。技术哲学中国化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技术哲学,这是我们不同于西方的一个本质区别和重要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技术哲学,一是要注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的重要论述;二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合理内核,并“为我所用”。
其次,要建构立足于中国实践情境的技术哲学。我们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逐渐构建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技术哲学研究要建立在中国技术实践情境中,这是在全球化状态下不断发展的中国语境。全球化既是技术逻辑的普遍化,也是在这种普遍化条件下结合了不同地域和文化的特殊化。面对全球化语境,如何坚持中国实践情境的技术哲学研究,对于中国这样的技术大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再次,要建构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技术哲学。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始终是面向人的现实世界、关于如何做人的实践哲学。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技术与人不是割裂、对立的,中国人对技术的理解体现了一种“真”“善”内在统一的整体主义技术观,以及一种驭术于道、天人合一式的技术文化。当然,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并不是直接“上手”的,它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深刻把握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尊重自然和求真向善的精神,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最后,要建构聚焦于中国问题的技术哲学。“技术哲学的中国问题”不仅是指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且还要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技术哲学在社会的实现程度,决定于它满足这个社会需要的程度。我们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不仅要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智库建议,还要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技术进步”“一带一路与技术转移”“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全球发展”“重大疫情防控与人类文明”等问题,都是技术哲学应该关注并回答的中国问题。“聚焦中国问题的技术哲学”往往要面对种种涉及面广泛、综合性极强的实践问题。因此,在发展狭义的技术哲学学科的同时,还需要发展“交叉学科、跨学科”的广义技术哲学。
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基于中国技术实践,面向全球化背景,“不忘初心、文脉传承”,中国技术哲学就会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国际技术哲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1]参见刘则渊:《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载《工程·技术·哲学》,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第134—141页。
[2]此著为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诞生的标志性文集,由美国学者拜克尔(Wiebe Bijker)、休斯(Thomas Parke Hughes)和平奇(Trevor Pinch)主编。
[3]参见陈凡:《技术社会化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4]参见刘则渊:《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载《工程·技术·哲学》,第134—141页。
[5]参见陈昌曙、远德玉:《也谈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7期,第39—42页。
[6]参见陈昌曙:《美国技术哲学文献简介》,《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8期,第14—17页。
[7]参见李河:《从“代理”到“替代”的技术与正在“过时”的人类?》,《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第116—140页。
[8]参见陈凡、程海东:《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及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151页。
[9]分别参见弗里德里希·拉普:《技术哲学导论》(原名《分析的技术哲学》),刘武等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殷登祥、曹南燕等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唐·伊德:《 技术哲学导论》 ,骆月明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
[10]参见陈昌曙:《STS研究与中国国情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1期,第86页。
[11]参见郝立新:《新时代中国的哲学自觉与哲学自信》,“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10月18日。
工程哲学:回顾与展望
李伯聪(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一
中国的工程哲学研究走过了一段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1992年,经殷登祥联系,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美国技术哲学学会首任主席)和斯蒂芬·卡特克里夫(Stephen Cutcliffe,曾任美国STS学会主席)来华参加由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今中国科学院大学)举办的“中美STS讲习会”。会议的两个重头戏是卡特克里夫关于“STS和技术史”、米切姆关于“技术哲学”的长篇报告。这次讲习会对推动中国的STS研究具有关键意义。1994年,我去美国理海大学访学,与米切姆有了进一步的接触。米切姆把他新出版的《通过技术思考》赠送给我,我浏览后认为这是代表技术哲学领域最高水平的著作。米切姆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其中“关于技术哲学存在两个传统(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的观点更是意蕴深刻。
1995年,《Techne》(美国技术哲学协会的电子刊物)刊发了一组关于“技术哲学20年”的文章,主旨是回顾与展望,多位技术哲学大家参与研讨。学者们对于技术哲学成就的总结毋庸赘言,值得注意的是,约瑟夫·皮特(Joseph Peter)、唐·伊德(Don Ihde)、弗里德里希·拉普(Friedrich Rapp)不约而同地认为技术哲学仍然处于哲学的“边缘”位置,技术哲学家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例如,皮特特意谈到了他任技术哲学学会(SPT)副主席时经历的一件事。当他向技术史学会的一位显赫人物建议与SPT一起召开学术会议时,那人的回答竟然是:“不!那些SPT的人憎恨技术,并且他们对技术一无所知。我们(技术史家)要与他们说些什么呢?”这显然是一件耐人寻味的轶事,但本文不能对其潜台词有更多分析了。
20世纪哲学界的头等大事是语言学转向,自此,语言分析成为哲学研究的流行方法,其中所涉及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也渗透到了工程哲学领域。例如,有人把“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翻译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我们知道,engineering有两个不同的义项:工程学和工程实践(活动),两者虽有联系但绝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汉语来说,“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工程(主要指工程实践)的技术哲学”含义迥然不同,我认为应该翻译为后者。当然,这又绝不意味着“工程的技术哲学”不研究工程学中的哲学问题。
更复杂的是“技术(technology)”一词的含义和所指。弗里德里希·德绍尔(F. Dessauer,德国技术哲学家)明确指出技术的核心是发明,许多中国学人也持有此论,比如夏保华便认为应把英国工程师德克斯(Henry Dircks)的《发明哲学》(初版时间比卡普的《技术哲学纲要》早十年)视为技术哲学开端的标志之一。在我看来,对于发明和技术的关系,既要承认没有发明就没有技术,也要看到技术有比发明更广的含义,特别是在汉语中,“技术”的“术”字强调了“技术”常常是指方法和途径。由于英语中technology又用于指人工物,于是人工物就成为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的“共同对象”。
英语和汉语中的“科学”“技术”“工程”都是多义词。以往许多人都倾向于把三者混为一谈,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承认三者有联系并不妨碍承认三者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从理论上看,分别以科学、技术、工程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就可以形成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这三个“并列”的“兄弟学科”。米切姆曾经追踪技术哲学的历史,指出从1877年到1927年,先后由卡普(Ernst Kapp)、恩格迈尔(Peter K. Engelmeier)、席梅尔(E. Zschmmer)、德绍尔撰写了四本以“技术哲学”为书名的著作,技术哲学也逐渐获得了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可谓工程哲学形成的酝酿期。1991年,美国出版了《非学术科学和工程的批判思考》(“技术研究丛书”第4卷),该论文集成为当时欧美学者对工程哲学“对立态度”的集中反映。这套丛书的主编是卡特克里夫和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他们在该书“前言”中指出,希望此书能够促进对工程哲学的研究。实际上,古德曼在1990年已经发表《哲学、工程与西方文化》等文章论述了工程哲学的重要性,他甚至预言“工程哲学应该是科学哲学的范式,而不是相反”。有趣的是,卡特克里夫和古德曼却又邀请保罗·杜尔滨(Paul Durbin)主编《非学术科学和工程的批判思考》,后者在该书“序言”中明确表示“不赞成”研究工程哲学。这个矛盾现象正是工程哲学“正式出场”前的“正常状态”。
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是在欧美形成的,然后传入中国。可是,21世纪初工程哲学“正式形成”时,中国科技哲学界没有再度落伍,连续出版了数本以“工程哲学”为书名的著作。2003年中国在西安交通大学、2006年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各自召开了工程哲学的首次国内会议,2007年又在荷兰召开了工程哲学国际会议。这意味着工程哲学在21世纪初在中国和欧美同时、同步形成。在工程哲学创建之初,中国和欧美的学术交流不多,后来才发生了较大改观。
二
那么,应该怎样认识工程哲学的性质、特点和意义呢?工程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本体论高度(而非仅从工程学角度)认识工程。在20世纪的欧美和中国,广泛流行的观点是把工程解释为“科学的应用”,其实质是把工程看作科学的“派生物”,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工程派生论”观点。
本体论是一个意见纷纭的领域。中国工程师和哲学家在研究工程本体论时,立足工程实践并参考张岱年、李泽厚和西方学者对本体论的认识,提出“工程是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强调这才是与“工程派生论”迥然不同的“工程本体论”观点,并倡导必须从工程本体论高度分析和认识有关工程的各种微观、中观和宏观问题。工程本体论由于突出了工程活动是发展生产力的活动而不同于某些哲学家主张的自然本体论或物质本体论,由于突出了工程活动是以人为本的活动而不同于神学本体论。工程本体论的内容深刻而丰富,不能对其作教条化、简单化的理解。
从工程本体论出发考察“工程方法”,可以看出“工程方法”在本性上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科学方法”则是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这是两个不同的方法论体系。工程活动中也要使用科学方法,但工程活动运用的基本方法是“工程方法”。工程方法论绝不是科学方法论的派生物。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追求真理和以真理为标准,在真理面前没有妥协的余地。可是,对于工程方法论来说,工程方法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并且以生产力为标准,其中协调和权衡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工程方法是软件、硬件、斡件的统一。工程方法论是工程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从工程本体论出发考察“工程知识”,可以看出“工程知识”在许多方面均不同于“科学知识”。前者是以人工物为对象的知识系统,后者是以天然物为对象的知识系统。尽管两者存有密切联系,但绝不能认为工程知识是科学知识的“派生知识”,不能以科学知识论的研究取代对工程知识论的研究。另外,就基本分类标准而言,科学知识是按照科学学科、工程知识是按照工程行业进行分类的,两者之间存在差异。
三
在开创工程哲学的过程中,中国和欧美的工程界和哲学界都开始逐步改变长期存在的“工程界不关心哲学、哲学界不关心工程”的固有传统,逐步树立“工程界学习和研究哲学,提高工程界的哲学觉悟”与“哲学界学习和研究工程,提高哲学界的工程觉悟”的新传统。
在工程哲学开创过程中,中国、美国、英国三国的工程院都及时关注了工程哲学在本国兴起的趋势和意义,并且给予了不同方式的支持。特别是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已经成为组织中国工程师和哲学家合作研究工程哲学的强大引擎。
中国工程院自2004年起“连续立项”研究工程哲学,先后出版了《工程哲学》《工程演化论》《工程方法论》和《工程知识论》。通过持续研究,中国工程师和哲学家提出并阐释了一个包括“五论(工程技术科学三元论、工程本体论、工程方法论、工程知识论、工程演化论)”且以工程本体论为核心的工程哲学理论体系框架。虽然它还有许多不成熟和有待继续发展之处,但它无疑已经成为在“工程哲学广袤处女地”上进行学术垦荒的前进基地。
应该强调的是,就工程哲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而言,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学术公器,无国家分野或族群分野可言,一如陆九渊所说“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亦如章学诚所说的“立言为公”。可是,就研究者的思想指导、理论创见、信息基础、学术进路、学术成就和学术风格而言,不同的学者又会具有自身特色,甚至形成不同的学派,显示出学派特色,对本学科的发展发挥某些特殊作用。从这方面看,可以认为工程哲学领域形成了一个中国学派。“工程哲学中国学派”对工程哲学这个新学科在国内外的兴起发出了“中国声音”,作出了“中国贡献”。
德绍尔指出,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之后,应该还有第四个批判——技术制造批判。某种意义上,工程哲学的开创就是要实现德绍尔的这个深邃预见。
工程哲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既要汲取和借鉴20世纪语言哲学的成就,又要依循工程哲学的对象特征、内在本性和发展环境以突破语言哲学的藩篱。例如,在语言学转向潮流中,语用哲学成为热点之一,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更提出了“以言行事”理论。由于工程活动是物质性的发展生产力的活动而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工程哲学就必须突破语用哲学、“以言行事”理论的藩篱,否则它就要沦落为“以言构造海市蜃楼”的理论。另外,中国哲学一向有“言者所以在意”“筌者所以在鱼”“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说,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也提出“在登上高处之后必须把梯子扔掉”。如果把语言比喻为看世界的“眼镜”,那么语言哲学则强调了人类看世界时离不开语言这个“眼镜”。可是,“对眼镜的研究”不等于“对世界的研究”。因此,在21世纪哲学界需要实现一场“转出语言”和“转向工程(实践)”的“再转向”。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应该在这一“新转向”中努力从哲学的“边缘”走向“哲学的中心区域”。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工程哲学显然属于改变世界的哲学,它今后要走的路还很宽、很长。2020年,米切姆出版了带有回顾性和总结性的新书《迈向工程哲学的步伐》,中国学者也要不懈精进,创生新论,开辟新域。
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
王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在当代技术迅速发展并深刻影响现实生活的社会背景下,技术哲学成为最具活力的学术领域之一。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既是技术哲学在本土发挥影响的需要,也是中国技术哲学研究走向世界的需要。米切姆(Carl Mitcham)教授对“中国技术哲学发展形成自身特色”这一点,始终寄予很高的期望,这是令人感动的。多年来,米切姆教授一直在热心支持和帮助中国学者开展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研究,并给出了很多重要评论与建议。在与米切姆教授的长期交流与合作中我们体会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需要注意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曾有过相当发达的技术体系和众多技术发明,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对此有过详尽展示。[1]尽管中国古代技术是在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由于注重技术发展与自然、社会、伦理、人的身心关系等相关要素的和谐,传统文化中包含很多有关技术的本质、技术与生态关系、技术的社会影响、技术伦理、技术认知过程等方面的思想资源。[2]这些思想资源不仅促进了传统技术的发达,其强调整体思考和有机联系的特点对于现代技术发展也具有重要价值。然而这些思想资源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对其合理成分进行发掘,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重新加以阐释,才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近些年来,我们开展了有关技术之“道”的研究,目前已经初显成效。[3]从技术哲学角度来解读“道”的含义可以发现,这一范畴在具体使用语境中更多地指向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宇宙生成”之类的问题。[4]“道”实际上是人类实践活动中最为合理与优化的途径和方法,是技术的最理想状态。为人们所熟知的“庖丁解牛”的寓言就是在说明“道”的这种本质特征。如果只是从操作者、工具和对象关系角度看待“由技至道”的发展,那只能把握寓于技艺之中的“小道”,所以儒家学者认为“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5]。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是技术活动与自然、社会、伦理、人的身心关系等相关要素的整体和谐与优化,这才是“大道”。现在我们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环境友好型技术”,正是这种“大道”观念的延续和发展。以此为基础,还可以对“技”“器”“象”“机”“和谐”等相关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给予重新阐释,说明很多技术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成因,探索高科技时代技术发展之“道”,逐渐形成一套与西方技术哲学逻辑起点不同并具备中国文化特色的技术哲学观念体系。这一努力得到过米切姆教授的热情鼓励。特别是“大道”的理念,他认为,相对于西方推崇工具理性的技术哲学而言,这一理念具有难得的优点。
第二,对现代中国技术实践展开哲学反思。现代中国技术实践在引进西方近现代技术的原理、方法、标准的同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注重技术与自然、社会、伦理等相关要素的整体联系,但也存在与西方技术发展类似的“二重性”问题。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工程风险等技术异化造成的社会问题,在近现代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在解决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困难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界人士在实践中都摸索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对现代中国技术实践展开哲学反思需要借鉴西方现代技术哲学的理论与方法,但更需要总结现代中国技术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经验,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研究范式。陈昌曙和远德玉教授倡导的技术价值论导向的研究范式,就是针对中国技术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的。在他们看来,技术与生态环境、技术的社会影响、技术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技术与文化传统的互动关系等方面,都涉及技术价值论的深层次问题,而技术价值论研究与技术的地域性、民族性、实用性特点关系更为密切,应该成为现代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导向性问题。[6]因此,他们倡导的技术哲学研究应关注技术活动的前沿进展,深入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实践的具体过程,关注哲学工作者与科技人员的思想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关技术发展的四个基本特点”“技术哲学研究的过程论视角”等来自现代中国技术实践的新观念。这种研究范式也得到了米切姆教授的高度评价。在与陈昌曙和远德玉教授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他曾经明确表达过这种赞赏。[7]
此外,在现代中国技术实践的哲学反思方面,还有一些成果相当具有中国特色。如李伯聪教授开创的工程哲学研究[8],关士续教授和王大洲、夏保华等中年学者有关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9],以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高新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10],等等。这些研究均展现了很有希望的发展前景。对现代中国技术实践展开哲学反思,需要注重米切姆教授所说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工程学传统和人文学传统这两者之间的有效对话,需要在哲学工作者和科技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有效对话,进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观念体系,以便更好地影响中国的技术发展与创新,协调技术与自然、社会、伦理及其他相关要素的关系。
第三,与国外技术哲学的对话与融通。发展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技术哲学需要注重与国外技术哲学领域学者们的思想交流与合作,在概念体系上相互映射(即寻找在研究对象、概念内涵、思考方法上的对应或互补关系,不断扩展研究视域),在话语体系上相互阐释,在问题意识上相互启发。与米切姆教授等国际著名技术哲学家的深入交往使我们既能够发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技术哲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又能够发现自身的不足之处,这对于中国技术哲学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冯友兰先生曾有“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提法。[11]可是,如果完全按照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接着讲”,很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对于国际技术哲学的发展也很难有更多的贡献。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利用学术会议、访学、合作研究等途径,与国外技术哲学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已经有了一些合作成果发表。但总体看来,用外文发表的成果还不多,国外学者对中国学者有自身特色的研究成果之了解还不够深入。要让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走向世界,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出现更多的中国话语,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国外技术哲学领域的对话与融通。
这方面的一项新近成果,是收录于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工程与技术哲学”丛书中的《中国的技术哲学——经典文献和当代成果》。[12]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向国外读者介绍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研究成果。首先,该书的“导论”部分对中国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着重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动态和标志性成果,包括有关技术解释和技术推理、技术现象学、西方技术哲学流派评析等方面的重要成果,以及一些中青年学者在各自研究方向上取得的重要成果。然后,该书在“经典文献”部分介绍了中国技术哲学研究领域老一辈学者中陈昌曙、远德玉、刘则渊、李伯聪的代表性著作及其评述。最后,该书在“当代成果”部分,介绍了技术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第二代学者有关工程美学、技术哲学的中国化与技术的社会化,以“道”“技”关系为核心的中国技术哲学、技术理性的演变及其人文关联,纳米伦理学研究与技术伦理学的中国视角,技术创新与生活世界,信息技术哲学及其在中国的当代价值等方面已取得的成果。这是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成果向国际学术界的一次比较集中的展示。米切姆教授在推动该书立项和出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学理上讲,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要能够发展起来,得到国际技术哲学界同行的认可和重视,关键在于找到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得以成立的根基。这就是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的支持,有对现代中国技术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经验的科学总结,有同各种技术哲学流派对话与融通的开放心态,因而能够提出与西方技术哲学流派在逻辑起点、研究视角、思路和方法上有所不同的观念,又能够用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话语表达出来,确实能够起到与其他技术哲学流派互补的作用,对解决当代技术发展所引发的重大现实问题具有显著价值。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还是刚刚起步的事业,需要我们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
注释: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导论”第1—2页。
[2]参见胡维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技术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赵海明、郭京生主编:《中国古代发明图话》,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3]参见王前:《“道”“技”之间——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
[4]冯友兰先生也曾指出,“道”生万物不属于宇宙发生论,它与时间没有实际关系。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116页。
[5]《论语·子张》,参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200页。
[6]参见陈昌曙、远德玉:《也谈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兼与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商谈》,《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7期,第34—42+52页。
[7]参见陈昌曙、王前:《关于技术哲学的五个问题》,《哲学分析》2010年第4期,第165—170+192页;远德玉、卡尔·米切姆、尹文娟、曹东溟:《中国技术哲学的起源、发展、困境及出路——访远德玉教授》,《工程研究》2016年第4期,第431—438页。
[8]参见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大象出版社,2002。
[9]参见关士续、王大洲:《有关技术创新的几个认知问题》,《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115—118页;夏保华:《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0]相关成果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科技化前景的哲学研究”(段伟文)、“高科技伦理问题研究”(王国豫)、“大数据环境下信息价值开发的伦理约束机制研究”(李伦)等。
[11]叶朗:《“照着讲”和“接着讲”》,《人民日报(理论版)》,2013年3月21日。
[12]Cf. Chines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Classical Readings and Contemporary Work,Qian Wang(ed. ), Springer, 2020.
技术治理与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
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对现代科技的正面评价,似乎多于西方学者尤其是欧洲学者,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最近的新冠疫情应对中可获得某种直观感受。比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运用其“例外状态理论”对政府隔离措施展开批评,这在中国学界几乎无人赞同。再如此次疫情期间,美国民间反智主义的一面暴露无遗,相比而言,中国社会则给予专家更高的评价和信任。
当代中国技术哲学亲近技术,与从业者学习美国的关系并不大,其原因应该从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找。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如郭颖颐(D. W. Kwok)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唯科学主义盛行。对此,有没有“唯”科学值得商榷,但推崇现代科技的观念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应是存在的。一般认为,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1840年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中中国遭受的屈辱有关。而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居然有人鼓吹“西医无用”和“中医万能”,说明现代医学在中国仍然有许多反对者,乾嘉学派“西学东源”的遗风仍在,中国人对待科学远未到“唯”的程度。
不可否认,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存在跟着外国同行“跑”的现象。不过关键问题大约不在于“亲近技术”或“质疑技术”——如果说美国技术哲学过于亲近技术,欧洲方面则更愿意批判技术,那么中国要么学习美国多一点,要么学习欧洲多一点——更多在于中国问题和中国语境的缺乏。具体表现在,比如问题方面,被别人的议程设置牵着走,没有反映中国技术发展的实际状况。如中国路桥和高铁技术发展世界领先,大工程领域更是世界首屈一指,然而这些成就背后的理论意义在技术哲学领域并未得到充分挖掘。在语境方面,对于西方理论的照搬往往“水土不服”,比如西方新近流行的“负责任创新”理论、“公民科学”理论和“公众理解科学”理论,其提出与当代欧洲民主制进程紧密相关,属于技术民主化运动之一部;而在中国并没有类似的社会思潮和运动。理论的引入应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比如“负责任创新”理论应该融入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理论阐述之中,而“公民科学”理论和“公众理解科学”理论则应与本土科学普及理论融合。
技术哲学如果不能在中国国情中扎根并汲取“营养”,就谈不上关注技术的“大”问题,更无法摆脱对过于实证和琐碎的问题的研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如德国哲学家诺德曼(Alfred Nordmann)所言,仿佛世界范围内真实的“社会实验”上演,尽显各国在制度、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就体现在技术治理的能力和模式上,因为抗疫工作的展开凸显着社会公共治理领域应用科学技术原理、方法和成果的关键性作用。
所谓“技术治理”,指的是在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经济领域当中,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标,系统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治理活动。技术治理思想的兴起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结果。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电力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变革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很自然地,一些学者便提出将威力巨大的科学技术用于社会变革和改造活动中,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造福社会公众,这就是技术治理思想的基本主旨。
技术治理并不止于一种观念或理论,而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引发了技术治理运动。著名的技术治理社会运动比如北美技术治理运动、苏联的控制论运动和智利阿连德政府的“赛博协同”工程。20世纪至21世纪之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公共治理领域内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当代政治的技术治理趋势”。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加快技术治理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
必须要指出的是,技术治理所运用的技术既包括自然技术,也包括社会技术。举抗疫为例,前者之应用如以病毒学、传染病学、临床医学和生物化学等方法来筛查和治疗病人、研制疫苗和对症药物;后者之应用如以公共卫生学、公共管理学、运筹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等方法,有序隔离人群、共享信息、调拨物资、维持秩序。“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关键是社会技术的运用。中国抗疫成果有目共睹,原因之一固然在于政府对专家意见给予充分重视,但成功的关键不是科技水平更高,而是社会隔离实施得好,即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的相互配合。这亦体现出中国更高的技术治理水平。
中国在过去40年间取得的成绩举世震惊,也让所谓“中国模式(China Model)”或“中国道路(China Way)”研究在国际上越来越热门。一些海外学人将中国的成功经验归结为某种技术治理实践,即所谓“技治中国论”,这种观点确实存在问题。因为中国并没有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道路,但对技术治理的强调似乎仅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某一个侧面的经验:运用好技术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这个角度看,技术治理研究可被视为一种技术哲学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研究,主旨是借助技术哲学的理论资源来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流动明显加快,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和升级,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这些都给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毫无疑问,与40年前相比,中国的治理水平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但是治理现代化的工作必须不断与时俱进。在其中,提高中国社会和政府运用技术治理手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能力,是中国治理现代化极为重要的一环,因而中国国情之下的技术治理理论研究,对于中国治理现代化之推进意义重大。
然而,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既有的技术治理理论研究均相当薄弱。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亲技术”与“反技术”二元对立的基本立场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一些技术治理主义者倾向于将所有政治问题都还原为技术问题,设想整个社会成为总体化的“机器乌托邦”;而一些反技术治理主义者则将技术治理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它必定会剥夺人的自由,危害民主制度,压迫工人阶级,甚至把个体变成社会“大机器”上可以任意替换的零件。
上述二元对立的极端观点是错误的,哲学对技术反思的根本态度同样要从一味的辩护、批判走向审度。赞美技术者只看到技术造福人类福祉的一面,迷信所有的技术问题只能由新技术来解决,甚至走向极端的“技术万能论”。反对技术者看到的则是技术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认为当代几乎所有重大的全球性问题都是现代科技所导致的“恶果”,甚至走向打砸机器和实验室的激进卢德主义。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米切姆(Carl Mitcham)主张将西方技术哲学理论划分为工程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传统,认为前者更为亲近技术,而后者多以批判技术为能事。
更好的技术治理理论应该坚持审度技术的基本立场。对于技术,不能单纯地给予批评或辩护,而是要结合具体国情,谨慎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展开审度。所谓“谨慎”,即强调反思技术要摒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全面看待问题;所谓“历史”,即要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调整对某一技术问题的认识;所谓“具体”,即主张在具体的语境中审视技术问题,区别对待不同领域、地区、民族和对象的技术问题。因此,研究技术治理,并非简单地支持或反对技治主义,而是要构建一种理解、选择、调整和控制既有技术治理实践的理论,强调“建设性引导”的基本立场。我们不能任由技术治理自生自灭,而是要将之引向有利于社会福祉的一面。
显然,经过如此审度的技术治理是一种积极面对新技术挑战的能动性理论。很多“亲技术”的人,坚持技术工具论立场,认为技术只是实现人类目标的工具,技术负面效应责任在人而不在技术。而“反技术”派则主张技术实体论的立场,认为技术发展有自主规律,它已在奴役人类,正将人类裹挟至万劫不复的深渊。技术审度论者则认为,工具论与实体论之分歧属于哲学论争,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伪之辨,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新技术挑战,人类是否有决心和勇气调控技术的发展,并为此付出必要的代价(比如牺牲某些技术便利)。我们可将此种观点称为“技术控制的选择论”。
反技治主义者的很多批评意见言过其实,但其中亦有不少值得认真对待,并在重构技术治理模式时加以注意。尤其是他们所指出的要防范出现“机器乌托邦”的风险。比如说,技术治理必然伴随着技术“反治理”现象,如技术低效、技术怠工、技术破坏和过度治理等。我们不可能也不必完全铲除“反治理”,而是要对其包容、理解和控制,实现治理与反治理在一定阈值内的平衡,如此一来才能实现最满意的技术治理效率。如在电子监控问题上,并非越多越细就越好,很多社会参数是没有必要获取的,很多违纪违规行为应该交还道德领域,甚至要被社会所容忍。过度监控可能成为阻碍治理的反作用力,浪费人力、财力、物力,陷治理于信息过载之中,严重降低智能治理的效率。
再比如,技术治理必须考虑再治理问题。技术治理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社会风险,其中最大的政治风险在于:专家权力过大,威胁民主和自由,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机器乌托邦”。所谓技术治理的“再治理”,就是思考以何种制度设计防范专家权力过大。其核心问题包括:其一,划定专家权力范围;其二,权力越界的纠错制度。“再治理”机制是上述“审度”的技术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以防范技术治理与极权主义结合进而走向技术操控。实际上,“治理”与“操控”的区别不仅对于“再治理”而言很重要,在技术治理于各个领域的具体实施当中,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技术治理的模式选择更大程度上与治理问题相关,而非纯粹的技术问题。换言之,技术治理是“治理中的技术”与“治理中的人”结合的产物,在不同语境、不同国情和不同历史条件下会呈现不同的模式。好的技术治理模式并非科技应用水平最高的模式,而是治理活动中人和技术两种因素结合得最好因而最适应的国情模式。对于中国而言,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目标服务的技术治理模式才是最好的模式。当然,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还必须考虑技术治理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米切姆所言,技术-生命世界是脆弱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技术治理系统才真正有利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中国技术哲学的国际化思考
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随着人类社会持续深度科技化,技术哲学讨论开始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中国化技术哲学话语的建构一直在摸索中前进。作为国际技术哲学学会的创会主席,米切姆(Carl Mitcham)始终特别关心中国的技术哲学发展。在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负责任创新”论坛和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工具与人”技术哲学论坛上,米切姆都作了有关中国技术哲学发展的演讲。他的《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应重视批判性》一文即脱胎于这两次讲演。米切姆对美国技术哲学圈内的技术乐观主义颇为失望,希望能从中国文化中寻找解药。马克思五十多岁学习俄文,米切姆七十高龄仍然在学习中文,若非对中国文化抱有巨大热忱,绝不能发愿如斯。不过,他仍感到中国技术哲学界对技术发展的态度过于乐观。
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的经济腾飞,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而科技哲学工作者对科技的评价整体上倾向于积极。近年来,越来越多技术哲学领域的青年学人到海外求学或访学,直接接触国际学界前沿问题研究。其中,技术哲学“荷兰学派”的工作备受关注。荷兰的高科技发展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对技术哲学研究有着强烈的社会需求,所以“荷兰学派”风头日劲。从“结构与功能分析”到“负责任创新”与“道德敏感设计”,“荷兰学派”引领了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设计转向”等诸多新趋势。“荷兰学派”大体包括三个思路:(1)以克罗斯(P. Kroes)为代表的分析技术哲学,主要研究技术人工物本体论地位问题;(2)以维贝克(P. Verbeek)为代表的现象学路径,侧重考察技术对生活经验的调节;(3)以拜克尔(W. Bijker)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路径,着力考察社会因素对技术发明的影响和构造。目前,这三种思潮尤以维贝克路径的风头最劲。在国内,一批有荷兰学习背景的青年学者努力介绍“荷兰学派”的研究成果,还试图从比较哲学思路进一步发展“荷兰学派”技术哲学。
总结起来,中国青年学者的技术哲学国际化工作主要分成三大块,分别是现象学路径、后现象学路径以及技术伦理学-STS的路径。此外,分析的技术哲学也有学者涉猎,但相对前三条路径而言研究者较少。许煜曾师从斯蒂格勒。承袭海德格尔、斯蒂格勒、西蒙栋等人的研究方法,他着力从现象学角度考察技术的本质问题,指出技术得以可能的存在论条件,即他所说的“技性(technicity)”问题。他不关心具体的技术,而是提出“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的概念,试图从中国特有的形上学出发来考察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性”概念。后现象学的思路则比较侧重考察具体的技术问题。维贝克的学生洪靖试图进一步发展设计哲学,尤其侧重考察儒家价值对技术设计的可能贡献。王小伟则从后现象学“文明给定(civilizational given)”概念出发,考察儒家的“礼器”概念的礼仪维度如何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技术。黄柏恒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技术伦理学领域,较早提出“走向儒家技术的伦理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朱勤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技术伦理和STS研究,一直试图借鉴儒家思想来开展工程教育工作。这些青年学者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学术交流频繁。黄柏恒、王小伟所编写《和谐技术:走向儒家的技术伦理学》(Harmonious Technology: A Confucian Ethics of Technology,Routledge,2021)一书,首次尝试构建儒家技术哲学。
目前来看,这些国际化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处于早期探索阶段,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各方大力合作。首先,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内外青年学人的文化自觉越来越强烈。建立必要渠道和平台使得知识和想法流动起来,能够帮助技术哲学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对国内外研究方法和范式的系统反思。另外,青年学者的工作必须建基于国内前辈学者的探索之上,必须将自己的研究同前辈学人的工作连接起来,才能作出有历史感的研究。国内前辈学者如陈昌曙、刘则渊、王前、李伯聪等都曾作过技术哲学中国化的努力,多次提到儒家传统可能的贡献。在此背景下,青年技术哲学工作者加强了同儒家学者的联系这一点也很重要。事实上,一些儒家知名学者对技术问题的态度非常开放。如李晨阳明确鼓励将儒家的技术哲学开展起来。近些年来,儒家技术现象学承袭后现象学和国内前辈学者的工作,颇为引人注意。
作为一种技术哲学中国化的努力,儒家技术现象学主要包含两种进路。第一种思路是将技术哲学作为“第一哲学”进行研究。海德格尔在这方面作了卓越的工作。他将技术当成一种“此在”的在世方式。但是,将海德格尔的思路作为一种方法来考察中国技术问题的研究路径有其不足之处。许煜延续这个思路作了一些工作,但他对中国技术观的历史梳理跨度太大,从上古神话到文化革命,试图从中理出一条有关技术的叙事线索。更为谨慎的方法或许是紧扣一个海德格尔的概念,例如他的“历史性”观念,考察如何把中国哲学放置在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技术史中展开思考。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指的是“此在”的在世结构,即“此在”将自己的过去当成有益未来的一种现在的存在方式。根据这一思想资源,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伦理学资源以及文化现实作为自己的历史如何能帮助我们深刻理解技术问题。这一进路一方面要求精研海德格尔技术哲学,另一方面要求创造性地将其思路通过概念“管道”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贯通。具体而言,有以下两个向度值得深入挖掘。
一是情绪的存在论考察。海德格尔提出了“焦虑”和“罪感”是“此在”在世的一种存在论情绪。当“此在”面向未来,看到无穷的可能,理解到一切意义都是无基础的,于是“此在”沉入焦虑之中。当“此在”朝向现在,发现自己的过去由“常人”所设定,自己则沉沦在闲谈之中,于是“此在”感受到一种良知的悸动,陷入“罪感”之中。可见,“焦虑”和“罪感”都是一种历史性情绪,这种情绪进而提示“此在”对自己的存在进行回应。而技术作为一种“命定”自然也会引发存在论情绪。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进一步追问中国传统哲学中是否有存在论情绪,它对我们理解技术有什么启示。一些学者认为,相较于西方哲学传统,中国哲学传统似乎更加重视情绪,如孟子的“四心”本身即具备认知和情感维度,“情论”是儒家和佛学的经典课题。如何开发这些传统资源,并将之同技术问题创造性地联系起来,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
二是将中国哲学资源当作技术可理解性的前提,考察不同文明所蕴含的不同形而上学如何理解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似乎认为,技术只有前现代和现代之分,而前现代的形而上学则将技术理解为一种“带出”的存在方式。类似地,比照古希腊,我们可以回到古代儒家思想中去寻找是否有不同于“带出”的技术观念,或者有别于古希腊“带出”的另一种“带出”。前者是更加基础的存在论考察,核心是找到在“带出”之外的存在可能。后者是具体的存在论考察,核心是“‘带出’的存在论结构是什么”。儒家“有机宇宙”观、“天人合一”观、“三才”观等都有与“技性”概念有关的资源,值得特别挖掘。另外,儒家“功夫论”与海德格尔的“上手论”都重视实践的生存优位,两者有相通之处。如何深入“开挖”儒家“功夫论”,把它当作一个存在论概念而非伦理概念去理解,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兴趣。
相较于经典现象学考察,儒家技术现象学的第二种进路是后现象学的。这一思路又可粗略地一分为二。一是将唐·伊德(Don Ihde)的实验现象学考察具体化,专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能否提供决定技术产品按照特有的方式显现给我们的视域。例如,考察中国人对木材、石材乃至金属等物质的生存属性之理解如何决定其对由这些材质所制造的技术品的体验。再如,研究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如何决定技术与美好生活的关系。这些研究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另外,也可以延续维贝克的思路进行具体的伦理考察。虽然师承伊德,但是维贝克把后现象学进行了伦理转向,开始关注道德规范性问题。按照这个思路,可以考察中华传统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设计、采用乃至想象具体的技术品。而“道器关系”“观象制器”“藏礼于器”等概念所包含的中国传统价值对物的设计、制造和布置的影响,亦均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以上这些向度都亟需在比较哲学视角下得到进一步推动。儒家技术现象学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伊德和维贝克的气质,对技术的态度相对比较乐观。这可能让米切姆感到忧虑。对此问题展开细致辨析首先需要区分两种技术观:将技术作为一种工程实践,与将技术作为一种哲学反思。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部分得益于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青年一代大都认同技术的工程效果。但是作为哲学工作者,大多数人对科技仍然保持着必要的批判态度。很多现象学的技术哲学工作者继承了海德格尔那种技术怀旧主义气质,即便是后现象学者,也都试图将偏好悬搁起来,考察技术如何显现的问题,其根本的思路是纯粹描述性的,一般不带有个人的价值偏好。
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0)中,许煜鲜明地表达了对技术发展的担忧,并试图通过回归“宇宙技术”的办法来防止现代技术对丰富存在的破坏。“宇宙技术”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技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前文提到的《和谐技术:走向儒家技术伦理学》一书则试图回归儒家“礼器”观念来找回技术的超越维度,将“用物”观改造成“敬物”观,这显然也是出于对技术之忧思。概言之,中国青年技术哲学工作者的根本态度更接近所谓的“审度”观,结合观察、描述、批判与扬弃,试图发展出一套别具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
从技术哲学史的角度来看,米切姆在北美学界所感受到技术乐观态度或许并非来自某个具体的哲学家,而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后的技术哲学群体的普遍特征。“经验转向”之后,哲学家们开始关注具体技术品,不再将技术当成整体去批评。一旦对具体的技术品展开考察,技术往往呈现利弊共生的样态,较难统论好坏。不过,米切姆的忧虑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在一个工程大国研究技术哲学,的确要时刻避免自己的思考受到工程效果的压倒性影响。在此意义上讲,他的担忧深刻而现实。
深度科技化与中国技术哲学的未来之路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哲学固然是基于普遍性的思考,但又应是在特定时空境遇中展开的富有意义的探究。要探寻中国技术哲学的未来之路,先要立足哲学的旨趣,从世界和中国两个维度,对当下的技术与技术哲学进行一种概览或通观。
如果将技术哲学的使命简略地概括为“技术时代,哲学何为”,则必须进一步廓清的是,与海德格尔及埃吕尔(Jacgues Ellul)、鲍德里亚和德勒兹等所批判的“技术时代”相比较,我们所处的“技术时代”具有哪些全新的特征和趋势?对此,在哲学、伦理和文化理论等研究中,许多学者开始以“人类世/人类纪”“后人类”“人类2.0”“生命3.0”等概念刻画我们正在经历或即将打开的“技术时代”的新版本。而这些概念得以出现的共同原因,皆在于科技正在带来一系列颠覆性的变化,从对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改变到“基因编辑”与“人类增强”,其实质是科技对世界与人的全方位深度介入。因此,可以用“深度科技化时代”或“科技世代”来概括我们这一代人与技术关系的特殊性,预思我们正在开创并将置身其中的科技未来。而不论是福山有关生物技术与“后人类”的讨论,还是斯蒂格勒、孙周兴等所聚焦的“人类世/人类纪”,都可被纳入“深度科技化时代”的叙事之中。
从当代技术演化进程来看,深度科技化是科技一体化与控制论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世界与人的有目的的技术重构和再造因而成为可能。一方面,各种技术化科学和科学化技术使得科学解释与技术操作组合为一种新的认知-行动闭环,从而使得一切可被认知的自然过程同时也成为可被操控的人工过程,世界和人因此成为深度科技化时代不断被技术重塑的对象。另一方面,运用反馈控制的思想可以为技术系统设计人工目标,使机器得以完成带有目的性的活动,这令技术人工物和技术系统不再是没有“活力”的“死物”,而能够在由人和机器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中发挥其能动作用,以实现设计者的意愿和满足使用者的意图——人们甚至担心,一旦机器觉醒而具有意识,会不会转而碾压人类?
在走向深度科技化的进程中,世界与人的技术重构在认知与存在的意义上涌现出诸多革命性的变化,由此产生了若干值得关注的技术新形态。一是技术空间与技术圈的出现。技术空间不仅包括由技术拓展或介入的物理空间与生命结构,如可观测宇宙、纳米尺度、基因组等,更重要的是在物理空间之外形成了虚拟的信息空间,如网络空间、赛博空间等。由此,技术在地球自然生态圈之上正在构建自然过程中不存在的信息圈、知识圈乃至智慧圈,这些圈层都是由技术作支撑的,可以统称为技术圈。自然生态圈与技术圈的交缠互构决定了世界和人的存在与境况。二是虚拟认知与实践方兴未艾。通过数据采集和信息计算,人们用数据来刻画世界和人,对其进行模拟、分析和干预,使认知、制造乃至生活与交往实践超越物理空间和现实可能性的限制。三是技术日渐成为无形的自动化过程。技术系统的实时化、泛在化和微型化,使得技术无远弗届、无所不及地嵌入到物理、生命乃至社会空间与过程之中,越来越隐而不现,使人难以觉察。最后是人与机器间的差异呈现出日渐弥合的趋势。随着人与机器的交互不断深化,出现了人的机器化和机器的人化这种人机同化但又存在内在冲突的趋势(谁同化谁?)。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马兹利士(Bruce Mazlish)将人与机器之间的差异性称作“第四间断”。前三次已得到弥合的间断分别是哥白尼的“日心说”使得地球与其他天体之间的差异不复存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消除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异,弗洛伊德的理论使人不再作为理性的存在而与其他非理性的存在相区分。而图灵提出的机器思维的思想及其引发的人工智能革命则昭示着人与机器间的第四间断也可能会消失,“机器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奇点是否会来临”这一质疑,成为西方科技未来及后人类愿景绕不过的思想终点。
毋庸置疑,对于深度科技化时代所展示出的诸多技术新形态的反思、批判和审度将成为技术哲学的关键主题,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主题对于中国技术哲学探究的意义何在?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那么无疑只有真正处在时代漩涡之中的哲学家才能领悟其中的时代精神。虽然技术是一种与人类相伴而生的知识与实践形式,但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其科技文明有一个领先、落后、追赶和突进的繁复而微妙的过程,中国技术哲学的发展路向无疑与中国科技文明的总体态势休戚相关。因而,对于中国的哲学研究者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无法身处海德格尔、埃吕尔、马尔库塞所置身其中的技术社会,难以在当时感受到“座架”和“单向度的社会”,而只能在滞后的现代化进程中与之形成共鸣。
实际上,米切姆(CarlMitcham)所指出的中国技术哲学不应该盲目跟随西方思想以及批判乏力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科技创新在一定时期跟随西方的思想文化副产品。在科技追赶的氛围下,各种舶来的对于晚近现代性的批判性思考,包括社会建构论以及各种后现代思想及其怪异的文学化修辞风行一时。这些批发来的思想如同母体的脐带血一样,甚至来不及确认其知识类型与思想谱系,就被直接拿来作了反思和批判后发现代化遭遇的到各种问题的武器。由此带来的好处是,面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我们总可以找到知识经济、国家创新体系、科学传播与公众参与、新兴科技的伦理法律社会研究等可以学习的主题,但由此产生的成果在转化为现实影响力上往往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在一阵阵由新的译介带来的学术“自嗨”之后,很自然地产生了思想造血功能不足这一严重的后遗症——不借用外来思想,就无法对其切身的技术境遇展开哲学思考和论述。这一态势,并不完全是由技术哲学研究者造成的,而更多地取决于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对于相关研究的需求,也和思想需求与思想供给之间沟通与协商的渠道是否畅通密切相关。以中国的工程哲学为例,它之所以能够在近二十年间异军突起,成为世界范围内该领域的并跑者,既与中国在工程领域独步世界不无关系,也得益于其推动者对哲学与工程的对话以及跨学科研究策略的重视。
不难看到,正是由于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技术领域勇闯无人区,深度科技化时代对于中国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挑战将远比海德格尔等人的技术时代更为直接,更具冲击力。从中国科技走向突破性发展的总体态势来讲,在科技风险、新兴科技伦理与治理等领域的现实需求给技术哲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利好,甚至国家正在构建专门的科技伦理委员会,对影响重大的科技活动实施系统的伦理评估和制度化的审查。但这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这些问题除了涉及观念与原则的辨析之外,更多地涉及对复杂的利益和风险的权衡。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既不能单单诉诸经验研究,也没有太多可以借用的外来思想,这意味着具有思想深度的本土技术哲学思考不可缺席。
根据这一时代性的思想需求,在中国的语境中,对于深度科技化时代及其全新技术形态的哲学反思应该成为人类新的思想热土。近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对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关于技术与时间和人类纪的思考之重视超过西方这一看似反常的事实,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正是因为中国已然成为深度科技化时代的热土这一现实,使得中国亦正在成为技术哲学反思和构建的前沿。后期斯蒂格勒在中国讲授人类纪的艺术和人类纪时代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既表明中国的思想文化创新需要这种前卫的技术哲学思考,也显示出中国已经成为通过深度科技化闯入人类科技未来的急先锋,并由此迎来了哲学和思想创造的全新机遇。在注重天地化育和经世致用的东方思想底蕴的涵育下,中国在深度科技化时代能不能打开进而如何打开一片全新的创造空间和科技文明,不仅取决于物质的力量和经济的计算,更在于哲学如何为其找到一种兼具科技创造与人文观照的稳健智慧之道。
面对深度科技化时代中国可能引领世界的历史机遇,中国技术哲学的未来之路应该如何重新定位?
第一,要反思中国技术哲学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对西方技术哲学的引进与消化吸收而实现专业化发展的收获与问题,探寻超越之道。一方面,西方技术哲学带给我们最为重要的收获是关于技术本质和技术社会的一般性认知。例如,技术不一定是科学的应用、技术负载价值、技术具有政治性、技术是由利益相关者和人工物构成的行动者网络、技术与社会相互构造,以及技术社会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技术修复,而应该通过技术调节将价值和伦理嵌入技术设计和使用之中,等等。这些认知与技术实践相结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的异质性实践过程,使相关问题和冲突得到解决和调适。但实际上,由于这些源自西方的理论建立在我们没有直接体验的技术实践之上,很多理论所涉及的技术社会学、技术人类学等科学技术研究的方法很难在中国推行,其实际效果也难免打折扣。另一方面,我们在学习西方技术哲学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了其中存在的一些困境,从中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教训。首先是二元论思想的局限性。以技术社会学为例,最开始的技术社会建构理论十分激进地刻意凸显利益磋商对技术路径的影响,后来又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等走向软化,最后回归技术与社会的多元互构。但实际上,在中国思想中,从一开始就有从关系与互动的维度进行的整体思考。以“科技”一词为例,西方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花费很大力气提出了“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这一学术名词,不论将其翻译为“技术科学”还是“技性科学”,普通的中文读者依然不明就里。而实际上它最为确切的对应词就是“科技”。其次是不断“转向”的迷思。虽然所谓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分析的技术哲学转向、物的转向、设计的转向等都有一定道理,但这种格局不大的新的方向规划很容易让人“找不到方向”。最后是容易陷入对概念的设问式论辩。如对于“负责任创新”“道德物化”等高度基于实践和路径依赖的概念,往往满足于其在概念层面对技术实践的似是而非的表面性作用,展开了过多不必要的辨析,而未能将着力点放在使其对技术设计和工程实践的实质性影响力的提升之上,因而使得这类研究实际上存在着米切姆所诟病的“小的”“亲技术的”技术哲学的问题。由于缺乏对这些弊端的自觉,中国的跟随者难免重蹈覆辙。
第二,要面向中国当代科技创新实践中的复杂性问题和真实的冲突,发挥中国思想中关系论、整体论、有机论和权变的文化基因,适当抑制借助语焉不详或语义不明的外来思想进行抽象的形而上学叙说的欲望,从深度科技化时代的现实矛盾中揭示出深层次的问题,进而提出系统的反思、预见和调节框架,以此突破西方技术哲学思想的二元论和乌托邦的局限性,寻求一种既具有批判性、建设性、预见性的思想功能,又能使之融会、协调的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应对近年来国际上对“中华未来主义”前景的质疑,构造出一种更具中国智慧的面向美好生活的新中华未来主义。这方面的探寻应该致力于运用各种思想资源激发新的思想和方法,而不应片面地引经据典或脱离技术实践伪造华而不实的虚假思想。同时,在有关科技与人类未来之关系的讨论中,面对西方科技文化中“技术奇点”等技术乌托邦思想和末世论思想,对于其中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因素要予以必要的廓清。当然这种研究不应是简单粗暴的直接否定与批判,而应深入了解其中的思想文化脉络,洞察其思想局限,展开更有深度和广度的运思。
第三,走出文本解读和理论评述的窠臼,拿出本土思想方案。聚焦深度科技化与人类未来的热点和难点,从中国在科技创新和面向未来科技社会的构建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出发,寻找解决本土难题的方案,并使之具有世界性的启发意义。例如,在人工智能伦理和治理领域,中国正在进行创新试验区的建设,社会科学界也在通过计算社会学、计算人文研究展开社会科学实验,这无疑是中国技术哲学可参与其中并大有可为的新天地。
第四,将技术哲学上升到一般哲学和智慧层面,以揭示人与技术相处之道和技术活动之道。为此,应该会通东西,使得东西方思想在深度科技化时代的社会与生活境遇中实现二次激发,得到创造性的阐释。例如,在人机关系方面,可以赋予“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君子之道以新的内涵,从科技赋能与深度科技化时代重构人的自尊的角度,构建人在科技时代的生存之道。又如,面对数字化所带来的自我生活时代、移动时代等全新的课题,应该深入探讨科技时代的自我伦理和生存智慧。
最后,要走出技术哲学的小圈子,迈向问题导向、学科交叉和知识融合。在深度科技化时代,技术哲学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相互承认的学术小圈子,而应该成为哲学发挥其时代敏感性的思想创构的开放性场域。面对深度科技化时代与人类科技未来,在会通东西的同时,技术哲学应该实现内外两个层面的思想融通。一是技术哲学应该成为整个哲学学科具有普遍意义的生长点。实际上,不论是中西马还是美学、伦理或者文化哲学,所作的很多研究其实就是技术哲学。就像技术已经无处不在但又隐而不见一样,技术哲学将成为所有面向现时代的哲学研究的底色。二是要从所有的学科和知识领域吸取思想和理论资源,要善于从中学习它们对深度科技化时代的各种经验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洞见,使技术哲学与哲学研究避免陷入自说自话的思想孤儿生态位之中,致力于让哲学在人类知识生态系统中广为接受,真正成为技术时代的生存之道与智慧之光。
展望未来,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应审时度势,令其影响力配得上技术时代。在中国迈上自立自强的科技强国之路的今天,技术哲学家要敏锐地把握这一可能极大地体现其思想工作价值的窗口期。我们应该意识到,必须超越学科共同体的理论言说与观念游戏,才能使技术哲学成为有影响、有实效的思想劳动。具体而言,要从抽象的讨论走向对真实世界具体问题的辨析,让更多人知道技术哲学探讨的是什么,使人们愿意借助技术哲学所提供的理论工具与思想架构,探讨和应对技术时代涌现出的各种实际问题,甚至将技术哲学思想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行动。对于技术哲学而言,这一过程无疑将带来脱胎换骨的改变。
质言之,技术哲学惟有成为技术时代的思想孵化器和联结器,既以其思想的种子激发人们对技术的深度关注,又作为技术实践层面可被普遍接受的思想框架,才能在对技术时代的人的认知与行动有所贡献的意义上具有合法性。为此,技术哲学家似乎可以给自己设定新的使命:勇当哲学界乃至学术界的思想先锋,走出“二级学科”的格局,使技术哲学成为面向科技未来的“第一哲学”;同时,致力于提升学术影响力、思想传播力和对青年的感召力,让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认识到,对技术的哲学反思是技术时代各种问题研究的思想基线。而要实现这一使命,我们需采取必要的知识策略,思考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则,如何设置技术时代的哲学议题,如以技术与设计、技术与艺术、新兴科技(人工智能、基因科技、神经科技)伦理等关注度高的问题为突破口,吸引更多领域的思考者参与讨论,使技术哲学通过广泛深入讨论的洗礼,改进表达方式,成为学者与政策制定者普遍接受的思想、方法和知识。二则,如何通过更有效的传播形式,使技术哲学更具社会影响力,成为技术时代的普通人反思生活、改变世界和创构未来的启示法。由此,技术哲学将不再只是为学科共同体承认的狭义的技术哲学,而是由相关社群共同探讨和实践的广义的技术哲学,成为可以调节技术活动的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