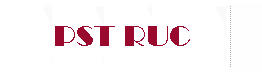摘要:对复杂性研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历史回顾,现状概述,学派评介,几点认识,哲学回响。讨论了复杂性研究与系统科学的关系,重点强调复杂性研究要求的方法论变革,呼吁哲学界对这一科学文化思潮作出必要的回应。
关键词: 复杂性;复杂性研究;复杂性科学
作者简介:苗东升,我国系统科学哲学领域资深学者,1937年生,山西榆社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先在国防科研部门供职,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科技哲学专业教授、研究生导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哲学及其实践研究,著述丰富,著有《复杂性管窥》《开来学于今:复杂性科学纵横论》《系统科学大学讲稿》《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系统科学辩证法》《混沌学纵横论》《模糊学导引》等。2020年3月苗东升教授因病去世。本文是国内系统哲学界引用极高的一篇学术综述,重发此文作为纪念。
一、历史回顾
1.复杂性研究前史
每一种新科学潮流都有其萌发、孕育过程。复杂性研究也经历了很长的孕育过程。普利高津把它追溯到1811年,认为傅利叶关于热力学的研究是复杂性科学即“新型科学的起点”[[1]]。此说不够科学,理所当然受到质疑。圣菲研究所(SFI)第一任所长柯文认为,复杂性研究作为一门科学,以及对复杂性的现代兴趣的唤醒,肇始于贝塔朗菲1928年的工作[2]。实际上,复杂性研究的萌芽恰好是现代系统研究的萌芽,二者同根同源,都开始于20世纪初,泰勒关于工厂管理的新思想,兰彻斯特的作战问题研究,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格式塔心理学,等等,都是源头。
2.复杂性研究的开创时期
20世纪40年代,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系统工程先后问世,它们原本都是为解决以往科学技术难以解决的复杂性问题而提出来的。“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3]贝塔朗菲的这句话道出了整个系统运动的初衷。这场系统运动提出探索复杂性的科学任务,提供了今天复杂性研究必须的若干概念(系统、信息、反馈、组织、自组织等)和方法论思想(对还原论的质疑和超越)。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复杂性研究就是系统研究,主要代表人物首推贝塔朗菲。维纳是另一个重要人物,虽然控制论的创立并未明确提出研究复杂性问题,但由于维纳注意的中心是对机器(人工世界)、动物和社会的统一描绘,后两者属于典型的复杂巨系统,与其后出现的以工程系统为对象的工程控制论、现代控制理论显著不同。埃·莫兰认为控制论是“通向复杂性研究的阶梯”,[4]这个说法有道理。
这个时期必须提及的人物是韦弗尔W,他把科学对象分为三类:简单性、无组织的复杂性和有组织的复杂性,研究它们分别产生了19世纪的科学、20世纪上半期的科学以及未来50年将要产生的科学。他还讨论了科学的限度、利用计算机模拟进行复杂性研究等,都是当前复杂性研究的重要问题[5]。这样一篇纲领性文章出自信息论权威之手,绝非偶然,它表明复杂性与信息、复杂性研究与信息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关于复杂性的科学与社会信息化的内在联系。只有对系统观点和信息观点都有深刻理解的学者才能做到这一点。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冯·诺伊曼。这位极善于对问题作形式化表述和求解的科学家,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主要兴趣转向复杂性问题。在提出计算机原理的过程中,通过对“电脑”和人脑的比较认识了思维的复杂性:通过研究机器能否像生物那样具有自复制能力,了解了生命现象的复杂性:通过把博弈论应用于经济问题而了解了社会的复杂性。诺伊曼据此得出结论说:“阐明复杂性和复杂化概念应当是20世纪科学的任务,就像19世纪的熵和能量概念一样。”‘[6]韦弗尔和诺伊曼的预见未能在20世纪实现,但他们的超前眼光极大地启迪了后继者。诺伊曼创造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则成为当前复杂性研究常用的锐利武器。
3.复杂性研究与系统研究的分野
后来的发展表明,系统研究与复杂性研究毕竟不是一回事。系统科学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取得重大进展。但明显地呈现出下列特点:
1)基本属于工程技术层次(系统工程、人工智能技术等)和技术科学层次(运筹学、控制理论、信息论、人工智能理论等),贝塔朗菲和维纳对复杂性的理论探索未被引向深入。
2)研究对象是简单系统,特别是线性系统,新的理论成果几乎都是线性系统理论。
3)就方法论看,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还原论。
为解决复杂性问题发动的科学探索,首先建立的仍然是“简单性科学”,出乎人们预料,却显示出科学发展历程固有的辩证特性。线性系统理论至今仍然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内容,它的理论和方法在精确性和严格性方面并不亚于主流科学,这些已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线性理论显然不是复杂性研究关注的东西。由此得到的启发是:系统研究并非必定是复杂性研究。
但是,这个时期的系统科学家始终没有放弃复杂性探索,并且在缓慢地引向深入。除了诺伊曼的元胞自动机理论,代表性工作还有:艾什比在研究“大脑设计”(1957)年时针对这种复杂系统问题提出“研究复杂系统的战略”,认为“大脑事实上是这样复杂多变,不能指望有一种理论可以达到牛顿理论的那种简单性和精确性。”[7]比尔S在应用控制论于管理(1959年)时,把科学研究对象划分为简单而动态的、复杂而可描述的和极端复杂的(经济、大脑等)三类[8],探索新的管理方法。西蒙的论文《复杂性的构造》(1962年)对复杂性概念和复杂性研究给出当时最深入的论述。[9]
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70年代以后,随着线性系统理论走向成熟,科学家面对的系统问题越来越复杂,控制论、运筹学、信息论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这种窘境促使复杂性探索重新高涨起来,终于在80年代出现新的生机。
二、现状概述
复杂性研究在这次世纪之交走向高潮,主要表现如下:
1)复杂性研究目前已遍及所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巴西、俄国等欠发达国家,成为一种具有世界规模的科学思潮,一种文化运动。
2)目前的复杂性研究称得上学派林立,观点纷呈,新见迭出,已经有大量著作问世,有关文献在加速增长。
3)按照钱学森的学科体系结构观点,每一门类的科学都具有:“三个层次一座桥梁”的结构。到这个世纪之交,复杂性研究已不只是某个学科层次的现象,而是从工程技术到技术科学,到基础科学,再到科学通向哲学的桥梁,四个层次都有大量工作,初步形成繁荣局面,代表现代科学一种全局性的新动向。
4)当复杂性研究基本由那些从事新型科学、交叉科学、应用科学的学者倡导和推进时,它的档次总显得不够高,被主流科学界看不起,对科学的总体影响有限。这种局面在逐步改变。有三个动向特别有意义。首先是诺贝尔奖得主普利高津和艾根、有世界性影响的科学家哈肯等人先行介入,基于现代物理学和生物学成就探索复杂性,引起广泛关注,标志着基础科学层次开始了复杂性探索。接着是另外三位影响更大的诺贝尔奖得主盖尔曼、安德森、阿罗大力推动建立圣菲研究所,被称为“老帅倒戈”[10],给世界科学界带来的震动非同凡响。再到1999年SCI-ENCE杂志的专集《复杂系统》,精心组织一批正在主流科学主战场物理、化学、生物、经济、生态、地理环境、气象、神经科学等前沿工作的著名学者探讨各自领域的复杂性,有力地表明到世纪之交主流科学界对复杂性研究的明确关注和认可,并直接参与进来,这是极有意义的进展。
一句话,复杂性研究今天已经初成气候,并将随着新世纪的步伐而迅速发展。21世纪将是复杂研究大发展的世纪。韦弗尔、诺伊曼等人未实现的预见,将在这个世纪实现。
三、学派评介
我们重点评介欧洲、美国、中国三大学派。
1、欧洲学派
复杂性研究在德、比、荷、奥、英、法、丹等国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贡献最大的当推以普利高津为首的布鲁塞尔学派,主要是:较早论证了复杂性科学的概念和提出“探索复杂性”的响亮口号[11];开展远离平衡态研究,提出耗散结构论,为世界各地复杂性研究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武器:分析界定复杂性概念,其努力不一定成功,但属于开拓性工作:提出复杂性有不同等级的思想,特别考察了“最低复杂性”[1],提出放弃世界简单性的信念,以便锻造复杂性研究的方法论:关于复杂性的哲学思考,如复杂性的客观性、简单性与复杂性的辩证关系等。总之,在有关复杂性研究的哲学观点、科学思想、方法论等方面,普利高津学派的影响深远,至今无出其右者。
其次是哈肯学派,理论旗帜是协同学,就简单巨系统问题很好地论证了客观世界的复杂性是通过自组织从简单性中逐步演化出来的,自组织是刻划复杂性的科学概念。如哈肯所说,协同学是目前“最先进的自组织理论”[12],这一点大概未来十年还不至于改变。协同学解决问题基于数学模型,主要是常微分方程。只要能有效确定序参量,且个数很少(一个或几个),能够建立序参量方程,系统的自组织即可用数学方法精确刻划,与硬科学无二致,在这一点上远胜于普利高津。但他的方法局限性比较大,如果宏观序参量过多,或无法建立有效的序参量方程,协同学也只能提供定性分析。钱学森把它看做简单巨系统理论,有道理。但不可把这个看法绝对化,某些复杂巨系统问题仍可用协同学方法描述。
艾根的超循环论是关于分子进化的自组织理论,对生物复杂性有较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揭示生命起源的奥秘,是复杂性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但还属于科学假说,影响有限。
英国的复杂性研究主要是应用科学层面的工作。杰克逊名声不小,他的工作属于从经验中提炼科学思想的软方法,缺乏理论深度。值得注意的是伏路德,他的论文《Complexity:a definition by construction of a conceptual framework》和专著[13]对复杂性有独到的理解(着重于认识论意义上的复杂性),但也不属于基础科学层次的复杂性研究。总的来说,英国人在这个领域的影响不大。
笔者基本赞同朱志昌的看法:欧洲学界(包括英国)的复杂性研究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和哲学精神[2001年1月4日朱志昌致苗东升的信]。如果说像普利高津这些来自自然科学的复杂性研究者已经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特点,那么,像莫兰这些主要研究社会复杂性的学者就更是如此。
2.美国学派
按照沃菲尔德的划分,美国复杂性研究又可以划分为五大学派[14]。我们只谈论其中的两家。
2.1圣菲研究所
圣菲研究所的特点是对世界各国开放,成员流动,众多世界级的科学家参与,开展规模空前的跨学科、跨文化综合研究,加上强大的硬、软件支持,声势夺人,影响巨大,被称为世界复杂性研究的中枢。最重要的是他们提出的一些概念和方法,被看作“代表着一种新的态度、一种看问题的新角度和一种全新的世界观”[15]
国内最早注意到SFI的是钱学森,并影响到他的众多追随者。国内学者早期(包括钱老)对SFI的评价过低,许多人受霍甘文章的影响,喜欢谈SFI“从复杂性到困惑”[16],对他们的贡献估计不足。笔者“偏师借重圣塔菲”的说法[17]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建立系统学要借鉴欧洲学派,更要借鉴CAS(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普利高津要么抽象到哲学,要么具体到理论物理,中间的空白太大。SFI恰有介于中间的东西,有超过欧洲学派的新思想新方法。CAS理论代表复杂性研究和系统理论的一个重要方向,对解决一大类复杂系统问题比较有效。从建立系统学看,SFI关于涌现性的探索很有价值。还有一种误解是认为SFI只有具体方法的创新,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其实,有科学方法的重要创新,就有方法论的创新。基于计算机的模型与传统的数学模型不仅是建模方法的不同,也是方法论的重要更新,前者是生成论的,后者是构成论的。SFI是生成论的,哈肯是构成论的。完全跟着SFI走也不好,他们同样有局限性。霍甘对SFI的挖苦[18],钱学森对SFI的批评[19],都有一定道理。他们的目标太大,如建立复杂系统一元化理论,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实现这个目标。
2.2结构基础学派
乔治·梅森大学成立了集成科学现代研究所,以沃菲尔德为代表,围绕管理问题研究复杂性。他们以西方(特别是皮尔斯)哲学为指导,通过总结管理经验,提出交互式管理的新概念。基本观点在有关文章[20]中表述得很清楚,认为复杂性科学的核心是由三个相关的方面构成的集合,简记作LTI集: LTI集={复杂性的20个定律,这些定律的分类,复杂性的5个指标}。
所谓复杂性定律,如必要吝啬定律、内在冲突定律等,严格说,算不上定律,不过是一些经验总结。但在管理实际中颇有些效力,有较浓厚的人文精神,值得关注。
3.中国学派
中国复杂性研究的核心是钱学森,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洞察到这个科学新方向的重要性,通过系统学讨论班聚集起一批力量,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OCGS)理论为学术旗帜开国内复杂性研究之先河,我称之为钱学森学派。钱学森是从两个方面走向复杂性研究的,一是解决国家重大实际问题,如军队建设、国家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经济决策问题等;二是建立基础科学层次系统理论即系统学的工作。其概念形成经历了三步曲:巨系统[21](1980年)→复杂巨系统[22](1987年)→开放的复杂巨系统[23](1989年)。
钱学森的复杂性研究在国内是超前的,起初不为科学界理解,甚至被某些人当作伪科学。十多年后才被接受。他的贡献主要是提出复杂性研究的独特思路和方法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从方法论层次划分简单性与复杂性,强调解决复杂性问题必须利用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对各种理论知识综合集成,对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专家经验、不成文的感受等)综合集成,对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综合集成,对机器“智能”和人的智能综合集成,对定性材料和定量数据综合集成。总之是综合的综合,集成的集成,集大成。这是系统方法最概括的表述。二是具体方法层次,也就是复杂巨系统工程,建立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用于复杂巨系统的预测和决策,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对中国学者工作的评价也要适当,至少要注意以下几点:(1)理论上还有重要问题尚需研究,如综合集成解的存在性问题;(2)不是理论研究方法,例如,不可能通过综合集成研讨厅的操作建立系统学;(3)建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目前还是一项理论探索的目标,具体成果不多,只要复杂巨系统学尚未建立,就无法令主流科学界信服。
中国学者的另一项有价值的工作,是顾基发、朱志昌等倡导的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也是为解决复杂性问题提出来的,颇具中国文化特色。基本方法论思想是强调:在解决复杂性问题时要做到懂物理、明事理、通人理,把三者结合起来,把握物理-事理-人理的整体性,以正确解决复杂的实际社会问题[朱志昌.创立品牌,走向世界——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国际交流的回顾.打印稿.2000]。但在国内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4.所谓“软科学”也是复杂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有两大类,一是牛顿、爱因斯坦代表的“硬”科学知识体系,二是感性经验、不成文的感受等非科学知识,软科学指处于这两端之间的中间地带。由于它也是成体系的知识,有理论概括和逻辑论证,同纯粹经验知识比,属于科学知识;但毕竟不如硬科学那么严格、精确,显得相当“软”,不被主流科学家承认,只得在“科学”前面加个修饰词“软”,叫做软科学。在方法论上,软科学也是超越还原论的产物,其生命力正在于能够对付硬科学束手无策的复杂性。由于从事复杂性研究的主流科学家心目中想要建立的还是类似硬科学那样的“复杂性科学”,软科学成果并未进入他们的视野。但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将改变这种观念,承认复杂性研究是一个十分广阔的战线,从计算复杂性这样的硬科学,到CAS理论、OCGS理论,到沃菲尔德讲的复杂性科学,再到软科学中最软的部分,大家都是复杂性探索的成果,对我们认识复杂性和解决各种实际复杂性问题都有贡献,都有其他方案不能代替的作用,都有权被复杂性研究的大家庭接受。
5.模糊学也是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方面军
模糊学的基本假设即札德的互克性原理,讲的是系统复杂性的增加将导致人们作出关于系统行为描述的精确性和有意义(或适用)性互不相容。模糊学代表处理复杂性的一条独特思路,值得关注。
四、几点认识
1.什么是复杂性?
据劳埃德统计,复杂性的定义已有45种[18],实际不止于此。现有的复杂性定义差别很大,无法统一,其中一些定义所讲的很难说是复杂性。复杂性是现代科学面对的最复杂的概念之一,复杂性要是轻而易举就能给出统一定义,便不成其为复杂性了。我们认为,至少目前不必追求统一的复杂性定义,这种定义现在不会有,也许将来也没有[24]只要每个学科领域有一个大体一致的定义,足矣。
复杂性的根源多种多样,任何单一因素(如非线性)都不能产生真正的复杂性,多种根源交织在一起才能形成真正的复杂性。普利高津之所以断言热力学就是复杂性科学,误把1811年当作复杂性研究的起点,是因为他单就不可逆过程这个根源看复杂性,忘记了傅利叶方程是线性方程,即使不可逆过程的线性关系也不可能产生复杂性,复杂性必定联系着非线性。多样性是产生复杂性的前提之一,研究复杂性必须注意这一点。
2. “复杂性科学”出现的必然性
所谓简单性问题,指一切可以用还原论方法解决的问题,已经得到系统、全面、透彻的研究。形成完全成熟的普适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体系。新的问题还会出现,但只要循着这条路走就可以解决,至多作一些局部的调整、修正,无须作方法论的变革。
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有两个来源。第一,客观世界本来存在的不能用还原论解决的复杂问题,如生命起源问题、意识的本质问题等。随着简单性问题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越来越多地呈现在科学家面前,必须建立新的科学体系。第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对象越来越复杂,不断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事物,如环境保护、因特网等,客观世界本身不断打上人的印迹,不断地复杂化,现有科学无法满足这些要求,世界的不断复杂化要求研究复杂性。
关于学科命名存在不同意见,一种看法是称为复杂科学[14]。我们认为不宜这样命名,因为中文的“复杂”是形容词,用“形容词+学”的方式给学科命名不合理,且含义为“复杂的科学”,即complex science:从学科命名的语言学规则看,应称为“复杂性科学”,即complexity science。对应地,以往的科学也不是简单科学,不是simple science,而是“简单性科学”,即simplicity science。
需要说明,不可把所谓“简单性科学”与简单的科学等同起来。难搞与复杂不是一回事,“简单性科学”的问题并非容易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方法论的不同。即使作这样的解释,所谓“简单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的命名仍有毛病。要说“相对论和量子论是简单性科学”,极易引起误会,必定受到主流科学家的嘲讽。应当给复杂性研究的学科定位寻找一个准确的名称。把按照方法论划分的观点贯彻到底,可否将“简单性科学”改称还原论科学,把“复杂性科学”改称涌现论科学?与reductionism对应,可否造个英文字emergencism?前者主要探求事物的还原释放性,后者主要探求事物的整体涌现性,代表科学探索的两个不同方向,而非高低、难易之分。
3. “复杂性科学”的历史地位
国内外都有“复杂性科学是一门21世纪的新科学”[2,25]的说法,需要加以分析。21世纪的科学将以复杂性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无疑的。但把这种研究带来的科学变革归结为建立“一门新科学”,此种提法不妥,因为复杂性研究的成果不是在相对论、分子生物学之外又出现的另一门新学科,而是所有学科领域都有自己的复杂性研究,都需要超越还原论。不可能把这些成果归属于某一门学科。复杂性研究改变的不是个别学科领域,而是几乎所有学科领域,所有学科领域复杂性研究的总和才是所谓“复杂性科学”。这样说还不够,复杂性探索将开辟大量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它们无法划归某个现有的学科领域,也不会形成一个单一的新学科。同各学科领域的复杂性研究相比,这种跨学科的复杂性研究更重要,更能体现未来科学的特点。
这样的复杂性科学是整个人类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从更大历史尺度看,如果把科学发展看做一种演化系统,则复杂性科学代表这个系统的一种新的历史形态,简单性科学是该系统在以往400年中呈现的历史形态,即通常所说的传统科学。要从建设信息-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复杂性科学的发展问题。所谓简单性科学是支撑工业-机械文明的科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复杂性科学是支撑新兴的信息-生态文明的科学。
4.复杂性研究与系统科学的关系
4.1不可笼统地把复杂性研究当做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Science》1999年出的那个专集,由一些纯粹的地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化学家等等对各自学科领域的复杂性问题进行探索,虽然应用了系统观点,讨论的却是地学的、分子生物学的、化学的以及其他学科的具体问题,不属于系统科学。
4.2经典控制论、运筹学等研究的基本是简单系统,属于系统科学的重要成果,但都不能划归复杂性科学。
4.3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之间是交叉关系,不是隶属关系。
1989年钱学森在提出OCGS概念的同时,指出这是“系统科学涌现出来的一个大领域”[23]。1990年,在他与于景元、戴汝为合写的那篇著名论文[26]中,把这个观点作为文章标题予以强调。这可能是有些学者把复杂性研究作为系统科学发展新阶段的思想来源。这里存在误解。建立OCGS理论,即复杂巨系统学,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为了建立这种理论,必须对地理、人体、思维、社会等领域的具体复杂巨系统深入研究,以便发掘建立复杂巨系统学的原材料。对这些系统问题的研究属于复杂性探索,所得到的具体结果属于地理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复杂性研究成果,但不属于系统科学,从中提炼出来的系统观点、理论和方法才属于系统科学。这次研讨会的有些报告是关于地理科学、管理科学、社会学和哲学的复杂性研究,划归系统科学势必遭到非议。
五、哲学回响
一种新的科学思潮出现,必然有一种新的哲学思潮跟进。世界范围的复杂性研究的兴起和高涨,很快就会有相应的哲学研究出现。实际上,世界复杂性研究的代表人物都在对复杂性作哲学思考。复杂性研究的兴起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新机遇:宇宙观、物质观、运动观、规律观、时空观、因果观、科学观、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审美论、方法论,等等,都会随之发生大变化。关心辩证唯物主义命运的人必须关心和参与复杂性研究。普利高津在探索复杂性中得出结论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辩证的自然观。”[27]这对我们极有启发。
复杂性研究的兴起给科学哲学带来转折点,给中国的科学哲学发展提供了特殊机遇。科学的限度是当前科学哲学的一大话题,1994年曾召开专门的国际会议,复杂性科学家是重要参与者,但并未解决问题。这里的教训是:莫把还原论科学的限度当作整个科学的限度。在把握事物乃至世界的宏观整体特性方面,还原论科学的确遇到了极限(并不意味着还原论科学已无发展余地),这正是涌现论科学登上舞台、大显身手的时候。科学哲学必须站在前沿去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谁回答得最好,谁将执未来科学哲学之牛耳。
复杂性研究的深入将给我们解读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全新的视角和参照系统。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也将给复杂性研究提供许多重要思想启迪,从老子到毛泽东都有宝贵的贡献,我们不要自暴自弃。钱学森的复杂性研究始终自觉运用毛泽东思想,虽然受到某些人讥讽,却代表了正确的方向。
有关复杂性的哲学研究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中国的哲学界应有所准备,去努力占据一个与伟大的中华民族相称的位置。
参考文献
1伊·普利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46,50
2 Cowan C A.Conference Opening Rem arks.In:Pines A.Meltzer D,et al eds.Complexity,Metophors Models and Reality.New York:Addision-Wesey,1994.1~4
3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林康义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2
4埃·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
5 Weaver W.Science and Complexity.S cientist1948,36(4):536~544
6郝柏林.复杂性的刻画与“复杂性科学”.科学(上海),1999,51(3):3~8
7艾什比WR.大脑设计.武夷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4
8 Beer S.Cybernetics and Management.New York:John Wiley&Son,Inc,1959.7
9西蒙HA.人工科学.武夷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66~197
10米·沃尔德罗普.复杂.陈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1尼科里斯,普利高津.探索复杂性.罗久里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ⅲ~ ⅶ
12赫·哈肯.大脑工作原理。郭治安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5
13洪水,卡森,E,R.处理复杂y:系统科学理论与应用的介绍。 (第二版) 纽约和伦敦:全会出版社,1996.23~38
14成思危.复杂科学、系统工程与管理:许国志主编.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0.12~23
15 李夏,戴汝为.系统科学与复杂性.自动化学报,1998,24(2-3):200~207476~483
16 约翰·霍甘.复杂性研究的发展趋势——从复杂性到困惑.科学(重庆),1995(10):42~ 47
17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36
18约翰·霍甘.科学的终结.孙雍君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290,329
19王寿云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88
20 Warfield J N. 复杂的扭曲定律:组织中的一范围一项运动。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1999,16;3~40
21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增订本).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32
22席彤.社会系统研究的方法论.光明日报,1988-03-24
23钱学森.基础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哲学研究,1989(10):3~8
24 苗东升.论复杂性.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0 ,(6):87 ~ 92
25 戴汝为.复杂巨系统科学———一门 21 世纪的科学.自然杂志,1996,19(4):187 ~ 197
26 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自然杂志, 1990, 13(1):3~10
27 伊·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湛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145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Complexity Research
Miao Dongshe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research were analysed from five aspects: historical review, survey of current situation, evaluation about schools, some views and philosophical echo.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mplexity research and sy stem science have also been discussed with the emphasis put o n the transform of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ers are called to respond this scientifi-cultural thoughts.
Key words complexity; complexity research; complexity science
原文发表于《系统科学学报》(原名为《系统辩证学学报》)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