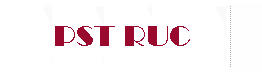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摘要] 自然神学是欧洲近代思想的底色,它对欧洲近代文化思想领域的影响和渗透是全方位的,其中也包括自然科学在内。与中世纪的思辨性相比,近代自然神学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和实证性。基于这一特征,自然神学在近代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为近代自然科学提供了助力:一方面它给自然科学提供了价值观基础,另一方面它构成了某些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框架。客观认识上述两个方面,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及曲折性。
[关键词] 自然神学;近代科学;欧洲思想;科学史
[作者简介] 马建波: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北京,100872)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科学史研究中一个具有相当分量和影响力的研究领域。大体来说,可以把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分为內史和外史两种路径。外史把宗教作为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外部社会因素来看待,着重考察它对于科学发展的推动或阻碍作用。默顿在其经典名作——《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秉持的正是这种思路。內史也即思想史的进路则把宗教思想视为近代科学思想建构的一个内生成分,悉心探讨宗教思想如何参与和影响近代科学的演进。相对来说,吉利思俾在《〈创世记〉与地质学》中就更多地采取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两种路径具有互补性,对人们理解宗教与科学互动的多样性都有积极的作用。《自然神学与近代科学的兴起》一文,以“近代自然神学”为纽带,将內史和外史两种视角结合在一起,拓展了人们思考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深度和广度。
一、近代自然神学的兴盛及特征
在基督教神学思想中,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与启示神学(Revealed Theology)相对应。前者依靠人的理性来认识和理解上帝,后者则依靠《圣经》和教会认定的权威来宣讲信仰。众所周知,基督教神学思想是古代犹太教的一神信仰与希腊理性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自然神学一直在基督教神学传统中保持着相当强劲的影响力。中世纪神学巨擘托马斯·阿奎那改造亚里士多德哲学,给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是中世纪思辨自然神学的一个极致典范。在近代,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自然神学一度受到思想家们更加充分地关注,进而深刻影响了欧洲近代思想史的运行。
从基督教神学本身的内在逻辑来说,自然神学在近代的滥觞源自于宗教改革带来的思想混乱。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新教诸派别,与罗马教廷在一些基本教义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加剧了欧洲原本就存在的社会矛盾,从而引发了欧洲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三十年战争”(1618——1648)。战争中无处不在的暴力和血腥,在促使人们呼吁宗教宽容的同时,也促使他们去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以超越宗派之间的争执,为信仰找到合理性的根基,从而结束思想混乱的局面。用著名基督教思想史研究者利文斯顿的话来说,在“整个欧洲被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弄得精疲力竭”之后,人们“产生了一种愿望,想要寻求某种共同的宗教基础,一切有信仰有理性的人们,不管他们彼此有什么差异,都可以赞同的基础。”也就是说,其时的人们希望,如果能够像几何证明题一样清清楚楚地证明上帝是存在的,那么关于信仰就不会产生如此多的纷争,世间也就不会产生如此之多的动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自然神学被人们寄予了厚望。
与中世纪相比,近代自然神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启示”以及“奇迹”旗帜鲜明地批判和拒斥。在所有的宗教中,启示和奇迹都是用来规劝人们皈依的常用手段,基督教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然而,刚刚发生的残酷宗教迫害却让人们意识到,启示和奇迹只能催生宗教上的狂热,而无法有效引导信仰。而无所节制的宗教狂热恰恰是一切混乱和暴力的根源。因此,近代诸多的基督教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对传说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所谓“奇迹”,自觉地进行了抵制。在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能够通过理性认识到上帝的存在,动辄诉诸各种奇迹来渲染上帝的威严和无所不能,既不可靠也无必要。英国近代自然神学的奠基人——赫伯特(Edward Herbert)在《论真理》(1624)中就认为:“任何一种对某个启示大肆宣扬的宗教都不是好的宗教,而一种依靠其权威性来施加教训的学说也并不总是最为重要的,甚至可能根本就毫无价值。”[2] 这种思想显然来自于他对宗教迫害地深刻反省。当宗教信仰脱离理性的指引,仅仅依赖于启示或者说奇迹的鼓动,只可能陷入盲从而无法自拔。所以,赫伯特强调:“我们应该依靠普遍的智慧来为宗教原则确立根基,以使任何真正来自于信仰之命令的东西,都能够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就像屋顶是由房子所支撑起来的那样。”[3]
同样,洛克也告诫人们不要寄希望于把宗教信仰的合理基础建立在奇迹的基础上,他的自然神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基督教的合理性》(1695)一书中。为了避免触怒保守的宗教信徒,洛克小心翼翼地避开谈论奇迹的真假,而是委婉地暗示奇迹不应该成为信仰的核心论题。洛克承认施行奇迹是上帝的权能,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展示这种权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施行奇迹是上帝的惯常的行事方式,更不意味着信仰必须依赖奇迹来保证。相反,洛克认为,除非必要,上帝“倒是经常依照万物的本性行事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的意思是,自然按照既定的规则运行,已经是人世间最大的“奇迹”了。对此视而不见,却对种种怪力乱神孜孜以求,不过旁门左道而已。按照洛克的观点,奇迹对尚未开化的远古时期的人来说也许能够起到作用,但对于今人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人完全能够通过理性在自然的秩序中发现上帝无处不在的智慧。过多地谈论奇迹,不仅无助于坚振人们的信仰,反而会让他们堕入迷信和虚妄当中。所以真正的信仰应该通过对自然的理解和认识来达成。
赫伯特和洛克的观点,在同时代人中引起了广泛共鸣。在随后的启蒙时代,那些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比如伏尔泰、莱辛等人,在对体制化的教会及其僵化的神学体系进行抨击时,沿袭着同样的思路。所以,自然神学是启蒙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来源。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近代自然神学对启示和奇迹的批判,最重要的后果并非是对理性地位的张扬和提升——虽然它毫无疑问的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而是从神学的高度确定了自然在认识中的核心地位。中世纪的神学家们也讲求理性,然而在他们那里,作为理性认识对象的上帝是抽象而高远的,因此中世纪的神学主要是由概念推演的玄学思辨模式构成的。近代自然神学在拒斥启示和奇迹之后,实际上用具体的自然取代了抽象的上帝原本占据的位置。就像洛克所说的那样,自然本身即是最大的奇迹,它出自于造物主的恩赐和创造,所以,能有什么比自然本身的规律性以及和谐完满新更能说明造物主的权能和智慧的呢?人们对一个工匠技巧高低的评判,是通过对他的作品的精巧程度来进行的;既然如此,如果充分揭示出自然内在的秩序,不正好彰显出创造和设计这一切的上帝的鬼斧神工吗?自然神学的这种观点,人们一般称呼为“设计论”。设计论客观注重通过发现自然的秩序和规律来窥探上帝的奥秘,客观上助长了实证精神的勃兴。不难看出,占据近代思想史主导地位的机械主义世界观——那种将自然视为一台设计精密、运行良好的机器的观点,背后最大的推手也是自然神学。
近代自然神学放弃了对缥缈的上帝之道的寻求,转而追索实际的自然之真理;它也不再满足于从概念到概念的干巴巴讨论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转而通过对自然规律活生生的求证来触摸上帝的奥秘。这使得自然本身悄然成为了新的权威,它不仅是认识的起点和归宿,也是一切真理的实际仲裁者。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曾经恰如其分地对此进行了概括,他认为在整个启蒙时代:
基督徒、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大家全都承认自然界这部大书的权威;假如他们意见不同的话,那也仅只是涉及它的权威的范围,即涉及它究竟仅仅是肯定抑或是取代旧启示的权威。在18世纪舆论的气候下,不管你是寻求对什么问题的答案,自然界总是验证和标准;人们的思想、习俗和制度假如要想达到完美之境,就显然必须与“自然界在一切时间里、向一切人显示”的那些规律相一致。[5]
显然,这样一种氛围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自然神学为近代科学提供了价值观基础
从价值观的层面看,自然神学对近代科学起到的作用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自然神学为早期科学的研究者提供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其二,自然神学为科学自身的合法性辩护提供了理由。人们往往只关注到第一个方面,而忽略了第二个方面;或者把二者混淆起来,忽略了它们之间显著的区别。我们可以言简意赅地说明这种区别:前者是科学家说给自己听的,而后者则是说给别人听的。
先来看前者。囿于历史条件,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家大都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这个客观事实决定了他们必然会率先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工作。从自身的主观意愿来说,早期的科学研究者们相信,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或者,换个说法,他们之所以从事科学研究,相当程度上出自于宗教意义上的使命感。

比如,哥白尼在他划时代的巨著——《天体运行论》中,就以一种克制的笔调表达了这一观点:
虽然一切高尚学术的目的都是诱导人们的心灵戒除邪恶,并把它引向更美好的事物,天文学能够更充分地完成这一使命。这门学科还能提供非凡的心灵欢乐。当一个人致力于他认为安排得最妥当和受神灵支配的事情时,对它们的深思熟虑会不会激励他追求最美好的事物并赞美万物的创造者?
相较而言,开普勒的则要夸张很多。在提出了奠定近代天文学基础的行星三定律之后,他用一种饱含浓烈感情的语气说:
创造我们的上帝啊,我感谢您,您使我醉心于您亲手创制的杰作,令我无限欣喜,心神荡漾。看,我已用您赋予我的全部能力完成了我被指派的任务;我已尽我浅薄的心智所能把握无限的能力,向阅读这些证明的人展示了您作品的荣耀。……如果我因您的作品的令人惊叹的美而不禁显得轻率鲁莽,或者在这样一部旨在赞美您的荣耀的作品中追求了我自己在众人中的名声,那么请仁慈地宽恕我;最后,愿您屈尊使我的这些证明能够为您的荣光以及灵魂的拯救尽一份绵薄之力,而千万不要成为它们的障碍。
无需罗列过多,只要愿意,我们能够在近代绝大多数科学名著中找到类似的句子。这很容易理解。在一个宗教氛围仍然浓郁的时代,科学家们自觉地把自然的规律性归之于上帝乃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在他们看来,在这方面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不过是在为荣耀上帝这项伟大的事业添砖加瓦。
再来看后者。不过,在详细讨论这一点之前,有必要搞清楚一个重要的问题:科学在今天的功能和地位,与近代是完全不同的。
在思考历史的时候,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陷入一个误区:如果一个事物在今天具有什么样的特定功能,那么它在历史上也理所当然具有这样的功能;或者,如果它今天被认为非常重要,那么它在历史上也必定理所当然的被认为重要。拿自然科学来说,它是今天指导人们实践最有效的知识体系,今天的人们也普遍认为,它是最值得优先发展的事项。因此,很多人也都认为,科学自来就是这样的,而这也是它自近代以来能够突飞猛进的原因。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历史的演进比想象要复杂很多。科学的实用性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展现出来的,它在起初表现得并不那么出色。伏尔泰在一封写于18世纪20年代的信中就抱怨科学家们对科学的实用性关注不够,没能在改善民生上做得更多。[8]而是否要支持科学研究,尤其是纯粹的理论研究,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未达成共识。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17世纪60年代,但迟至18世纪中期,人们对其意义和性质仍然颇多质疑。这让学会一度陷入财政上的窘境。亨利·莱昂斯(Henry Lyons)在《英国皇家学会史》中曾经对此有过精彩的描述。
因而,在科学展现的巨大力量让所有人膜拜的今天,人们似乎很难理解,宗教上的价值和意义曾经是近代初期科学获得社会认可的主要理由之一。不过,只要意识到今天与过往历史情境的巨大差异,理解这一点就不会有什么障碍。在一个宗教信仰仍然被个体视为安身立命之本、以及宗教仍然强有力地控制着社会各个方面的时代,着力强调科学的神学功能,在为科学争取到更高的社会认同度以及关注度方面的作用,当然不可能是无足轻重的。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提出的所谓“默顿命题”,想要说明的就是这一点。不过他把讨论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的宗教派别,视野过于狭窄了。实际上,无论出身基督教的何种教派,欧洲近代科学家们都热衷于宣扬科学在宗教上的意义和价值。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科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的地位和价值在今天当然是毋庸多言的。但在当时,本书第二版主编科茨(Roger Cotes )是这样为牛顿辩护的:
他把宇宙体系这幅最美丽的图卷如此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即使是阿尔方索王还活在世上,也不会挑剔说其中缺乏简单性或和谐性这些优点。现在我们已能更加真切地欣赏自然之美,并陶醉于愉快的深思之中;从而更深刻地激起我们对伟大的造物主和万物的主宰的敬仰与崇拜之情,这才是哲学的最好和最有价值的果实。如果有谁从事物的这些最明智最具才艺的设计中看不到全能创世主的无穷智慧和仁德,那他必定是个瞎子;而如果它对此视而不见,那他必定是个麻木的疯子。[9]
接下来,科茨进一步强调,牛顿体系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是用来对付“无神论者”的强大武器。科茨的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本特利(Richard Bentley)——他研究古希腊哲学同时也是英国国教会牧师,在教堂中的布道便取材于牛顿的这本巨著。为了更好地达到布道的目的,他虚心地向牛顿请教了很多问题,后者也非常热忱地给予了回应。按照本特利的说法,他的一系列布道取得了很大成功。
三、近代地质学和博物学的自然神学基质
自然科学发展并不平衡,各门学科的成熟程度并非齐头并进的。在近代,像天文学这样的数学化程度很高的学科,已经日趋成熟,而像地质学和博物学之类的学科才属起步阶段。因而,自然神学对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对于成熟程度较高的学科,自然神学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如前所述的价值观功能;而对于刚刚起步的学科,除此之外,自然神学还深刻影响到它们的研究内容和形式,构成了这些学科的研究框架。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地质学和博物学在近代,其实是特殊形式的实证性自然神学。
1681年,后来成为英王私人牧师的本内特(Thomas Burnet)出版了《关于地球的神圣理论》一书,其中充满了浓郁的自然神学风格。本书以《圣经》为蓝本,将地球的历史分为7个时期,详细描述了各个时期的特征以及之间的演化。根据《圣经》文本,本内特认为大洪水是影响地球表面形态变化的主要原因,并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眼光探讨了它的由来。在本内特看来,当他把《圣经》中的创世神话还原为一种自然进程的时候,有助于坚定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本内特很难被认为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关于地球的神圣理论》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无论在实际意义还是历史价值上也都无法相提并论。但不容否认的是,他其实提出了后来地质学的研究主题:地球的结构如何?地质演化的主要作用力是什么?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本内特把对地质学的研究视为神学的一部分,以及把大洪水作为地质变化主要作用力的思路,深远影响到了近代地质学理论的建构。直到19世纪中期,以大洪水为基调的自然神学框架在地质学研究中仍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科学史家吉利思俾(Charles Coulston Gillispie)在他的经典作品《〈创世记〉与地质学》中,就详细分析了这一框架是如何影响到地质学史上历次重大理论争论的。因而,近代地质学的发展与自然神学可谓紧密交织在一起。
与地质学相比,近代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有着更加浓郁的自然神学色彩。博物学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是一门对矿物、动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进行收集、归纳、分类、记录的学科。在《科学与启蒙运动》中,汉金斯(Thomas L. Hankins)认为在17世纪,存在一场显著的“博物学的复兴”,并认为自然神学的兴盛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根源。[11]博物学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自然神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目的论主导了近代博物学的研究。目的论认为万物皆有其既定的位置,生物个体结构和功能与生存环境相适应,出自于特定的设计而非偶然。虽说目的论思想自古代希腊就有巨大影响力,但近代博物学中的目的论显然直接来自于自然神学的设计论。物种分类方面的研究之所以成为18世纪博物学的主题,与目的论的强势影响息息相关。既然物种是按照特定目的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它们必然也能被一一对应地放置在恰当的位置,就像人们整理储物箱。反过来说,如果能够把物种按照某些特性井井有条地进行分类,那就必然能够证明它们的确是按照既定目的被创造出来的。林奈的皇皇巨著——《自然系统》是18世纪物种分类研究方面的最高成就,也是目的论指导之下的集大成之作。
其次,近代博物学的参与者中很多有着正式的神职身份,英语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名词——“Parson-naturalist(圣职博物学家)”指的就是这类人。他们日复一日严谨细致地观察自然,勤勤恳恳不怨其烦地描述事物的特征和各种细节,目的是为了论证上帝创造万物的精妙。在他们愉快地享受这一过程的时候,人们对生物世界的认知和了解也水到渠成的被提高到一个相当的程度。雷(John Ray)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典范,他不仅大大推进了植物学研究的水准,也开创了对动物适应现象的研究。他在植物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名为《创世中的神圣智慧》。如果单看书名,人们只会它当成神学著作。
同样,自然神学在博物学中的影响力到19世纪中期仍然存在。达尔文就坦承他在年轻时深受自然神学的影响。而且有趣的是,尽管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摧毁了旧有的目的论,但他并不排斥有人对他的进化观点做出自然神学的解释。
四、结束语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论证自然神学是近代科学兴起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只是对历史进程实事求是地予以客观描述。自然神学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这些作用,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因为近代自然科学恰好是从基督教文化母体中诞生的。在科学已然昌明的今天,它早已摆脱了自然神学的框架和束缚,更无须借助宗教的力量来获得认可。然而客观认识和评价自然神学与自然科学的这段历史,仍然是不无裨益的。它能够让人们充分意识到人类进步之大不易。人类科学的进步和思想的提升,每一次都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继承与开拓之间的艰难抉择中奋勇开辟出来的,其中的蜿蜒曲折、崎岖逶迤一言难尽。本文所揭示的自然神学与自然科学在近代的互动,直观地呈现出了人类思想运行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自然神学的初衷是论证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但是事实表明,它无法承担起历史加之于其上的重担。在18世纪,自然神学的两个直系后裔——以霍尔巴赫为代表的朴素唯物论,以及以休谟为代表的哲学上的不可知论,都背离了它的初衷。这颇有些讽刺的意味。
自然神学的设计论与朴素唯物论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设计论预设了一个上帝的存在,并且力图通过自然的和谐完满来论证它。但是一旦人们认为自然的和谐完满足够充分自洽,那样一个预设就会越来越丧失其意义和价值,甚至成为一个毫无必要的累赘。因此,当人们毫不犹豫地抛弃掉自然神学中的上帝之后,自然神学就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就是这样做的。
与朴素唯物论不同,休谟的不可知论来自于对自然神学内在逻辑地批判。休谟从方法论的角度紧紧抓住了自然神学的痛脚。休谟指出,自然神学对上帝的设计论证明,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类比。然而类比并非一种严格的演绎式证明,而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一种推测。类比的合理性只能建立在相似经验的基础上。举个例子来说,人们看到一部精密的钟表,推测它必定是某个工匠制造的,这个类比推理很合理,因为人们可以从其他地方看到有人制造过钟表。但是不管人们发现整个宇宙有多么和谐,推测它必定有一个创造者,也都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神创造宇宙的经验。所以,设计论并不能为信仰提供一个真正坚实的基础。尽管休谟对自然神学的系统批判集中在晚年的《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但在反映其不可知论思想的早期作品——《人性论》中,他对因果关系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已经深刻体现出对自然神学这种方法论上的驳斥了。
Natural Theology and The Raise of Modern Science
MA Jianbo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7872)
Abstract: Natural theology was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European thought. One of the goals of modern natural theology was to try to know God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nature and the search of laws of nature. So, it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rise of science. On the one hand, it provided a foundation of values for modern science,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vide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for certain disciplines, such as geology and natural history. This article helps people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modern history.
Key words: natural theology; modern science; history of science
(原文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