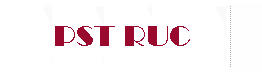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摘要] 古代科学传统(“第一种科学”)虽然可能暂时有利于环境保护,但是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最终也不能保护环境。近现代科学(“第二种科学”)的“建构”(包括实验室“事实建构”和数学抽象的“理论建构”)与“规训”(包括实验室认识过程中的“规训”和科学应用过程中的“规训”),是近现代科学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鉴于此,试图通过发展“第二种科学”来解决环境问题是行不通的。要解决科学应用造成的环境问题,就必须改变近现代科学“建构”和“规训”的性质,让科学“回归”自然、“顺应”自然,大力发展直接“面向”自然,对自然自身展开研究的“地方性科学”( “第三种科学”)。“地方性科学”“出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一改近现代科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旨归,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也能够保护环境,是一种比较完善的科学。
[关键词] 近现代科学;古代科学;地方性科学;经济;环保
在现代,近现代科学受到多个层面的评判。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求力”的科学,如吴国盛提出的“求力科学”等[1](P41-50, 156);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求利”的科学,如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还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求权”的科学,如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SSK的“后殖民科学”等。科学的“求力”、“求利”、“求权”有好的一面,不能否定;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会造成“科学与人文的冲突”、“科学与自然的冲突”,并因此受到人们的批判。
某些人文主义者利奥塔、福柯、罗蒂等主要从“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视角来对科学加以批判,给出“后现代科学”的概念,试图凭借对科学真理性和权威性的否定,实现“科学主义”的祛除,从而消除科学对人文的僭越,“把科学的还给科学,把人文的还给人文”。某些自然主义者或环保主义者则从“科学与自然的冲突”来对科学加以批判,一般崇尚“回归科学传统”,即走向“地方性知识”、“博物学”等古代科学形态。
对于人文主义者的“后现代科学”,已经受到许多批判。批判者认为它消解科学的客观性和经验基础,否定科学的真理性,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是不可取的。
对于自然主义者或环保主义者的“回归科学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回归“古代科学传统”(称为“第一种科学”)。这样的“回归”可取吗?如果不可取,则是否可以沿着近现代科学(称为“第二种科学”)的道路来解决环境问题?如果不可以,则是否应该走向“第三种科学”呢?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回归“第一种科学”:环保但不经济
回归“第一种科学”,即回归“古代科学传统”,在我国学者那里,主要指向“地方性知识”和“博物学”。
(一)回归“地方性知识”:文化的限制与局限
对于“地方性知识”,国内外学界多从相应地区、民族(主要是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来阐述其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内涵。一个普遍性的结论是,“地方性知识”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有利于环境保护。甚至有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环境保护”具有不可替代性、低廉性和纠错性。[2](P24)
考察“地方性知识”及其应用,具有生态保护功能。按理,这种生态保护功能必须与“地方性知识”的定义相一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定义:“地方性知识和本土知识指那些具有与其自然环境长期打交道的社会所发展出来的理解、技能和哲学。对于那些乡村和本土的人们,地方性知识告诉他们有关日常生活基本方面的决策。这种知识被整合成包括了语言、分类系统、资源利用、社会交往、仪式和精神生活在内的文化复合体。这种独特认识方式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方面,为与当地相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3]
据此定义,“地方性知识”就是一种地域性的知识、经验性的知识、情境性的知识、文化性的知识,是一种文化体系,有其自身独特的特征。国外有学者认为,地方性知识包括三个层次:(1)经验性的知识,涉及对动植物的认知,以及利用它们的目的与方式;(2)知识的范式——理解,即对经验观察进行解释,并将之置于更大的情境之中;(3)制度性知识,指知识镶嵌于社会制度之中。[4](P320-321)我国学者认为,地方性知识具有几个特点:(1)地域性——“地方性知识”是特定地理区域内原住民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生存手段、获取生存条件的知识;(2)整体性——“地方性知识”植根于原住民社区的社会理想和实践、制度、 关系 、习惯和器物文化之中,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授权性——“地方性知识”对地方人的活动有一定的约束和规范,这种约束和规范使得地方人的生产生活秩序井然。[5](P35)
综合上述有关“地方性知识”的层次和特征的论述,要想发挥“地方性知识”在现代生态保护实践中的作用,就需要改变现代社会,使之与“地方性知识”的产生及其发挥作用的社会文化背景相一致。但是,在现代,要贯彻这一点是完全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改变“地方性知识”的特征,使之与现代社会的近现代科学知识形态相一致,即运用近现代科学(第二种科学),对“地方性知识”的机理加以科学阐述,改进其操作,使之标准化、精确化、可操作化,最终达到顺利传播、继承、发扬和贯彻应用之目的。
可以说,那些宣扬“地方性知识”的学者正是基于这一意义进行阐述的。问题是:这样做有道理吗?一定意义上没有道理。因为,运用第二种科学对“地方性知识”的机理阐述,实质上是运用近现代科学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改造”,由于近现代科学的范式与地方性知识的范式不同,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可通约性,即存在着内在矛盾,因此,这样的“改造”只能是“脱胎换骨”的、“袪情境化”的、“脱域”的和“重塑”的,结果导致经过改造后的“地方性知识”就不是原先的“地方性知识”,而是近现代科学化了的“地方性知识”,其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根基,原有的保护生态的效用会大打折扣甚至失败。
这是其一。其二,西方学者谢巴德·克雷奇曾针对美洲土著民族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他们普遍是生态学家,但是,对于他们是否是自然的保护者,答案大部分是否定的。[6]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们虽然具有保护生态的“地方性知识”,但是并没有保护自然的意识,并将此意识和“地方性知识”应用到自然保护中。如此,就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如果上述克雷奇的研究结果成立,那么,具有“地方性知识”的很多人就没有或少有保护自然的观念和行为,为何今天的学者还将保护自然的理念和行为赋予他们呢?第二,既然那些具有“地方性知识”的人们不是自然的保护者,为何他们的行为又会每每产生自然保护的结果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学者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加以分析。纳达斯蒂认为,“自然保护”并不内在于美洲土著民族的信仰体系,之所以现在有人认为美洲土著民族具有自然保护的思想,是由那些带有西方自然保护思想的人们对此进行的带有偏见的评判,是西方文化建构的结果。[7] 蒂莫西·卢克甚至指出,沿着福柯的进路,“环境”一词不应被理解为由具体化的生态过程给定,而应理解为公众的历史建构,是工业社会的产物。[8](P236-261)
对于第二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虽然那些掌握了“地方性知识”的人们不具有“环境”以及“自然保护”的观念,但是,他们具有并且运用了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地方性知识”,结果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保护生态的功效;另外一种是,“地方性知识”运用的“生态保护功效”,并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其运用的结果,而是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我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总结,认为:第一,地方社会都有人口密度低的特征,避免了资源压力造成环境退化;第二,这些社会获取资源的技术与形式不足以造成资源退化;第三,这些社会的经济目标是有限的,他们是为了“使用而生产”而非“为了交换而生产”。[9](P25)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第四种因素——有利于自然保护的“神学观念”。
对于上述观点,尽管不无欠缺,但是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由此,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保护功能,所应持有观念是,虽然不可完全否定,但不可夸大,将环保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地方性知识”上,试图通过对此进行近现代科学(第二种科学)的改造以解决环境问题,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二)回归“博物学传统”:方法的限制及其局限
对于回归“博物学传统”,我国某些学者大加赞赏。如有学者认为:博物学能够拯救人类灵魂 [10](P50-52) 、是比较完善的科学[11] 、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12](P37-45) ,应该中兴博物学[13](P42-50)[14]。甚至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博物学传统[15](P22-24) ;中国古代的科学本质上是博物学,应该用这一新纲领来重写中国古代科学史[16](P11-19) ;中国博物学传统具有世界价值,要重建中国博物学传统[17][18](P45-53) ;中国作为独特的博物大国,其博物经验具有实践性、体知性、集体认知性、伦理性等特点,具有不可穷竭的价值,可以滋养和引导我们走向建设性的未来[19](P5-11) 。
这些都有一定道理,给我们深刻启发。不过,对于博物学,其意义和作用不可夸大,博物学毕竟是一门“前科学”,一门主要运用观察方法而非实验方法和数学的科学,一门位于科学成熟之前的认识形态。它虽然一定意义上能够让人们亲近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乃至达到人类精神的提升,达到陶冶情操和纠偏作用,但是,其改造自然的作用是不大的,对于人类物质生活的贡献是不大的,甚至其保护自然的作用也是不大的。在当代人类如此巨大地改造了自然、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以及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破坏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博物学”路径来解决精神的和环境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总之,通过“地方性知识”、“博物学”解决环境问题,作用是有限的,也是很难行得通的。而且,即使不考虑这一点,默认其保护环境的作用巨大并对此广泛推广,也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事实上,无论是“地方性知识”,还是“博物学”,都属于“前科学”的经验性的、定性的认识,是地方的、零散的、有文化限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外在的自然界,其关于自然的认识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改造自然的强度是不大的,其应用范围主要集中在农林牧副渔上而非工业上,结果是,对它们的回归,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环境危机,但是,有可能会使人类重新回到如农业文明时代那样的物质匮乏年代。试想,一旦物质匮乏了,在目前人口众多的情况下,人类为了走出这种匮乏局面,必然会过度开采自然资源,进而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甚至带来文明的毁灭。人类历史上“玛雅文明”的毁灭就是先例。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那些坚持走向“第一种科学”的人们,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主义者、一种理想主义者、一种超现实主义者。他们更多地着眼于“第一种科学”的非物质价值而聚焦于文化、伦理、历史、环保等价值,忽视了其比较低下的生产效率,存在“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之嫌疑。回归“第一种科学”,“环保但不经济”,虽然可以考虑作为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路径,但不可以作为解决目前“科学与自然的冲突”所应该遵循的普遍模式。
二、推进“第二种科学”:经济但不环保
一种观点认为,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即随着“第二种科学”的发展,其应用将会产生越来越少的问题,越来越能够解决环境问题。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一)科学对环境的破坏会随着其“建构”的增强而增强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验室研究”表明,科学家更多时候不是直接面向大自然,去发现自然界中存在的自然规律,而是在特定的实验室人工背景下,利用一定的实验仪器,渗透一定的科学理论,对处理过的对象(很多时候是人工对象而非自然对象)进行特定的操作,从而迫使实验对象产生特定的人工实验现象或规律。这是“发明”基础上的“发现”,即在建构科学事实或科学规律的基础上再“发现”这样的规律。这样的规律不是自然规律,即不是自然界中自在的规律,而是人工规律或人工自然规律,即如果没有实验者如此这般地实验,则这样的规律在自然界中不存在。
以上是由“实验室研究”推而论之的,属于“事实建构”。实际上,与科学实验相联系的“理论建构”也同样说明这一点。卡特赖特就认为,科学定律是反事实条件的,并且是其他情况均同条件的构造。[20]将这一点与实验结合起来,科学理论是与理想化的科学实验相对应的,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自然界在自然状态下是什么样子,而只是说,具有且仅有如此这般的前提条件,科学理论所面对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理论和模型是直接面向物质世界的,描述着它的状态和性质,但它们最多只是对自己意图表象的实在世界的理想化或抽象。”[21](P206)这也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说明了科学规律的人工性。
正是上述科学规律的人工性,导致科学应用生产出了许许多多的人工物,建构了另外一个人工世界。这些人工物以及人工世界,是自然界中所没有的,也是经过自然界的演化永远也不可能产生出来的,具有自然界中的事物所不具有的特殊的性质,相对于自然界中的存在就是“异质性”的存在,是“第三者”,在其生产、消费、排放过程中,会与自然界中进化而来的存在物发生作用,产生冲突,扰乱生态平衡,造成环境破坏。而且,随着科学实验的推进以及科学的数学化的加强,这种科学的人工建构性将会越来越强,所产生的人工现象和人工物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特殊,功能越来越强大。这虽然一方面能够越来越满足人类通过消费主义文化的“消费的生产”而刺激起来的欲望和需要,但是,另一方面所产生的人工物以及人工自然与自然物以及天然自然的差异越来越大,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结果只能是对自然的破坏越来越大。由此,通过这样的科学进步是不可能解决其自身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
(二)科学对环境的破坏会随着其“规训”的增强而增强
劳斯在《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中对此问题有所涉及。[22](245-247)笔者在 《科学之于环境:“规训”还是“顺应”》(待发)中作了概括总结。结论是:科学认识是科学家通过实验室的实践完成的。实验室可以理解为一个权力关系的场所。其中,科学家通过建构微观世界而完成对实验对象的“规训”。同时,这一“规训”也发生在认识者身上,以及一个实验室的认识向另外一个实验室的认识转移中。正是这样的“规训”使得“科学认识”成为“人的科学认识”,所得到的科学规律更多地呈现为“人工自然规律”,而非自然规律。这样的规律不是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知识,而是只有在实验室背景下才能获得并成立的“地方性知识”——理想化的、数学的、标准化的、人工化的、普遍化的“实验室知识”。当将这样的知识应用于改造自然时,就不是普遍的自然规律的应用,而是把适应于实验室背景下的科学知识应用于地方自然环境中。此时,由于地方自然环境与实验室背景不一致,因此,要想使得科学的应用得到实现或获得成功,就需要改变或“规训”这样的地方环境,使之更多地与实验室环境相一致。这是“让环境适应科学”而不是“让科学适应环境”,必然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
这是科学应用造成环境问题的另外一个根本原因。试想,随着这种“规训”的科学向前推进,科学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如何能够解决呢?是不能解决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实验室中“规训”的加强,科学所获得的知识或规律越来越特殊,越来越具有实验室的“地方性”,其适用范围和条件越来越特殊和苛刻,其人工性和实验室的地方性越来越强,与自然界的距离越来越远,其要应用于自然的改造,对自然环境的“规训”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越来越特殊,由此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越来越特殊。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如此“规训”的科学进步,是不能解决科学应用过程中出于对自然的“规训”而产生的环境问题的。
近现代科学的“建构”、“规训”充分说明,“第二种科学”是一种遗忘了地方环境和自然的科学,忽视了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其应用必然造成了环境破坏。不仅如此,如果不改变“第二种科学”的“建构”和“规训”的特征,那么,随着这样的科学发展,其应用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广泛。虽然随着这种科学的发展,其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在增强,但是其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将远远赶不上其应用对环境的破坏。鉴此,试图通过推进近现代科学进步以解决其所造成的环境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
三、走向“第三种科学”:既环保又经济
人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在解决其基本需求的同时,又能够摆脱环境危机呢?要想解决科学应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必须变革“第二种科学”,从根本上改变其应用造成环境问题的根基。
对于“科学的‘建构’与环境问题的解决”,应该使科学更多地走出实验室,回归自然,发展真正的自然科学(即以自然界中的对象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以获得对关于自然的更多、更全面、更正确的认识。“‘回归’自然的科学”是生态文明的基础,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必需。[23](P105-111)
对于“科学的‘规训’与环境问题的解决”,应该改变“规训”自然的科学,走向“顺应”自然的科学。“‘顺应’自然的科学”,不是完全否定实验室之“规训”,而是坚定地认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少地“规训”自然,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比较上面两点,有共同之处,即要从根本上解决科学应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就必须直接面向大自然展开认识。大自然自身是具体的、地方性的、异质的,因此,“回归”以及“顺应”自然的科学理应把重点放在对地方环境的认识上,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地方性知识”。这样的“地方性知识”,不是基于“实验室实践”背景下的“地方性知识”,而是直接面对自然的“地方性知识”,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它所获得的认识,更多地是“回归自然”以及“顺应自然”的认识或“地方性认识”,可以将此称为“地方性科学”。
分析“地方性科学”,它的最大特点是“回归自然”和“顺应自然”。所谓“回归自然”,指的是回到自然本身,获得关于自然的自在状态的认识;所谓“顺应自然”,指的是按照自然的法则或尺度(对象尺度、时间尺度、空间尺度)办事。只有“回归自然”,才能获得关于自然本身的认识,也才能在按照这样的认识去改造自然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只有“顺应自然”,即对自然施加尽可能少的“干涉”,才能获得更多的关于自然自在状态的认识,才能在科学应用过程中,不“规训”自然,“让科学适应环境”,而不是相反。“回归自然”、“顺应自然”,是“地方性科学”的根本。这能够使科学走出实验室,走向自然,去研究自然界中的对象和现象,获得自然界中的对象和现象的认识,然后再按照这样的对象和现象改造世界,以真正做到“按照自然的状态改造自然,不造成或少造成环境破坏”。
考察“地方性科学”,它与“第一种科学”是不同的。“第一种科学”以神话宗教自然观为基础,强调神启和先验,运用观察、猜测、思辨等方法去认识自然,在价值论上是“神学中心主义”的。而“地方性科学”以有机整体性自然观作为本体论基础,以证实、证伪等作为认识论原则,采用观察、实验、测量等具体的方法,以及复杂性原则、整体性原则、非因果决定性原则等方法论原则来认识自然,最终目的是认识自在状态下的自然,并据此改造自然,从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理念。比较这两种科学,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上虽然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地方性科学”与“第一种科学”有一个共同点,是“回归自然”和“顺应自然”的,体现了认识的历史性、时空限制性、当地性,因此,它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是有利于保护自然的。而且,由于“地方性科学”并不排斥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而是充分利用这两种方法对地方环境进行认识,因此,它对地方环境的认识就不像“第一种科学”那样,完全没有实验以及数学的认识形式,而有着相应的机理明确的认识。这样的认识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数理形式的、确定的和可重复的,能够更多地生产出相应的产品,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就此而言,“地方性科学”“超越”“第一种科学”。
相对于“第二种科学”,“地方性科学”也有其优势。它与“第二种科学”不同,不是以机械自然观作为其本体论基础,也不是一味运用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干涉研究对象,建构科学事实,制造实验现象,在“发明”的基础上去发现“制造”出来的对象和现象,而是更多地走出实验室,走向自然,发展直接面向自然的科学——“真正的自然科学”,进行野外实验,在“处理”自然、“观测”自然、“模拟”自然的过程中,发现自然的自在状态,并进一步获得对此的相应认识。这样的科学认识本身就适应自然,与自然本身相一致,进一步根据此认识去改造自然,就不需要像“第二种科学”那样“规训”环境,造成环境破坏,因为此时“科学已经适应环境”了。如对于农作物新品种的培育,“地方性科学”着力于那些既具有良好的品质和增产潜力,又能够更加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农作物,因为这样就既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也能够少施化肥、农药等,有利于环境保护。
通过这样的认识和行动之后,就不仅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性科学认识”,而且还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性产品”。地方性是多样的,甚至是无限的,因此,地方性科学一定程度上也是多样的和无限的,由此应用生产出来的地方性产品也是多样的甚至是无限的,它能在满足各个地方公众需要的同时,保护地方环境。
需要提出的是,这里的“地方性科学”的例子是关于农业的,没有涉及工业,事实上,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地方性科学”,满足的仅仅是人类的饮食问题,要满足人类其他方面的需要,还必须发展“第二种科学”。“地方性科学”并不完全否弃“第二种科学”,但是,它坚持,“第二种科学”虽然在实验室中是正确的,但是相对于外界自然界就不一定“友好”了,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地方环境影响。要判断将科学应用于外在自然时的“友好”,还必须以是否能够更多、更好地符合外在自然而同时又更少、更弱地造成地方环境破坏为标准。一般来说,造成地方环境破坏越少的“第二种科学”,它相对于外在自然的“真理性”和“友好性”就越强,反之则就越弱。因此,在“第二种科学”应用之前,应该“让自然做科学的最终裁判者”[24](P54),即运用“第三种科学”对“第二种科学”进行地方环境影响评价,以最终决定是否应该应用其于生产生活中。就此来说,“第三种科学”“监护”“第二种科学”。
经过上述“监护”后,“第二种科学”就与自然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成为“地方性科学”的一部分;应用后的“第二种科学”,就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工业产品,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能够保护环境。这是一种新的形式的工业,本质上已经成为“地方性工业”。“地方性工业”和“地方性农业”一道构成“地方性经济”。
这样一来,“地方性科学”既吸收了“第一种科学”、“第二种科学”的长处,又避免了它们的欠缺,从而能够使它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保护环境,达到生产与环保的双赢。
鉴于“地方性科学”与“第一种科学”、“第二种科学”有本质的不同,笔者称之为“第三种科学”。走向“第三种科学”,能够做到环保与经济的双赢,是可取的。
四、走向“第三种科学”“地方性科学”的意义
概括上述分析,“第一种科学”、“第二种科学”、“第三种科学”的特征及其差异可以列于下表。
表1 三种形式的科学的哲学基础、认识特征及其实践结果
|
科学类别 |
哲学基础 |
认识特征 |
实践结果 |
|
本体论 |
认识论 |
方法论 |
价值论 |
对象 |
场所 |
方式 |
结果 |
|
第一种科学 |
神话宗教自然观 |
神启、先验综合判断等 |
观察、猜测、思辨等 |
神学中心主义 |
自然界、超自然界 |
居所、野外 |
观察、猜测、思辨等 |
非数理形式、非重复 |
人与自然和谐、物质生产不足 |
|
第二种科学 |
机械自然观 |
实证性的真理性认识 |
观察、实验、测量、数学等 |
人类中心主义 |
自然界、人工自然界 |
实验室 |
干涉、建构、发明、制造 |
数理形式、可重复 |
物质生产充足、环境破坏 |
|
第三种科学 |
有机整体性自然观 |
实证性的非确定认识 |
观察、实验、测量、数学等 |
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中心 |
现实自然界
|
野外观察和实验 |
处理、模拟、顺应、发现 |
各种形式的综合 |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与环保双赢 |
从表1可知,走向“第三种科学”即“地方性科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不是“‘神学中心主义’的科学”,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还不是纯粹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科学”,而是兼顾自然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性的科学;它既避免了“第二种科学”“建构”、“规训”的特征,又能够“面向”、“顺应”各个地方的生态环境;既能够发挥“第二种科学”方法及其相关认识的优势,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又能够实现地方生态环境的保护。“第一种科学”与农业文明相对应,“第二种科学”与工业文明相对应,“第三种科学”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第三种科学”是对“第一种科学”和“第二种科学”的革命,是一次新的科学革命。这次革命不单纯使得那些原先处于边缘的科学,如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气象学、海洋学、土壤学、森林学等,走向中心,而且还以“地方性科学”对“第二种科学”进行“监护”,使此应用有利于保护环境。这应该是“第三种科学”最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第三种科学”还具有以下意义。
第一,“第三种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不仅包括那些脱离了时间和空间尺度限制的普遍性规律的认识,更包括那些具体化的、具有时空特性的或受着时空限制的、地方性的自然的认识;“第三种科学”关于地方性自然的认识是复杂的、甚至是不确定的,有些时候甚至很多时候并不呈现数理形式,重复起来也很难,不具有普遍性,只是相对于地方环境才有效,由此,它是地方性的、多元化的、时空限制的、反科学主义的。但是,它又坚持面向自然,去努力获得自然自在状态的认识,因此,它又是坚持实在论的。只不过,这样的实在论更多地是埃利斯意义上的“实用实在论”——科学旨在提供对自然现象最好的说明性解释(explanatory account),对科学理论的接受包含了它属于这样一种说明的信念。[25](P48-74)
第二,“第三种科学”不是不要科学认识者和改造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是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在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第三种科学秉承的是“万物是人的尺度”而不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自然为人立法”而不是“人为自然立法”。“第三种科学”是一种走向自然、面向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是一种融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保护于一体并协调一致的科学。“第三种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在“顺应”自然的过程中完成的,而“改造自然”又是在“顺应性地”“认识自然”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的应用就能够保护环境。而对于“第一种科学”,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对自然的认识的,“认识”没有从改造自然的“实践”中独立出来,故处于朴素状态且进展缓慢,据此改造自然,对自然变革的强度不大,破坏性也不大,能够保护自然。对于“第二种科学”,认识自然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改造自然是在大自然中进行的,两者是分离的、断裂的,认识自然成了一种社会建制化的活动,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由此使得在此基础上改造自然的广度、深度和强度都大大增强了,结果必然造成自然的破坏。
第三,“第三种科学”无疑具有地方性,它所获得的知识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不过,这种“地方性知识”既不同于 “第一种科学”之“地方性知识”,也不同于“第二种科学”之“地方性知识”,是一种非常类似于生态学那样的“地方性知识”,可以称为“第三种地方性知识”。与古代科学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相比较,它祛除了其超自然的成分,而让有机整体性的自然观作为其本体论基础,因此,它不是文化相对主义和真理相对主义的。与近现代科学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相比较,它摆脱了实验室场所的束缚,而直接走向多样化的地方环境,由此使得它由原来的实验室背景依赖走向自然环境背景依赖,自然环境是多样的、异质的、可变的、时空负荷的,因此,它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所获得的认识也应该是多样的、可变的、时空限制的,甚至是异质的。
也正因为如此,“第三种科学”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地方性的,是为地方服务的,而且也只有地方,才能够更多、更好地发展并且利用这样的科学。它能够充分地调动民族国家的积极性,利用自身主场优势,展开“地方性科学”研究和“地方性科学”应用,发展多中心、多主体、多形态的科学,进行地方性产品的设计、制造和消费,实现地方的繁荣富强;它能够使欠发达国家摆脱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近现代科学的先发优势以及普遍性、全球化特征对欠发达国家实施的奴役,充分地实现自身“地方性科学”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自大,尽快走出“后殖民科学”状态。这有利于打破目前西方科学或者近现代科学“一个中心”、“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得“地方性科学”呈现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对科学技术以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第三种科学”是面向各个“地方”或“当地”的,目的是获得对各个“地方”的认识。对于各个“地方”,当地公众与此紧密接触,他们或者传承先辈“地方性知识”,或者在日常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获得各种各样的关于当地的认识。这些认识虽然可能缺乏科学的成熟形态,但是,其正确性以及价值和意义不可否定,因为,作为科学应用的实践者和环境问题的产生者以及承受者的他们,对地方性自然的认识以及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常常比科学家更为直接和具体,甚至也更正确。此时的公众,或者可以作为直接的认识者进入相关对象的认识中,或者其认识可以而且应该更多地被科学家所重视。
这样一来,与公众难于参与的“第二种科学”有所不同,公众可以比较自然地参与到“第三种科学”的研究和实践中,成为发展“第三种科学”的重要力量。在这里,公众对自然的认识与自身生产和生活实践融合了起来,对科学的研究与对科学的应用融合在了一起,公众和科学家一道开展并推进“第三种科学”。这样的科学可以看作是“人民的科学”,是一种公众涉入的并且参与的科学。在这样的科学中,科学已经不再作为科学家的特权,公众已经不再作为“门外汉”而被拒之门外,公众和科学家已经作为一个联合体参与到人与自然复合体系的研究和实践中。如此一来,民主化就内在于“第三种科学”之中,“第三种科学”的民主化就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 吴国盛:《从求真的科学到求力的科学》,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1)。
[2] 杨庭硕:《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 Local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2016-9. http://www.unesco.org/new/en/natural sciences/priority areas/links.
[4] A. Kalland. Indigenous Knowledge:Prospercts and Limitations,In 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Criticl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Edited by R. Ellen,P. Parkes and A. Bicker, Oxford: Harwood Acdemic Publishers, 2005.
[5] 安富海:《论地方性知识的价值》,载《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2)。
[6] S. Krech. The Ecological Indian: Myth and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1999.
[7] P. Nadasdy. Transcending the Debate over the Ecologically Noble India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Environmentalism.Ethno History, 2005, 52(2).
[8] T.W. Luke. On Environmentality: Geo-Power and Eco-Knowledge in the Discourses of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ism, The Environment in Anthropology:A Reader in Ecology, Culture, and Sustainable Living.Edited by N. Haenn and R. Wilk,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2006.
[9] 罗意:《地方性知识及其反思——当代西方生态人类学的新视野》,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10] 田松:《博物学:人类拯救灵魂的一条小路》,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11] 吴国盛:《博物学是比较完善的科学》,载《中国中医药报》,2004-08-30。
[12] 刘华杰:《博物学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13] 江晓原、刘兵:《是中兴博物学传统的时候了》,载《中国图书评论》,2011(4)。
[14] 毛中秋:《中兴博物学——访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12 -26 ,A05 版。
[15] 江晓原:《中国文化中的博物学传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16] 吴国盛:《博物学:传统中国的科学》,载《学术月刊》,2016(4)。
[17] 余欣:《中国博物学传统的世界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12 -26 , A04 版。
[18] 余欣:《中国博物学传统的重建》,载《中国图书评论》,2013(10)。
[19] 刘啸霆、史波:《博物论——博物学纲领及其价值》,载《江海学刊》,2014(5)。
[20] 卡特赖特:《斑杂的世界:科学的边界研究》,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21] 瑟乔·西斯蒙多:《科学技术学导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22]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3] 肖显静:《实验科学的非自然性与科学的自然回归》,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1)。
[24] 肖显静:《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科学的非自然性、环境破坏与自然回归》,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12)。
[25] B. Ellis. “What science aims to do.” In P.M. Churchland and C.A. Hooker (ed.) . Images of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Toward “ the Third Kind of Science”: Local Science
XIAO Xian-ji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oward “the first kind of science” (ancient scientific tradition) is not feasible. Although it may temporarily be conductiv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cannot satisfy people’s material life need, and ultimately cannot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he “construction” (including the fact construction in laboratory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mathematical abstraction) and “discipline” (including the discipline in laboratory cognition process a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modern science (also known as “the second kind of science”), is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view of this, it is not feasible to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y developing “the second kind of science.” To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scientific application, we must change the nature of “construction” and “discipline” of modern science to make science “return to” nature, “conform to” nature, and vigorously develop the “local science”(also known as “the third science”) which directly oriented nature and studied on nature itself. Then the “anthropocentric” modern science w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local science, which is a relatively perfect science, whose idea i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Key words: modern science; ancient science; local science; econom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原发于中国人民大学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