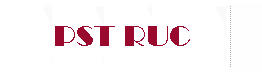摘要:波兹曼对技治主义的评论非常具有典型性。他分析技治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危害,指出当代技术与官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批评社会科学是技术统治工具和伪科学,提出以技术无神论应对技治主义的问题。波兹曼的分析是基于人文主义立场的,对于技治主义者和当代社会是必要的警醒,但用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专家的精英主义,忽视了技治主义进步的一面。
关键词:尼尔.波兹曼,技治主义,专家政治
Neil Postman’s Criticism of Technocracy
LIU Yongmou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Neil Postman criticizing technocracy is a kind of typical comment to American technocracy. Uncovering harms of technocrac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he insist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bureaucracy and modern technology. He argue that social sciences are technocracy tools and pseudo-science, that we should adhere to technological atheism against technocracy. From perspective of humanism, comments of Postman to technocracy are necessary warns to modern society and technocrats. In the mean time, positive values in technocracy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some sense, Postman’s critiques is a distinct case of humanities intellectual fighting for power with technology experts.
Key Words: Neil Postman, technocracy, expert politics
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当代公共决策和政治活动中的技治主义(technocracy)倾向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技治主义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并且分支、变种极多,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包括圣西门、孔德、凡勃伦等,核心立场包括:(1)科学管理(或称之为技术统治),即用科学思想和技术方法来管理社会;(2)专家政治(或称之为精英治国),即由接受了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包括社会技术专家)来掌控政治权力。[1]归根结底,技治主义的主旨是社会运行的理性化,尤其是政治运作的科学化。专家治国是技治主义的实践形式,实质是施行科学管理。换言之,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背景,还是人文社会科学背景,专家掌权若不不遵循科学思想、不运用技术手段、不依赖数量方法,则不算技治主义者。一般情况下,纯粹的人文学科专家由于对科学思想和技术方法的隔膜,很难成为真正的技治主义者。
技治主义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和机械主义色彩,因此一直被各家尤其是人文主义者所诟病。作为北美媒介生态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尼尔.波兹曼力主媒介生态学为人文主义研究。[2]他将技治主义称为社会工程学或唯科学主义,总体上对其持强烈批评的立场,但却呼吁精英控制社会信息传播,在反技治主义者中独树一帜。因此,对波兹曼的技治主义思想的研究,对于更深刻地理解技治主义乃至当代政治实践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从本质上说,波兹曼所称的唯科学主义大致等同于技治主义的主张。他将唯科学主义归纳为三者互相联系的观点:“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是,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第二个观念是,社会科学揭示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第三个观念是,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3]86-87前两个观念构成了他所谓“社会工程学”的基本立场,而后者则为他所谓“技术神学”的核心观念。波兹曼认为,社会工程学思想起源于18世纪的巴黎高等技术学院,可追溯到圣西门、安凡丹、拉普拉斯和孔德等人,主张运用实证化、经验化和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来实施对社会的工程化管理。后来兴起的技术神学思想把技术推到类似伊朗等神权社会中真主的至高位置,代替宗教成为当代社会的道德、意义和信仰的源泉,而把“精神治疗专家、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推上了新神父的位置。[4]因此,社会工程学是唯科学主义更为实践性、操作性的组成部分,而技术神学是唯科学主义中更为精神性、基础性的组成部分,力图将人的世俗事务和心灵事务一统于科学技术的权威之下,给社会工程学提供总体性、终极性和超越性的宏大诠释。与之相同,技治主义同样包含着由浅入深两个层面的含义:科学管理、专家治国更为具体,蕴含于其中的是将科学理性应用于整个人类社会,以将其建成为“科学城邦”的乌托邦理想。比如,技治主义创始人圣西门就主张组成各级牛顿会议,来代替教会来教育、管理和智慧所有社会成员。[5]总之,波兹曼所称的唯科学主义与技治主义是基本重合的。
技治主义在当代流行是有害的。首先,何为生命,何为人,社会工程学并不能回答诸如此类问题,更不具备鉴别不同答案背后标准的权威。波兹曼认为,唯科学主义要求科学回答类似问题,盲目接受科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归根结底“是一种绝望中的希翼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3]96。类似于科学的标准化程序根本无法为生命、人生和生活提供终极关怀和行为指导,实际上科学对此并不关心。其次,社会工程学危害人的主体性。波兹曼指出,“人的判断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歧义性是技艺的敌人。”[3]94因此,社会工程学要把人转变为可以测量、计算和控制的客体和控制对象,让人逐渐失去自信以及思考、判断的能力,将自身交给技术。最后,技术神学实际上在消解道德和信仰。波兹曼指出,技术神学用医学、精神病学、社会行为学等角度审视道德世界的问题,把罪孽、邪恶等传统道德概念转变成社会偏离、心理疾病等可以客体化和量化的技术概念。这从根本上消解了道德,技术专家们“服务的神灵不讲述公义、行善、悲悯或仁慈。他们的神灵讲述的是效率、精密和客观”[3]51。在当代社会,宗教世界在衰落,人们开始寻求替代性的道德权威,科学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但科学无疑担不起此任务。
更重要的是,波兹曼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的角度对唯科学主义的文化威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的角度,他把人类文化分成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6]孔德以及其他法国技治主义者思想的传播,尤其是泰勒、福特等美国技治主义者的努力,唯科学主义开始在美国流行,促成了技术垄断文化20世纪初从美国发端。泰勒提出技术垄断社会的主要预设:“即使效率并非人类劳动和思想的唯一目标,它至少是劳动和思想的首要目标;技术方面的精打细算总是胜过人的主观评判,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实际上,人的评判并非稳妥可靠,因为它受到粗疏大意、晦涩不清和节外生枝的困扰;主观性是清晰思维的障碍;不能计算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没有价值;公民的事务最好是由专家来指导或管理。”[3]30可以说,所谓技术垄断社会在实质上是技治主义社会。在其中,技术至上,技术对文化构成了致命威胁。波兹曼指出,“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太愚蠢了。”[7]文化不得不服从技术的权威,接受技术的指令,技术反对、压制和破坏一切与之不一致的文化因素,不断消解传统的符号和叙事。并且,当代技术压制文化对其进行反思,让人们沉浸在极端技术乐观主义的迷梦中。因此,波兹曼大声疾呼:“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3]自序,1-2
波兹曼深入分析了官僚主义与机器意识形态,指出了技术理性与官僚主义之间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一方面,他是从社会信息活动的角度来理解官僚主义的。他认为,官僚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由于政府管理领域不断扩张,而社会不断复杂化,社会管理方面的信息急速膨胀、复杂,于是政府引入官僚主义来应对管理信息泛滥的局面。“官僚主义原则上只不过是一系列技术工作的协调机制而已,意在减少需要加工的信息量。”[3]48官僚主义没有整体性、终极性的伦理关怀和政治理想,只有一个核心假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效率至上,按照可计算性和文牍中心两个原则来处理管理信息。官僚主义本来只是技术手段或工具层面的,但最终将服务于社会理想的一套技术方法转变成为凌驾于社会理想之上的超级制度,从工具僭越为目的。“19世纪官僚主义关注的主要是提高运输、工业和商品流通的效率。技术垄断时代的官僚主义挣脱了这样的限制,它声称拥有凌驾于一切社会事务的权威。”[3]49显然,官僚主义离不开各种技术和技术性机制。另一方面,他从反工具论的角度理解机器。在波兹曼看来,机器不仅是工具,背后隐藏着嵌入的理念即他所谓的“隐形机器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是机器力量的真正来源。这一观念类似哈贝马斯所谓的“隐形意识形态”[8],但波兹曼主要从人们忽视机器理念的意义上讲“隐形“,哈贝马斯则意指科学技术伪装成对既有制度保持中立。机器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包括:简单化,确定化,精确化,标准化,可观察,可计算,可操作等,这些均与官僚主义的追求是相吻合的。
当代技术的可能强化官僚体制,压制社会变革。波兹曼指出,技术在官僚机构的应用出现“动因漂移”现象。所谓“动因漂移”指的是当代社会将许多问题交给技术处理,因此当出现问题时,官僚机构可将责任推给技术设备,而掩盖官僚的责任。显然,“动因漂移”[3]65-66类似于鲍曼所讲的“道德漂移”[9],但前者讲的是官僚责任漂移到技术,后者说的是个体责任漂移到集体。正是动因漂移,官僚主义者拥抱技术,各种问题都被解释为技术升级问题或程序改进问题。比如,“电脑强化了官僚机构,压抑了追求重大社会变革的冲动,至少是产生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3]67
反过来,官僚主义支持技术的扩展。首先,官僚主义者在政治活动尤其是行政活动中大量引入各种“软技术”。波兹曼用测谎设备、民意测验、公务员考试等技术被官僚机构迅速接受和广泛应用,说明官僚主义对技术及其可操作化理念的认同。其次,官僚主义赋予技术专家以重要位置,将相当多公共决策权力转移给专家。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官僚本身即为技术型官僚。
波兹曼对官僚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是持警惕的态度的。首先,他不认为官僚主义解决了问题,因为官僚主义引入技术方法实际增加了管理信息量。其次,技术手段如电脑是打着提高效率的名义与官僚机构结合的,但是未必提高了机构效率,只不过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技术细节,把技术进步与机构进步乃至人类进步等同起来,而不是整体改进官僚机构。这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最后,专家们除了狭窄的专业领域,此外所知甚少,被赋予过高的位置。
波兹曼认为,社会科学实际是技治主义强有力的工具,试图按照技术原则、方法和规范来控制整个社会。社会科学在当代社会迅速崛起,正是借助唯科学主义、技治主义的力量。对此,他是不满的,甚至称当代社会科学为“神学”。[10]22社会科学不能以控制社会、管理人群为目标,否则社会技术实质就是为技术统治帮凶。
波兹曼指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媒介生态学等社会科学不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与人类智能无关的自然过程,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与人的决定和行动有关的实践,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如blink(眨眼睛)与wink使眼色的区别。自然科学力图寻找支配自然过程的不变和普遍的法则,而且假定过程之中存在因果联系。观察、量化和精确并非自然科学的排他性特征,实际上探案、商务和司法等许多活动都具有类似特征。实际上,社会科学自称科学与对自然科学的崇拜有关。社会科学总是重复着常识观点,但出于对数字的崇拜,用学院化的方法将常识量化和复杂化。但是,精确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问题难以起到实质性的帮助。波兹曼认为,社会科学努力成为伪科学(pseudo-science),一是要实现某种社会工程的业绩,这并不应该成为理论家的首要考虑,二是向争取社会给予自然科学的心理、社会和物质上的利益。
在波兹曼看来,社会科学是一种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形式,与小说类似,但又有区别。讲故事意味着作者给一系列人类事件以某种独特理解,通过给出例证以支持这种理解,并且,这种理解并不能被证实或证伪,其吸引力来自语言力量、解释深度、例证关联和主题的可信度,而不是来自真理或客观。讲故事意味着作者有一个可以辨识的道德目标,它受到时间、环境以及最重要的文化成见的影响。而社会科学与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1)小说是在叙述(narrative),社会科学是在阐释(exposition);2)小说家的故事是虚构(fiction),社会学家的故事是记录(documentary);3)19世纪小说是讲故事的主要形式,20世纪社会科学成了讲故事的主要形式,当代文化中有力的隐喻和图像大多出于社会科学家之手;4)小说注重细致描绘细节,社会科学讲求勾勒整体轮廓;5)小说专注于展示(show),而社会科学致力于解释(explain),更多地运用抽象的社会事实、推理、逻辑和论证。[10]28-31
波兹曼深入反思了语言技术、测谎技术、统计学技术、信用技术、成绩测验、教育技术以及管理技术等所谓具体的“软技术”或“隐形技术”(意思是很多时候人们没有意识到它是技术)的应用,它们实际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技术如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管理学。所有社会技术背后的意识形态支撑均为唯科学主义。它以科学思想和技术方法看待、干涉和改造人的世界,塑成了社会技术的一般标准。比如统计学技术。技治主义缺乏一套明晰的伦理,又排斥传统,却要寻求合法性的权威,只能求助于统计学的客观数字崇拜。波兹曼认为,用统计数字进行论证的要害有三:1)把某个抽象概念转变成某个客观的可测量的事物,如民意测验统计调查假定有个“舆论”或“民意”的客观事物,可以从民众身上抽取出来;2)排序即将个体按照某个标准安放在某个序列中;3)忽略未经或不可数字化的问题,让定义客观化和数字化,如智商测量中忽略想象力、联想能力的测试。显然,人类行为的抽象概念大多无法转变为可测量物,对于同一个对象有无数序列标准,不同标准背后又不同的预设,而要研究人,不能忽视不可数字化的东西,因此,统计技术是非常有问题的,却被广泛运用和神化。统计数字产生了大量的无用信息,造成信息的混乱。
当然,波兹曼并非完全反对社会技术的使用,而是反对技术的神化。“一句话,争论的核心不是技艺本身,而是应不应该让技艺高歌猛进,应不应该神化一些技艺,应不应该排除其他一些技艺。”[3]84很多时候,社会技术的使用往往已经僭越了它所服务的目的,成为独立自主的存在,甚至反过来压制使用技术的人。
面对唯科学主义、技治主义思想在当代社会引发的问题,波兹曼主张以技术无神论对抗技术神学,纠正唯科学主义、技治主义的错误。技术神学神化技术,“宣称通往天堂的路是技术创新”[11]。技术无神论不把技术看成神、主宰或终极关注,主张机器运算并不优于人类思想,技术思想不能主导信仰系统,世界是不可完全计算的,公民事务不应由技术专家负责。技术无神论对新技术持怀疑的态度,始终不忘记:(1)所有技术都是双刃剑,好处坏处同时存在;(2)新技术对不同人群影响不同,总是有利于一些人不利于另外一些人;(3)技术并非简单工具,每一种重要技术均包含着认识论的、政治的或社会的成见;(4)技术影响不是单一或局部的,而是整体性和生态性的;(5)技术是特定政治和历史语境下的人造物,但倾向于宣称自己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12]1-3
波兹曼的“技术无神论”并不成体系,实际包括一些零散的建议。第一,审视新技术,“对新技术提问”[13]。要对新技术的影响和效用进行深入的分析,消除社会中不必要的技术控制。波兹曼还提出一系列问题帮助人们审视新技术,包括新技术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谁的问题,产生什么新问题,如何解决新问题,何人和何机构因新技术而获得权力,新技术对语言有何影响,等等。“我们需要继续睁大我们的眼睛,我们许多人才能运用技术,而不是被它使用。”[12]8第二,加强技术教育,避免对技术社会影响的无知。波兹曼所指的技术教育围绕技术与社会、人的关系展开,而不仅是科学普及教育。技术教育主要让学生了解新技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教育学生如何使用技术而非被技术所用。[14]在中国的学科建制中,技术教育大体相当于科技社会学、科技史和科技哲学中有关技术尤其是新技术的内容。第三,社会科学研究非技术化,回归正确的道路。波兹曼指出,如果接受社会科学是讲故事的观点,社会科学则没有太多的局限,历史反思、哲学思辨、文学批评、案例研究、传记学、语义符号分析、人类学方法等都可以用于社会科学讲故事之中,恰恰不要过度地追求模仿自然科学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目标应该是:有益于人类理解和体面,重新发现社会生活的真实。波兹曼认为,社会科学只是“道德神学”(moral theology),不发现新的东西,而是重新发现社会生活中不断被阐明的真相,评论道德行为,最终促进人们理解和实践高贵生活。最后,要努力继承传统文化,反对当代技术垄断文化。技术成为当代文明的垄断性力量,所有非技术文化都受到压制。当代文化人要在技术垄断中自保,并且进而做抵抗技术垄断的斗士。
指责其为无视大众、贬低大众的精英主义,从民主主义的角度批评技治主义是很常见的意见。的确,技术与政治精英结合起来将变得异常强大,民主有可能在科学的名义下被破坏。然而,波兹曼并不是从精英主义的角度来批评技治主义的。虽然攻击专家地位过高,但他主要认为技术专家知识太狭窄不够全面,并非指的精英无权在公共决策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实际上,波兹曼的精英主义倾向很严重,为精英控制社会信息传播辩解,不怕被人攻击为威胁言论自由。[15]在他看来,公众面对电子时代的信息泛滥是没有分辨力、受人摆布的,只有寻求像他一样的精英的帮助。波兹曼不满的似乎是公众没有寻求他的帮助,而是寻求了技术专家的帮助。比如,他批评技治主义者托夫勒:“不要读任何未来学家的书,比如阿尔温·托夫勒。因为他们对现代技术了如指掌,却对人性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预言总是错误的。”[16]
实际上,这是用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专家的精英主义。波兹曼的潜台词是科学技术专家最好还是在自然事务中发言,人类事务是人文知识分子才有能力处理的复杂领域。事实上,尽管都被称为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技术专家之间在理念、目标、地位等各个方面均差别很大,并且对后者在当代社会中获得的权力和尊崇既羡慕又嫉恨。正如古德纳所言,所谓知识分子“新阶级的内部已经开始分化”[17]。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专家更多地与既有体制和政权相结合,而人文知识分子被相对边缘化,在知识分子两个不同部分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面对这种状况,一些人文知识分子试图放弃精英主义,与大众结合,从大众身上获得力量,而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无法放弃精英主义,只能在厚古薄今的叹息中孤芳自赏,如波兹曼对印刷时代的无限怀念。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上述所谓分化在于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
总体上看,波兹曼是从人文主义尤其是道德、信仰的角度来批评技治主义的。他并不讳言争做道德卫道士的立场。在他看来,所有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道德学,即以增进人类道德为目标,包括他从事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在内,媒介生态学的根本宗旨可以说是从道德、文化的角度反思技术尤其是传媒技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批评技治主义亦是一种常见的批评。这种观点认为,技治主义是机械主义,把人看成数字、零件,缺乏道德观念甚至是反道德、反信仰的,更忽视人的意义、价值和终极关怀;因此,技治主义导致社会冷漠、道德沦丧和信仰失落。应该说,这种批评是非常有道理,对于技治主义者是必要的警醒。
技治主义不能是民主的么?技治主义不能是道德的么?这是两个值得进一步剖析的问题。美国是公认的技治主义的国家,波兹曼亦如此认为,但谁能断定美国因此不是民主国家,因此而道德滑坡?这里的关键是技治主义可以定位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即操作方法层面和社会乌托邦层面。作为一种操作方法,技治主义可以为实现社会理想(如宪政)服务,提高公共决策和行政的效率,促进社会民主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乌托邦,技治主义试图建成科学城邦或机器社会,无疑对民主、道德、人文和信仰等具有颠覆性的破坏力。实际上,技治主义的乌托邦从来就没有被足够多的人接受,更不用说付诸实施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技治主义者试图将技治主义付诸实施,因而掀起了技治主义运动。但是,该运动很快就分裂,类似全盘颠覆既存社会制度进而重建所谓“技术人员的苏维埃”的激进乌托邦理想很快就被大多数技治主义者抛弃,而如社会测量、计划调控、能源调控等温和的操作措施则被坚持,并被当时的政府所采纳和吸收。因此,技治主义可以仅仅作为一种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理论,而不是宏大的贯穿性社会理想。当然,如此技治主义既可以和资本主义结合,亦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服务于既有社会制度的完善。实际上,从实际历史看,各种技治主义变种中,多数是定位于这个层面。无论如何,相对于封建世袭的权力分配制度来说,作为工具的技治主义主张以知识为标准来赋权,无疑具有正面意义。总之,波兹曼忽视了技治主义进步的一面,尤其是对于落后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永谋.论技治主义:以凡勃伦为例.哲学研究[J].2012, (3):93.
[2] Neil Postman.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J/OL]. [2010-03-18].
http://media-ecology.org/publications/MEA_proceedings/v1/postman01.pdf.
[3] 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 Neil Postman. Deus Machina[J]. TECHNOS Quarterly, 1992(4):20.
[5] 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M].王燕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3.
[6] 刘永谋.媒介技术与文化变迁:尼尔·波兹曼论技术[J].天津社会科学,2010, (6):31.
[7] 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4.
[8]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69-71.
[9] 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24.
[10] Neil Postman.Social Science as Theology[J].ETC, 1984(1):22-32.
[11] Neil Postman.The Information Age: A Blessing or a Curse? [J].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04 (2): 6.
[12] Neil Postman.Five Things We Need to Know About Technological Change [J/OL].
[2010-06-21]. http://www.mat.upm.es/~jcm/neil-postman--five-things.html.
[13] 尼尔.波斯曼.通往未来的过去——与十八世纪接轨的一座新桥[M].吴韵仪,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54-56.
[14] Neil Postman.End of Education: Redefining the Value of School[M].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5:190-192.
[15] 刘永谋.媒介编码VS社会控制:尼尔·波兹曼的信息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5):94.
[16] Janet Sternberg. Neil Postman’s Advice on How to Live the Rest of Your Life[J].General Semantics, 2005(6):155.
[17] 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M].顾晓辉,蔡嵘,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