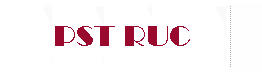作 者:王伯鲁 著
出 版 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3-1
页 数:213
简介: 《技术化时代的文化重塑》以技术化时代人类面 临的一系列挑战为背景,从对技术活动的哲学分析入 手,讨论了技术化进程与技术文化结构,揭示了技术 化时代的文化疾患及其根源,探讨了校正技术发展方 向以及重建技术文化的策略,着力描绘出重塑文化的 路径与维度。《技术化时代的文化重塑》笔者王伯鲁 既探究了技术化、文化疾患、文化创新等理论问题, 又讨论了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协同融合的可能路径与 模式,并制订了应对技术化时代挑战的路线和方针, 力图为人类的未来发展开辟出一条有光明前景的坦途 。
目 录
引 言
一、技术化时代的来临
二、技术文化的优势与缺陷
三、重塑文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第一章 技术的历史与逻辑
一、技术的历史发生
二、技术的认识之旅
三、技术的构成要素
四、技术的基本形态与体系结构
五、技术的基本类型
第二章 文化视野中的技术透视
一、文化及其体系结构
二、技术创造原则
三、功利价值观
四、技术精神的核心
五、技术的文化存在方式
六、技术的文化功能与价值负载
第三章 技术化的多维度解析
一、技术文化的演进动力
二、工具理性的膨胀
三、人的技术化
四、技术的内化
五、社会的技术化
六、文化生活的技术建构
第四章 技术化的文化疾患
一、文化的趋同化
二、技术与社会文化的裂变
三、科学技术的扩张与文化祛魅及僭越
四、技术化的人性压迫
五、“现实阱”的塌陷
六、风险社会之忧
七、技术困境之痛
第五章 文化嬗变及其根源
一、文化与技术的矛盾运动
二、现代技术介入文化的途径与机理
三、技术的那喀索斯隐喻
四、技术的资本化
五、功利价值观的缺陷
六、文化嬗变中的价值博弈
七、价值权衡中的认识难题
第六章 技术演进的文化校正
一、技术的反思与批判
二、技术的文化塑造
三、技术权力及其规约
四、技术异化之源及其消解
五、技术前沿的道德防线
第七章 技术文化的重建
一、技术的科学化
二、技术的人性化
三、技术的艺术化
四、技术的生态化
五、技术的民主化
六、开放包容的新型技术文化
第八章 文化重塑之路
一、文化的价值诉求
二、重塑文化之难
三、文化自觉与文化际盟约
四、文化创新的新课题
五、文化张力的恢复与重建
第九章 重塑文化的新维度
一、现代化的文化躁动
二、创建生态文明
三、新禁欲主义的兴起
四、教化德行
五、社会进步与体制创新
六、重建精神家园
七、人的协调健康发展
结束语
后 记5
作者介绍
王伯鲁,1962年9月生,陕西韩城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近年来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5部。
《技术化时代的文化重塑》引 言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现实,服务实践需要,始终是理论探索的出发点与基本品格。自工业革命以来,在资本扩张的裹挟下,技术与科学互动融合、合流并进,开疆拓土,日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当下,技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前所未有地扩张着,所以技术获得了决定现代人的观念、信仰的能力,并已到达这样一种地步:现在所有的行为都处于技术氛围之中。技术环境已经置换了以往的自然环境。”现代技术以目的性活动流程与人工物两种基本形态广泛渗入或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支持着文明的建构与社会的运行,塑造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乃至精神世界的面貌,把人类带入了技术化时代。
一、技术化时代的来临
“时代”就是基于事物的时间存在方式,对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历史时期的一种总体称谓。把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究竟命名为何种“时代”,主要取决于这一社会发展阶段或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唯有如此,这一称谓才能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当然,由于社会体系的复杂性、多层面性、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人们认识上的种种差异,对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称谓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多种“时代”称谓交错重叠、各行其是、并行不悖。这一状况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立体性,也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
作为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方式或机制,技术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或支点,是文明建构与文化发展的基本元素,渗透力极强,无孔不入。长期以来,技术突出地体现在社会生产尤其是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的演变中。“从事物的本性可以得出,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劳动资料或者说生产工具的发展上。”作为一种典型的技术活动,制造和使用工具是学术界公认的人猿揖别的分水岭,也是判定人类诞生的技术标准。由此可见,人一开始就是技术的人,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技术及其进化基础之上,重大技术成就自然就成为划分时代变迁的主要标志。“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通常所谓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合成时代,人力时代、自然力(畜力、风力、水力)时代、蒸汽力时代、电力时代、原子能时代,以及口耳相传时代、鸿雁传书时代、有线通讯时代、无线通讯时代、数字通讯时代、网络时代等称谓,就是分别从材料、能源和信息角度,对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技术特征的揭示。
事实上,技术不仅体现在生产工具上,也不只是存在于生产领域,而是以流程技术形态与人工物技术形态活跃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不仅有生产技术,而且也有管理技术、医疗技术、军事技术、司法技术、贸易技术等形态,千姿百态,不胜枚举。可以说有多少种人类目的性活动,就有多少种具体技术形态。不难理解,技术是人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人就生活在技术的建构与应用之中。然而,人的所有活动并非都是技术活动,或者说技术活动并非人类活动的唯一方式。尽管众多社会文化活动都以技术为基础,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归并、还原为技术活动,从而抹煞其丰富内涵与本质差别。同样,技术活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本能性活动向技术性活动演变,从低级技术活动向高级技术活动进化,由不自觉的技术活动向自觉的技术活动转变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化进程。
基于不同社会领域的标志性技术成就,对现时代的各种称谓就有很多种。例如,网络时代、多媒体时代、克隆时代、机器人时代、太空时代、高技术时代等。这些称谓虽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现时代的一些技术特征,但它们多是表面的、片面的、暂时的,并未触及现时代技术活动的灵魂与深层内涵。笔者认为,以“技术化时代”称谓现时代最为贴切、恰当,最能反映现时代发展的总体特征。这主要是基于如下三点理由而提出的:一是技术的全面快速发展。虽然学术界在技术发展测度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大,但是技术的全面、快速与加速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可以从专利申请量、新产品数量的增长率、交通工具速度的提升中直接感受到。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生活节奏加快、新技术形态大量涌现、技术更新换代周期缩短等事实,也间接地反映了这一点。
二是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多层面影响向纵深推进。技术系统纵向上的构成性与横向上的相干性,使任一技术成果都会通过技术世界网络向外扩散,引发一系列的相关技术变革。技术成果的结构层次越低,普适性、单元性越强,所引发的技术变革往往就越剧烈。事实上,以各类产业技术系统的建构与运行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活动,最先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生产与生活对技术及其创新依赖性的加深,技术进步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正在向纵深推进,由物质层面向精神领域渗透。例如,下一代人对供电系统、供水系统、通讯网络、交通运输工具等技术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了上一代人。不难理解,今天只存在技术影响大小、深浅不同的社会领域,而不存在不受技术影响的社会生活。
三是工具理性主义盛行。工具理性就是以理性方式对目的性活动效果、效率与模式的自觉追求,或者说是理性在功利与经济维度上的集中体现,表现为合乎理性的手段创建与自觉选择。事实上,围绕如何有效地实现目的这一现实课题,人们总是在已有知识、技能、经验和资源的基础上,凭依理性禀赋千方百计地展开探索、构思、设计与建构,进而创建和改进实现各类目的的具体技术形态。“技术已经为合理性创造了一个新定义,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它强调功能关系和数量。它的行动标准是效率和最佳标准,即利用最便宜和最省力的资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理性最终被当作一种合作协调的智力,当作可以通过方法的使用和对任何非智力因素的消除来增加效率。”工具理性上的盘算与建构,不仅是技术活动的基础和灵魂,而且已演变为当今理性的主流形态。
由此可见,现代“技术的可能性和后果是如此无所不及,一切事物如今是如此地打上了技术的烙印,而技术的发展速度又是如此令人咂舌,以致于使人感到,在技术的许诺本身的同时,出现了对人类及其未来的可怕威胁。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在现时代,技术视野已成为人们审视万事万物的一种基本理念,技术建构及其创新已成为人们应对各种挑战的一种思维模式或习惯,技术活动日渐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正如贝尔所言:“这个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了。机器主宰着一切,生活的节奏由机器来调节……这是一个调度和编排程序的世界,部件准时汇总,加以组装。这是一个协作的世界,人、材料、市场,为了生产和分配商品而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组织的世界——等级和官僚体制的世界——人的待遇跟物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工作中协调物件比协调人更容易。”今天,无所不能、无往而不胜的技术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社会的技术化进程全面、深入而有序地展开。“技术化时代”已悄然来临,人类生活因此而正在或即将发生深刻的变革。
二、技术文化的优势与缺陷
在现实生活中,技术与文化水乳交融、难解难分,只有在思维领域才可能把它们分离开来。从根源上说,目的性是构成理性的要素,也是人有别于其他物种的主要标志。目的与手段是反映人类活动方向与过程的一对范畴,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互相转化。一般而言,目的通过手段实现自身,手段又通过目的展现其价值;一个目的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实现,一种手段也可以用于实现多个目的;此时此地的目的可以转变为彼时彼地的手段,反之亦然。
从本质上说,技术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围绕“如何有效地实现目的”的现实课题,人类不断创造和应用的目的性活动序列、方式或机制。在漫长的进化发展历程中,人类始终面临着衣、食、住、行、用等物质文化需求,以及安全、信仰、幸福、求知、审美、自我实现等精神文化需要。这些需求既是人类各种目的性活动的起点和归宿,也是社会生活展开的轴心。其实,不同时代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人类基本需求的变化,而主要在于这些需求实现方式上的差异。正如马克思所言:“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里的“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就是生产技术的具体内容,它直接决定着物质生产与社会需要的实现样式,进而也间接地塑造着社会上层建筑与精神生活的面貌。
源于物质文化需求的人类基本目的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代实现这些目的的路径及其手段各有千秋而已,进而衍生出复杂而庞大的各类技术族系。例如,单就实现“出行”需要的运输技术而言,人类就先后创建了以骑马、马车、帆船、火车、轮船、汽车、飞机、飞船等为标志的众多技术形态。这些技术形态都能实现“位移”的目的,为人们的顺利出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选择,所不同的只是效果(规模、场合、舒适度等)与效率(速度、成本、安全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可见,技术研发活动并不满足于实现目的的已有手段,而是力图尝试和创建效果更好、效率更高的更多手段,以更切合实际、更符合个性需求的方式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在技术化进程中,技术效果的拓展及其技术效率的提升空间很大,技术的未来发展不可限量,没有终点或止境。
技术发展史表明,任何技术形态的创建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障碍。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会形成多条目的与手段的转化、延伸链条,以及纵向上不断分化派生、横向上相互交织融合的技术族系,进而催生出枝繁叶茂、繁荣昌盛的技术文化。在日趋庞杂的技术体系建构过程中,也会不断派生出众多衍生目的。如何实现这些目的?如何创建和驾驭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技术体系?日渐成为现代社会生活展开的轴心。在这里,原初目的的简单性与技术体系及其建构的复杂性之间的对立,常常会颠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主从关系,发生本末倒置,使技术体系的创建与运行转变为社会实践的中心任务,喧宾夺主,甚至使人们忘却原初的目的。“这种有效的技术活动,由于它的内在合理性,就有可能变成目的本身。在极端情况下,目的不再决定手段,反而是现有技术手段决定所要实现的目的。”今天,围绕新产业、新技术产品展开的市场培育与开拓,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不就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吗?
近代以前,作为人们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方式或机制,技术依附和从属于众多其他社会文化形态;近代以来,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技术才逐步演变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由于新技术形态在实践效果与效率方面的优势,使技术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现时代,逐步演变为一种强势文化形态。同时,由于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基元性、通用性与渗透性,因而在社会生活诸领域展开的各类竞争,最终都可以归约、转化为新技术开发上的竞争。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技术与科学已经取代了传统神话和宗教,而转变为现代社会中一切现象赖以合法化的基础。当今世界,技术已发展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或综合国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技术上的竞争。技术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都会引起经济的深刻变革与社会的巨大进步。这就是说,与其他文化形态相比,技术文化具有单元性、根源性以及明显的竞争优势,日渐成为现实生活的基础与轴心。因此,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只有那些注重新技术研发,优先采用新技术的组织或个人,才更容易在竞争环境中获胜和得到发展。这里也不难理解,竞争的社会环境对各种文化形态都具有明显的选择作用,当今技术文化的繁荣就是这种选择机制作用的直接结果。
然而,技术文化的繁荣以及其他人文文化的式微都是极其危险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单一化与人性的扁平化,是现时代文化“疾患”之根源。作为一种具体文化形态,立足创造、注重实效、鼓励多元、宽容失败、精准可控的技术精神是贫乏的,繁琐、刻板、僵硬的技术规范是冰冷无情的,难以提供人类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丰富的文化营养。更为严重的是技术文化所彰显的工具理性,正在抑制、排斥甚至吞噬价值理性与意义世界,排挤或替代人类对其他目的、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从而导致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精神生活源泉的枯竭等文化疾患。正如舒尔曼所指出:“必须生活于只相信技术、不相信任何其它东西的状态之中的人,失去了他的意义。‘因此,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些年,虽说是人类历史所已经知道的最为技术化的年代,同时也是最为空虚的。’”米切姆也强调:“科学的技术之臻于完善导致唯一的现代问题是:进行想象和产生希望的能力将会枯竭或消失,而正是这种自然产生的能力首先说明了人的思想创造的原因。……人们缺乏想象力,技术是‘一个空的形式——像最形式化的逻辑那样;它不能决定生活的内容。’科学的技术专家依赖于一种他不能控制的根源。”
由于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祛魅作用,处于膨胀之中的科学文化、技术文化正在摧残着传统文化中富有想象和魅力的部分,消解理想、信念、正义等终极的、高贵的价值追求,泯灭人性中最可贵、最本质的探索性、创造性和批判性品质。而当初正是依靠这些天赋品质与发达的价值理性,人类才逐步踏上了文明发展之路,才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文化成就。不难理解,技术文化的畸形发展是可怕的,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就像遮天蔽日的蝗虫,它们飞到哪里,哪里人们的精神的嫩芽就都全部被啃光,啃得连根都不剩。失去了精神性的人类的心目中只有金钱、金钱、金钱,而金钱之下覆盖的即是完完全全赤裸裸的人类的动物本性。”这也是技术文化危险性之所在。
这里还应当指出,技术化必然导致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促进目的与手段链条的不断分化和延伸,使处于其中的个体的知识与技能单面化、碎片化、零件化,从而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工具理性主义与技术文化,以应对日益技术化、专业化的事务性工作;同样,技术化也容易促使人们只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对终极目的、远大理想与崇高价值的追逐。愈益深化的社会分工促使人们以更狭隘的职业并入社会分工体系之中,生活在一个过程或环节的片断中,从而失去了对整个技术链条或体系的把握,乃至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正如一个分工明确的盗窃团伙成员在法庭上所作的辩护:“我只管监视主人的出入”、“我只管开门”、“我只管搬运值钱的东西”、“我只管销售交给我的东西”等。虽然“马仔”们可能被“大哥”蒙蔽或利用,单个行为不一定构成犯罪,但他们之间的有机结合却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犯罪链条。可见,技术化时代的人们生活视野趋于狭窄,对传统意义与价值的认同愈来愈模糊,追求远大理想与宏伟目标的热情也逐步降低,而被迫把有限的精力转移到学习和掌握不断翻新的各类技术模式上,从而更容易为工具理性所控制和主宰。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三、重塑文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现时代,畸形发展的技术文化犹如失去天敌,而又获得了良好生长条件的外来物种,快速繁殖和蔓延,挤占了其他文化形态的生长空间,进而导致文化生态系统失衡,给人类的生存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正如芬伯格在概述技术实体理论时所指出的,现代“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新的文化体系将整个社会世界(Social world)重新构造成一种控制的对象。这个体系具有一种扩张性活力的特点,它将最终侵入每一块前技术的飞地(pretechnological enclave)和塑造社会生活的整体。因此,总体的工具化就成了一种天命,我们除了退却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回归传统或简朴才能提供一种对进步的盲目崇拜的替代形式。”可见,技术化时代的文化危机与挑战,是现代人必须认真思考和积极应对的重大历史与现实课题。
由于技术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处的基础地位,因而它的社会影响多是根源性、派生性的。人们很早就觉察到技术文化的危害性,不过他们所看到的危害主要是指向人类德行的。例如,春秋末期的庄子认为,技术建构违背自然,技术功效容易激起人们的贪欲与投机心理,腐蚀纯洁的灵魂,不利于人们安身立命。事实上,在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轻视技术的价值倾向。“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和人生信条。在读书人看来,以追求经济效果或效率为核心的各类器械的制作与操作技艺,只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工匠们应当熟悉和掌握的。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雕虫小技、奇技淫巧、毫末之艺,难登大雅之堂,无益于求取功名和实现人生理想。尽管知识分子追求功名的过程也离不开技术的支持,但他们却仍然主张应当远离技术活动,自觉抵制技术对德行与理想的侵害。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是较早关注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命运的思想家之一。早在工业革命之初,卢梭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弊端,指出科学技术进步总是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道德的普遍堕落。
事实上,近代以前,由于技术发展缓慢,加之技术的基元性、潜在性、渗透性以及对人类其他文化活动的依附性,技术一直未能从其他文化生活中分化独立出来。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出现,以机械化、蒸汽化为核心的产业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伴随着工业技术体系的复杂化、精致化,在资本、科学与分工的推动下,技术研发才从工业生产以及其他社会生产领域中逐步分化出来,踏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技术文化形态。正如拉普所言:“由于技术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必然影响人的思想感情。在工匠技术阶段,这种影响只是现存文化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从此一切活动的目标都变成以最短时间最少耗费产生最大的效益。由于采用技术手段与科学方法,这条原则带来了更大的‘成功’。寻求更完善的手段最终必然成为一条规范。”
技术文化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强势地位,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根源的,主要应归因于人性的贪婪与竞争的社会文化氛围。源于人类生命过程的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欲壑难填的本性促使人类更多更快地获取实际利益,而技术正好是更多更快地获取利益的基本路径。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来自不同阶级、阶层、团体之间的利益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就形成了竞争的社会环境。先进技术形态在效果与效率方面的明显优势,一方面会促成竞相研发或引进新技术的社会动力,占有和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也会排挤那些对于赢得竞争没有直接帮助的文化形态,使其逐渐失去发展动力和社会资源。这就是技术发展的合理性与统治逻辑。
社会发展史表明,众多传统文化形态虽有助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的安定和谐,但与社会竞争力之间往往缺少必然的正向相关性,而技术文化却与竞争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相干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与残酷结局,迫切要求人们不断强化竞争实力,而工具理性与技术文化正好迎合了这一社会需求。这就是技术文化繁荣以及强势地位确立的社会根源。在中外历史上,文化落后的野蛮民族战胜文化发达的先进民族的事例屡见不鲜,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前者的工具理性与技术文化发达,军事实力较强,而后者往往价值理性与人文文化发达,军事实力或战争准备往往不足。赫梯人攻占古巴比伦,斯巴达人战胜迈锡尼,秦国兼并“六国”,罗马人征服希腊城邦等历史事实,概莫如此。可见,在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中,技术文化多以正反馈机制推进,从而拥有其他文化形态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发展潜力。
技术文化的畸形发展容易导致人文价值与意义世界的失落,使人类陷入深度的迷惘与危机之中。在技术王国里,人们将不再顾及价值与意义层面上的判断,代之而来的则是带有强烈功利主义色彩的技术理性判断;人们往往只重视短期的利益与效用,而忽略人类的整体性存在及其崇高理想。当今的社会生活完全依赖于庞大的技术体系以及技术化的社会运行体制,技术风险与生活的不确定性,使个体的盲目感、孤独感与无力感加剧,邪教与迷信等非理性活动盛行;现代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工作与生活节奏加快,使人的肉体和精神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压力;欲望的膨胀与消费主义文化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危机、文化冲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正困扰着现代人。因此,“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现代人就生活在这一精神家园破败衰落的文化危机之中,而单纯依靠技术文化是注定不可能拯救人类的。正是基于对文化危机与人类命运的担忧,当代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才提出了长期萦绕在他心头的“霍金难题”:“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动荡的世界里,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100年?”
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都表明,人既有适应客观现实的受动性,也有努力改变生存现状的主动性;人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创建者。因此,从根源上说,当今技术文化的畸形发展与文化危机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重塑文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如下三条理由:一是对技术文化的批判与质疑。在从庄子、卢梭、马克思、韦伯、海德格尔到马尔库塞、芬伯格的历代思想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批判技术异化的主线。虽然思想界对技术文化的批判和质疑不是社会主流,但自古至今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世界各国都开始反思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与技术发展模式。人们把众多现实问题与挑战的根源普遍归结为科学与技术的快速发展,甚至出现了反科学、反技术的思潮。对技术文化的反思、批判和清算,是一种抑制技术文化畸形发展的力量,也是我们重塑文化的出发点和动力之源。
二是价值理性的觉醒与复兴。在现代化进程中,尽管以工具理性为支点的技术文化畸形发展,而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人文文化相对衰落,但是两者之间的张力却始终存在。这一方面反映了人文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与价值所在,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人文文化复兴的希望。价值理性力图恢复理性的“人性”本质,重视人生、人性、人本及其意义,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及其价值。随着价值单一、内涵贫乏的技术文化缺陷的暴露,人们普遍意识到价值理性的觉醒与人文精神的回归,才是医治当代文化“疾患”、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柱。这也是我们今天重塑文化的思想基础。
三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实践经验。近几十年来,针对技术文化畸形发展所引发的文化危机与时代挑战,人们并没有只停留在认识层面上,而是在建设精神文明的旗帜下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展现出社会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共中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施纲要》、《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举措,都有助于推进人文文化的繁荣、人性完善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动对真、善、美、智、圣等多元价值的追求。尽管这些文化重塑工作仅仅是初步的、点滴性的,但是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重塑文化的宏伟工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Carl Mitcham,Robert Mackey,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Techn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3,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