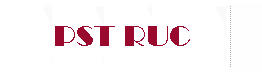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摘要] 当下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另类科学哲学家异军突起。费耶阿本德、罗蒂、福柯等另类科学哲学思想,共同指向对正统科学哲学的解构,揭示了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动向。另类科学哲学主旨不同、基础迥异,视域、论域和方法均有突破,与科学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向人文的变化,表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气息。应关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另类眼光,在科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人类学、科学文化哲学以及科学伦理学等领域扩展科学哲学研究。
[关键词] 另类科学哲学;正统科学哲学;费耶阿本德;罗蒂;福柯
[作者简介] 刘大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刘永谋:哲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
对于哲学尤其是20世纪哲学之发展,科学哲学起到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9世纪、20世纪两次世界性的实证哲学运动中,科学哲学都是始作俑者。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正统科学哲学的兴起、传播和学科化,一些科学主义理念成为流行的共识,从哲学领域散播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人类知识部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活动。
在中国,科学哲学在近现代思想启蒙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初震撼中国思想界、哲学界的论著如《天演论》等,多属科学哲学。五四时期,对中国思想开放和哲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外国哲学家是杜威和罗素,他们先后在中国本土对知识界和公众作了“五大演讲”,这些内容广泛的演讲,核心也是科学哲学。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高举科学旗帜,疾呼打倒“玄学鬼”,其科学观大多偏向急进的科学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哲学一度比较沉寂,发展比较缓慢,但改革开放后又迎来了新的繁荣。科学教育是拨乱反正的前沿,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特别有生命力和吸引力,成为中国哲学界最重要之“理论生长点”。
经过近30年的成长,正统或“标准的”科学哲学已然壮大,在中国也可以说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科学哲学的另一种倾向也渐渐兴起,它们多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可称之为“另类科学哲学”。五花八门的另类科学哲学,彼此的取向往往相左,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正统科学哲学之解构。毫无例外的解构虽然在当代引发了诸多困惑,但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若干观点和思路也不无意义。无论如何,都应当认真地去对待它、审视它,汲取精华、消弭困扰。
一、另类科学哲学家的异军突起
30多年前,费耶阿本德曾经说,科学哲学是一个有着伟大过去的学科,并暗示科学哲学是一个没有将来的学科。[1](P124-136)如果从正统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或许可以说,今天的科学哲学正在衰落,甚至是在终结自身。对科学的哲学反思虽然异彩纷呈,新的视角、新的主题不断涌现,但正统科学哲学研究正在逐渐丧失其所谓正统地位,仅仅成为多元化探讨中的一极。那些与正统进路迥异、旨趣不同的新研究,或是问题域,或是应答域,却早已突破了正统的局限,极大地改变了科学哲学的基本形相,已然成为气候。
相对正统或标准而言的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最显著的表征是有影响的另类科学哲学家及其科学哲学理论受到学界的重视。如果把卡尔纳普、赖欣巴赫、亨普尔等人作为正统科学哲学家的代表,把波普、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看作从正统到另类的过渡人物,那么,费耶阿本德、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罗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人应当说就属于另类科学哲学家。他们有的在时间上平行于正统的科学哲人,也有的晚于正统的科学哲人,但近年都在科学哲学界制造话题、引领潮流。另外有一批活跃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当代学者,例如阿伽西、苏珊·哈克、海丝等人,虽然不属另类,却是深受另类科学哲学家影响,而走出科学主义营垒、向人文主义蜕变的别开生面的科学哲学家。在此,列举三位最为典型的另类科学哲学家——美国的费耶阿本德、罗蒂,法国的福柯,他们堪称对科学哲学改变最为重要的另类学者,以便粗略地描画另类科学哲学的“精神气质”,从而引入对另类科学哲学之思考。
1.宣称“告别理性”的费耶阿本德
费耶阿本德为人并不特立独行,但其思想的批判性和冲击力却是无与伦比的。他早年深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是一位狂热的实证主义者,后来又受到维特根斯坦和波普的影响,最后却既反对逻辑实证主义,也反对波普,成为“科学最坏的敌人”,被称为异端。早期的费耶阿本德主要关注科学理论的解释问题和经验主义问题,20世纪70年代经由科学史研究转而关注科学与社会关系和自由问题的研究。费耶阿本德主张一切传统都属于历史传统,推崇对科学的历史主义研究,否定逻辑主义。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费耶阿本德批判了科学沙文主义,指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于科学发展是有害的,科学不是人类知识的唯一形式,要打破科学的垄断地位。他认为,科学只是人所发明以便应付其环境的工具之一,绝不是唯一的知识形式,原始巫术、神话、宗教和形而上学也包含丰富的知识。他甚至认为:“科学是今天的神话,神话是过去的科学。”[2](P48)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费耶阿本德批判了经验主义,指出在科学史上没有任何理论是与事实完全一致的,经验论把经验作为知识基础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任何经验都离不开理论和主体性。费耶阿本德认为,现代经验主义已经陷入困境,“即从反教条主义精神及其进程中引入的有些方法(指经验方法——引者注)必会导致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建立,以及使形而上学免受实验检验要求排斥的机械保护主义的建立。”[3](P69)费耶阿本德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理性主义,指出科学史的实例表明各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方法论对科学发展的说明都是不适当的,甚至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他认为,科学远远超出了大多数当代理性主义者所解释的“理性”的狭隘范围,它并不受这个“理性”的束缚和限制。费耶阿本德还批判了波普、拉卡托斯的证伪主义,无情地否定了证伪原则,认为“一个严格的证伪原则,或者像拉卡托斯所称呼的素朴证伪主义,就会消灭我们所知道的科学,而压根儿就不允许它出现。”[4](P176)费耶阿本德还极力反对“专家治国”,要求将知识分子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清除出去,主张外行干预科学活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自由社会。费耶阿本德主张科学与国家分离,防止科学对自由的干预和侵害。实际上,后期的费耶阿本德从对科学、哲学的批判最终转向了对人类自由和幸福的思考。
费耶阿本德以“反对方法”和“怎么都行”著称。在对科学史细致、严谨的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费耶阿本德创立另类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和多元主义方法论。他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一切方法论都有局限性,必须放弃方法一元论,采取发散式、开放式的方法多元论;科学是一种自由的实践,科学发现并没有绝对的规律可循,科学一直在利用非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来丰富自己。他写道:“看看实际的历史情况,我们就会知道,科学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发展着,科学的问题也被许多不同的方法所抨击。在实践中所遵循的不变的唯一原则应该是:怎么都行。”[5](P 118)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首先体现的是一种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民主的科学精神,反对学术上的独断专横。费耶阿本德发现,传统科学哲学把科学变成一种神话,并把自然科学的优越性归结为科学特殊的方法论体系,这对于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他说已有的科学方法虽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认为科学必须照此办理,那就适得其反了。当然,并不是要把科学哲学所肯定的已有的理论和方法一概否定,而是说任何方法,即使在科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也不能将其作为教条、程式化的东西。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选择,包括对现成的方法要敢于不用,甚至否定。费耶阿本德更为强调的是科学的个性,而以往多是强调科学的普遍性和工具性。一个科学家搞科学要注重其个性,太强调科学的工具性、抽象性和普遍性不利于科学的进步。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并不是不要方法,而是要多元方法和自主选择;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警惕一元方法论 ——“我没有说认识论应该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或科学哲学应该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我说这两门学科应该把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药予以接受。认识论现在有病,必须予以治疗,而药就是无政府主义。” [6](P139)与传统科学注重精确性不同,费耶阿本德认为模糊性更能确保变化。他指出,粗糙的对错二分法是以忽略特殊和细节为代价的。费耶阿本德认为自己既不是理性主义的也不是非理性主义的,因为理性和非理性的划分本身就是两个极端,而在两者之间还应有更多的可能选择,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和多元主义方法论就是其中之一。
费耶阿本德在科学哲学界独树一帜,以所有理论的批判者和科学哲学的终结者自居。有评价说:“他是理性主义者,但他的观点对理性主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是一个实在论者,但他的学说给实在论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同时,它又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他并不倡导一切形式的相对主义。”[7](译者的话)他既反对方法又主张多元方法,既反对理性又不主张非理性,风格既像古希腊的智者,又具有后现代主义因素。总之,人们对费耶阿本德褒贬不一。费耶阿本德对科学哲学的贡献是独特的和突破性的。在他那里,科学的各个矛盾的特征显现得一览无余。无可否认,他使科学哲学走出逻辑主义和不那么彻底的历史主义,从而迈向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反科学主义。这对正统科学哲学是瓦解性的,但也由此启迪人们打开思考科学的各种新思路,展现了一个宽阔的视野。
2.提倡“后哲学文化”的罗蒂
罗蒂同样是在分析哲学传统中成长起来,同样对分析哲学传统反戈一击,并据说因此不见容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罗蒂的反叛以对维特根斯坦之后的语言学转向的思考为开始,而以宣称哲学的终结即主张一种“后哲学文化”为其旨归。与费耶阿本德相比,罗蒂不仅要反叛分析哲学,更是要反叛整个西方哲学传统,这是柏拉图以来延绵不断的传统,力求超越意见的真实知识、发现现象背后的绝对实在。罗蒂认为,西方哲学传统的根本精神体现于“自然之镜”的隐喻之中。按照这个隐喻,人类知识就是准确的表象,认识论就是研究如何保持这面镜子的“光洁”以确保表象的准确性。然而,在罗蒂看来,所谓“心身问题”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假问题,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一个称之为“心灵”的分离之实体,从而打碎了“自然之镜”,动摇了认识论的基础。罗蒂指出,康德之后,传统认识论的发展开始背离基础主义,进入20世纪又遭到塞拉斯、奎因等人的重创。按照“自然之镜”的线索,罗蒂质疑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他认为,虽然分析哲学以语言代替心灵或意识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把语言理解为“作为构成信念和欲望的媒介,即介于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第三要素”[8](P 20),并没有彻底放弃柏拉图主义的非历史性绝对实在的迷梦,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知识论所面临的难题,破除表象主义的魔咒。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罗蒂主张以非还原的物理主义来代替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构建一张反复编织的信念与欲望之网来代替“自然之镜”。罗蒂强调“隐喻与信念之网的编织”,认为在彼此联结的众多信念和欲望之外,并无独立的心的存在;心灵本身就是诸多信念和欲望彼此交织的巨大网络,认识并非是心灵对于心外之物的再现;某个具体信念的真伪对错实际取决于信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联结方式。[9](116)这是一种融贯论、整体论的真理观。
罗蒂进一步把研究的问题从认识论扩展到伦理学和政治学,这种扩展的结果就是主张“后哲学文化”。罗蒂认为,当下哲学已与传统哲学根本不同,以维特根斯坦、杜威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一些大陆哲学家具有共同的历史主义立场,以及拒绝非历史的永恒化之旨趣,应该把美国哲学与大陆哲学在实用主义的主题之下联合起来,这种结合最终会产生后哲学文化;这种后哲学文化的建构将真正破除表象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摧毁哲学的真理垄断地位,最终使哲学走下神坛,重觅自身之位置。[10](序)在罗蒂看来,在后哲学文化中,我们并不能解决传统哲学提出的问题,而是对这些问题采取淡漠和搁置的态度。后哲学文化不是建构性的,而是诊疗性的,或者说对话性的。通过哲学研究不能认识世界本身或世界的本质,更不能获得认识活动和认识者本身的本质。因此,后哲学文化中的哲学不能再作为基础,揭示由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提供的认识论主张。“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被挑出来,作为样板来说明(或特别不能作为样板来说明)文化的其他部分所期望的条件。”[11](P14-15)在这种文化中,没有哪一个文化部门具有特权,哲学、科学、文化、政治等文化部门都是平等的,我们“不再崇拜任何东西,不再把‘任何东西’视为具有准神性,从而把所有东西——我们的语言、良知、我们的社会——都视为时间和机缘的产物。”[12](P35)当然,后哲学文化中也不会有任何所谓(大写的)哲学家,没有人能主持理性法庭去审查其他的文化领域,只有(小写的)哲学家即某些能够理解事物如何联系的专家。
罗蒂的科学哲学融合在他对“后哲学文化”的建构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之中。他反对那种盲目崇拜科学的科学主义,反对将科学作为整个文化的基础,尤其反对将科学的成功归功于坚持独特的科学方法;认为在奎因、塞拉斯和戴维森那里, 分析哲学超越和取消了自身, 哲学的科学化和寻求确定性以失败而告终。 因此,科学已经不再是整个文化效仿的榜样,也并非接触实在的惟一途径。罗蒂认为,在传统的观念之中,科学和真理基本上是等价的,科学因此获得了人类其他知识部门无法比拟的崇高地位,成了一切人类知识的基础,但这些都是误解,“自然科学的这种神化作用,是当代西方哲学逐渐在使自己摆脱的若干观念之一”[13](P15);科学家在现代社会中似乎成了一种新的牧师,不仅科学家不能占据特殊的地位,任何人都没有这种特殊地位,从事不同文化领域的人在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罗蒂主张采纳一种所谓“培根主义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着重强调科学作为技术的先导和基础作用,注重科学的技术功能和实用主义,注重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在此基础上,他转向实用主义,倡导一种超越科学主义的“对话的哲学”,反对基础主义,反对科学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试图消解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并使之融合。因此,有评论说:“罗蒂对自然科学的特点的解释完全是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实用主义的,它拒斥一切‘深度’的解释。他根本不想探究自然科学为什么如此成功。”[14](P146)总之,罗蒂的科学哲学是对追求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之“强理性”的反动,反映了整体主义、有机论的复苏,以及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传统的强烈愿望。
3.致力于“对主体解构”的福柯
福柯名气很大,其人举止乖张,其文主题冷僻,其思惊世骇俗,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另类。福柯哲学的主线是对主体的解构。之所以福柯选择了彻底解构主体的立场,是因为他认为现代哲学强调主体、张扬主体,其实是对主体的迷信,而现代西方社会一切问题的都可以溯源到对主体的迷信。这些问题既包括理论问题即现代哲学、现代思想的混乱,也包括实践问题即现代实践观、现代伦理的混乱以及个体在现代社会被齐一化规训的历史处境。福柯认为,“不存在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主体”[15](P19),与之相连的人性观念也“不是一个科学概念”[16](P217),两者都是“在19世纪初被建构起来的”[17](P430)。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给解构主体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尤其是微观权力分析方法。福柯运用考古学和谱系学对主体以及主体哲学进行了历史和社会两方面的解构。对主体的历史批判,集中体现为福柯的“知识型”理论。福柯运用考古学分析了400多年西方思想史,指出主体是一种现代才出现的历史性观念,描述了主体的诞生和消亡的历史,得出了主体必将、也正在“死去”的结论。福柯指出,他所有的研究就是要揭示“在我们文化中把人变成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18](P271),这个过程实际就是现代知识-权力“生产” 现代人的过程。福柯引入谱系学的起源分析方法,即微观权力分析法,将研究的主题从知识转向权力,揭示主体与知识、权力之间的深层关系。在福柯看来,现代人是“把人变成主体”的结果,现代人本质上是个体被知识-权力彻底奴役的产物。“把人变成主体”的过程通过区分、规训与主体化三种方式,现代科学、现代知识将社会变成控制机器,使现代人自愿接受科学和知识的统治。正是现代知识和权力建构了作为主体的不具差异性的现代人,因此,福科提出了反规训、反主体化的解放方案,即“局部斗争”和“生存美学”。
福柯从科学史开始其哲学研究,其科学哲学研究则以主体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知识问题只是福柯研究的起点,福柯哲学最终指向知识背后的人特别是现代人的真实历史境遇。在解构主体的主旨之下,福柯知识研究既不同于科学认识论,也不同于传统科学史研究。按照福柯的表述方式,福柯的知识研究“贯穿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这条轴线”,而“并不贯穿意识―知识―科学这条轴线”[19](P204)。相对于科学认识论,它从实践的角度看待知识、科学,即把它们看作一种实际展开的历史活动,关注的是知识是如何取得知识的称号的,而不关注知识的合理性问题。相对于科学史研究,它是从话语角度来看待知识、科学,即把它们看成按照一定形成规则组成的话语群中的一类,不关心科学(从“前科学”、“非科学”中)的诞生问题,而关注话语的形成问题。福柯用知识考古学取消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否认科学的进步性和真理符合论,强调不同时代科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又将谱系学的微观权力分析方法引入知识研究,破除了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认识论观点,指出了知识实践相对于主体的自主性方面,尤其强调了知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深入地剖析另类科学哲学的意蕴,比较它与正统科学哲学之异同,对于揭示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动向是十分必要的。从费耶阿本德、罗蒂和福柯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另类科学哲学与正统科学哲学相比,主旨不同,基础迥异,视域、论域和方法均有突破,与科学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总的说来,另类科学哲学表现出更加宽容、平等和多元化的气息。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实际上是当代科学哲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和转向的表征。
1.当下科学哲学研究基础的转向
从20世纪60、70年代始,科学哲学的发展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逐渐偏离了正统科学哲学的路线。其后愈演愈烈,概而言之,当下科学哲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变化。
(1)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向历史主义、社会学化和“后哲学文化”。在科学哲学的诸多流派中,通常把波普的证伪哲学之前的诸流派称为逻辑主义,将其后的流派称为历史主义,波普哲学则可以视为由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化的中间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逻辑主义主要是对科学做静态逻辑分析,历史主义则是对科学做动态发展研究。由于库恩、费耶阿本德和劳丹等人的努力,历史主义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并且进一步向社会学、文化学方向演化。可以说,当代科学哲学已偏离了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即不再纠缠于科学的意义标准、逻辑结构、发现与辩护的区分这些认识论问题,而是指向科学背后的人类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一般哲学问题。比如,海德格尔对技术的研究,哈贝马斯对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研究和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等。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试图研究实际科学史,描画真实的科学历程,科学史案例也愈益受到重视。科学哲学的社会学化可以追溯到默顿,在他之后,科学社会学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分支,最近兴起的知识社会学更是把社会学的方法应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分析。另一方面,文化哲学的研究也是如火如荼,比如,罗蒂提出的“后哲学文化”强调科学、艺术、哲学和政治等彼此平等,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不再是独立特行的,而要和对其他文化样式的哲学研究交织在一起。
(2)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消解和多元主义的兴起。随着唯科学主义的退潮,坚持自然科学有其客观基础的基础主义、坚持自然科学通过外部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本质主义受到人们置疑,把自然科学知识视为客观真理、把科学发展看成线性积累和持续进步的观点正在动摇,对数学和物理学的推崇正在减弱。研究方法从着重建构转变为对基础主义和一切绝对化倾向的解构。在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时代,科学哲学试图从对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中建构科学认识的一般标准、规范和方法,并且极力主张用科学认识的基本模式改造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人类知识。而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则努力探究作为选择之一的自然科学模式之具体的、历史的建构过程,消解自然科学的作为认识模式的必然性、唯一性和特殊性。另类科学哲学的态度,根本上不是说已有的东西有问题,拿个新东西来替换,而是认为理论和方法是一个发展过程,是永远不可能完全确定的,只能在不断否定中暂时确定。随着多元主义对科学哲学的逐步渗透,自然科学越来越被看作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对科学的认识论研究也越来越成为诸多哲学反思中的一种。对科学的总体立场从唯科学主义到温和的科学主义、到各式各样的调和观点、再到反科学主义,是越来越多元化了。
(3)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后现代性的“解构”方法渗入;研究目标从偏爱行动、追求可操作性转向某种对科学文化体制的诘难和社会批判。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以胡塞尔的晚期作品《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为出发点、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和解释学方法用于解决科学哲学问题。此后,结构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影响越来越大,解构主义方法渗入科学哲学,极大地改变了科学的哲学基础和主流科学观,改变了传统的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正统科学哲学将自然科学知识视为人类知识的典范,不仅强调其真理性,而且强调其行动性和操作性;不仅要推广自然科学的认识模式,而且要推广基于自然科学的实践模式;不仅要科学地改造自然,而且要科学地改造社会乃至人自身。但是,随着解构的流行,对自然科学的诘难越来越多,科学哲学就不再仅仅是为自然科学辩护的学科,而逐渐变成与科学有一定距离的旁观者。由于人们确认已不可能按照程序化来解决眼前一切问题,所以,偏爱行动、追求可操作性目标也不再压倒一切,某种对科学文化体制的诘难和社会批判反倒成为时尚。
(4)从论题的角度看,当下科学哲学的视域、论域越来越多元化,研究旨趣也转向科学、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首先,在另类科学哲学中,科学被理解为决定人类本质的本体性存在,语用学被引入科学哲学,科学成为与“上下文”相连的整体,对科学知识的理解、解释和应用具有不可或缺的情境依赖性。其次,与正统科学哲学强调自然科学价值中立、只关注自然而不关注人相反,另类科学哲学重新把科学看成人的科学,把科学世界看成是人类世界的一部分,科学世界及其与生活世界的关联进入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区域。再次,科学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实践活动和文化现象。在正统科学哲学中,科学基本被看成知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构规范的、无矛盾的体系。而在另类科学中,科学首先是实践,是在一定目标指导下改造世界的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即文化。最后,在世纪之交,自然科学正在走下神坛,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消解两者之间的鸿沟成为当代科学哲学一个重要问题。毋庸讳言,唯科学主义是正统科学哲学之“精神气质”,从研究旨趣上可以说,正统科学哲学是维护自然科学传统的社会研究体制的“意识形态”,科学与人文的两分是基本的科学哲学观念。但是,当下科学哲学却正以更大的包容性、甚至用自我反省的态度来看待自身。科学的发现本来也就是人文的发现,所以不能拘泥于唯科学主义之科学观,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成为时代的主题。
科学哲学在当代发生如此重大变化有着深刻的学理和社会文化背景。从学科内部发展历史来看,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建构出一劳永逸的经验证实原则,虽然几经修正最终还是陷入了困境。波普提出了证伪原则,极富创造性和想象力,然而经验证伪并不是清晰明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以及“不可通约性”理论,非难了自然科学线性积累和持续进步的乐观主义。费耶阿本德提出“怎么都行”,使得从方法上为自然科学的独特性进行辩护受到致命一击。至此,正统的核心问题都在消解、变形,自然科学至上的正统科学哲学教条基本上不再牢靠。从整个哲学发展形势来看,英美哲学阵营与欧洲大陆哲学阵营正由分立逐渐走向对话、交融。一方面是英美科学哲学开始汲取大陆哲学的有益营养,典型的比如罗蒂哲学、劳斯的科学政治学;另一方面,大陆哲学家逐渐重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典型的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哲学、海德格尔技术哲学和法国科学史研究开始成为科学哲学的组成部分。从更广泛的科学、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哲学的新动向与其说是哲学演进的结果,毋宁说是科学实践在文化上反思的结果。没有自然科学的兴起,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便很难成为声势浩大的哲学的运动,正统科学哲学更难以成为20世纪哲学界的显学。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从17世纪以来,我们就发现,今天所说的哲学处在一种变化了的情势中。面对科学,它开始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证明;而且直到黑格尔和谢林去世的整整两个世纪中,哲学实际上是在对科学的自卫中被建构起来的。”[24](P5)但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负面效应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两次大战和今天的资源短缺、生态危机,惊醒了沉浸在唯科学主义迷梦中的人类,对科学的质疑开始大行其道。另类科学哲学的新动向及其“反科学”倾向与其说是对正统科学哲学的攻击,不如说是对科学负面效应的反思。
2.当下科学哲学的另类眼光与研究扩展
我们的时代,既是全球化的时代,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时代。当下科学哲学迈出了多元探索的脚步,围绕科学展开的任何哲学反思都是可能的。今天的科学哲学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科学本身,而是“穿越”科学指向社会,指向更一般的哲学问题,比如自由、价值、存在等,可以说出现了某种“从科学出发的哲学”的趋势,盛行一种另类眼光。从审视科学出发,走向超越科学:费耶阿本德钟情自由问题,罗蒂转向文化问题,福柯探讨现代人的历史性生存,等等。总之,一切皆有可能。
具体到中国,科学哲学作为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基础地位固然不变,但是,科学哲学面对的问题已经改变,科学哲学的态势和视野也不复从前。一些正统科学哲学时代不被认同或尚未成型的分支,典型的比如科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人类学、科学文化哲学以及科学伦理学等,正在或已经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
(1)科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古代经典问题是世界是怎么的,近代哲学问题是人们怎样认识的,当下哲学更为关注知识本身之意义与背景。因此,认知科学成为认识研究的主导,即由原来认识论的怎样认识转到对认知进行科学的心理、生理分析,并对传统的空洞论证持批判之态度。科学的知识论是认识论受到普遍置疑的基础上对知识论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知识论摒弃了认识论中的先验倾向,把知识研究转变成知识实际产生过程的经验研究。比如说,认知科学利用心理学、生理学、逻辑学和哲学等多种方法研究人脑如何产生观念、知识,而不再论辩这些观念、知识是否是真理。实际上,当下科学的知识论研究倾向于超越纯粹的哲学思辨,变成综合了各种方法的、围绕知识问题展开的、典型的跨学科研究。
(2)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取得重要的成果和学术地位,比较有影响的学派如强纲领SSK,代表人物有布鲁诺·拉图尔、卡林·诺尔-塞蒂纳、马尔凯、巴恩斯等。其主要观点被称为“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跟其他知识形态并无本质的区别”,“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物,必然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25](译者前言,P2)与此相关,随着人类学的方法对现代发达社会的研究的关注,科学以及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也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比如人类学家特拉维克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研究。[26]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开始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的社会性质,比如拉图尔对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27]SSK重视科学实验室的田野调查,学术环境和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如科学家共同体的范式、科学家的思想、科学技术政策、科学技术的资源分配、行政管理和知识界的科层制等问题,都是哲学层面关注的对象。
(3)科学文化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支配性文化样式,从而与社会的其他文化传统特别是人文文化之间产生了冲突和矛盾,因此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引起了科学哲学界的关注。科学的文化哲学,就是将科学看作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但它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局限于认识论研究,因此既不同于传统科学哲学,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哲学。科学的文化哲学的代表作品有斯诺的《两种文化》、约瑟夫·阿伽西的《科学与文化》、安德鲁·皮克林的《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以及小李克特的《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等。这两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医存废的争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以及弗雷恩颇受关注的话剧《哥本哈根》,均属于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的范围。
(4)科学伦理学。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首先,与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研究逐渐发展成大规模、大建制的“大科学”有关。科学活动的社会性越来越明显,科技体制的功利色彩越来越浓厚,科学的价值中立性受到人们的置疑,科学逐渐被认为具有很强的价值负载,渗透着伦理判断。因此,科学的伦理学研究不仅研究科学家道德、社会责任问题,还开始关注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科学价值负载问题、科学无禁区与技术有责任问题。其次,当代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宇航技术和材料技术等飞速发展并广泛应用,给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比如核武器伦理问题、信息伦理问题、克隆人伦理问题、器官移植伦理问题,等等。新科技从总体上改变了人类生活,给人类生存带来了难以预计的威胁和困惑,使得科学的伦理学重新思考科技实践与伦理重构之间的互动。再次,20世纪的科技发展逐渐在社会层面显现出其致命的负面效应,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过剩等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危机,引发了科学的伦理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环境伦理、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关注。
当然,诸如此类研究的扩展,不仅要坚持“一切皆有可能”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追踪当代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而且要从实际出发,谨记研究的时空背景。面对另类科学哲学,重要的既不是盲目跟风,也不是一味排斥,而是恰当地回应。
参考文献
[1]《科学哲学:有着辉煌过去的学科》,载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 [3][5]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76
[25]迈克尔·马尔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Reflection on Alternative Philosophy of Science
Liu Da-chun Liu Yong-mou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100080;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00081)
Abstract: A prominent phenomena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has been the unexpected uprising of alternativ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is thesis analyzes in depth such alternative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as Paul Feyerabend, Richard Rorty, and Michel Foucult, summariz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lternativ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so as to unveil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 is viewed that with different theme and foundation, alternative philosophy of science has made break-through in terms of scop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its relation with science has shifted to be humanism-oriented, with more diversities presented.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alternative perceptions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could be expanded into fields of epistemology of science and cognitive science, of sociology of science knowledge and science anthropolog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culture, as well as science ethics.
Keywords: alternativ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ul Feyerabend; Richard Rorty; Michel Foucault; 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