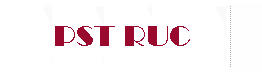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J.C.亚历山大在《新功能主义》中宣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政治结构已经可见端倪。……那些一向处于边缘的运动和集团正取得中心地位。”1990年前后,治理兴起,但似乎很少有人在分析治理的理论渊源时提到功能主义及其社会系统论基础——人们更喜欢将之归功于福利国家的失败、市场失败、新公共管理运动等等更表浅的原因。这种现象在近几年终于有所改变,一些学者在寻找“一般(general)治理理论”或“一般治理模式”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功能主义,回到了社会系统论。这似乎表明,社会系统理论就是具有一般性和统合性的治理理论基础。
一、治理理论的两本新手册
经过约30年发展,治理理论愈发丰富:2010年,知名学术出版机构赛奇邀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科学系的马克.贝佛领衔,召集了国际上39位权威专家汇编出版《赛奇治理手册》(The SAGE Handbook of Governance,Bevir,2010),整理出网络政策理论、理性选择理论、解释理论、组织理论、制度理论、系统理论、元治理、国家-社会关系、政策工具与治理、发展理论和治理测评等11种理论。多则多矣,却给人以杂乱之感。比如,解释理论和系统理论更像是哲学而不像是“治理理论”,而理性选择理论和发展理论等更像是治理理论的基础,而不“直接”就是治理理论。
6年后,另一知名学术出版机构爱德华-埃尔加邀请了贝佛的同事克里斯托弗.安塞尔和雅克布.托芬担当主编,汇聚全球63位作者编写出版《治理理论手册》(Handbook on Theories of Governance,Ansell & Torfing,2016),将治理理论细分为理论基础、理论分析模型和治理形式三类:如将集体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公共管理理论、规划理论、国家理论、民主理论、公法与监管理论、发展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等作为治理的9种理论基础,将商谈理论、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作为10种理论分析模型,将民主网络治理、合作治理和元治理等作为11种治理方式;该书还将系统控制(steering)和学习等作为11种基本概念。这表明,国际学术界已经初步意识到:要想对治理理论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必须在洞察其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对各种治理理论进行分类、分层。这是第一步。
二、两种最新的“一般”治理理论(模式)
要想走出治理理论的“复杂丛林”,还必须将理论基础进一步提炼浓缩,找到更具基础性、总括性、统合性的理论,由此出发才能发现主要线索,寻找到正确的出路。在这条探求基础之基础的道路上,贝佛用《一种治理理论》(A Theory of Governance,Bevir,2013)表明他依然走在前列。该书从后预设主义(postfoundationalism,一译后基础主义)的意义整体论出发,用历史主义、建构主义去批评理性的、正式的机制、制度和规范,用分化理论(Decentered theory,一译去中心化理论)的多元性、随机性、叙事性和谱系性来批判实证主义现代治理的物理化和形式化。上述哲学引导贝佛将国族(民族国家)、网络、市场以及由它们形成的(联邦)国家统统都看成社会组织,治理于是就成为人的有意义的活动的叙事,是一种语言游戏、表演(实践)游戏、管理游戏,具有实践的(practices)而非制度的(institutions)型式( patterns)。公共组织(行为)从官僚政府转向网络和市场,国家权力于是分散在空间和功能上不同的网络之中,这导致治理型式日益多元、随机、复杂。系统治理可以通过对话、参与、协商共识、授权和社会包容应对这种复杂性,其具体方法,就是通过政策级联(policy cascade)形成系统性的交叠制度,使网络社会保持有效结构。虽然我们不认同贝佛站在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上指责治理实践的实证主义和工具论倾向,但他由哲学到社会再到政治,由社会观到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值得关注,其中对理想化的系统治理理想的现实状况分析也颇有价值。贝佛宣称该书用整体意义论构建了“一般(general)治理理论”,在我们看来是从历史人文主义走向了系统治理。
另外一条指向社会系统理论的路径,是理性选择的新制度主义。比如,以《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Peters,1996)和《没有政府的治理?》(Peters & Pierre,1998)享誉治理学界的彼得斯和皮埃尔,在经过《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制度理论》(Peters,2011)的三版修订后,用《比较治理》(Comparative Governance: Rediscovering the Functional Dimension of Governing, Peters & Pierre,2016)宣布要以系统治理回归帕森斯(Parsons,1975)和默顿(Merton,1957)的功能主义。与帕森斯注重体制性结构的、相对僵化死板的规定性功能(Stipulated Functions)相比,彼得斯和皮埃尔将核心放在了过程上,尤其是组织的决策过程、决策功能,这就使得“系统性治理功能,应急性(Emergent Functions)功能具有动态性,代表着政治系统的自适应过程”。这就回到了西蒙的组织系统论。而我们知道,西蒙深受巴纳德社会系统理论影响。虽然彼得斯等站在偏经验主义和工具理性立场上对功能主义和系统治理的分析相对简单和粗糙,但他通过交互治理研究回到社会系统论值得肯定。彼得斯和皮埃尔宣称从系统性的功能主义出发构建了“一般治理模式”,在我们看来是从理性实证主义走向了系统治理。
三、治理理论的两条主要线索及其共同基础
两种构建一般性治理理论的雄心,分别来自历史人文主义和理性实证主义两个不同的方向,最后都回归到了社会系统理论。这背后隐藏着的两条主要线索,代表治理理论的两大干流,值得我们认真梳理。
第一条是关乎治理基本社会观念的社会系统理论,其根源可追溯到马克思、齐美尔和滕尼斯社会结构论;其直接起点是颇受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影响的帕森斯(1937/1955)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系统论,中间经过默顿和塞尔兹尼克(Selznick,1957)等关心社会心理层面的自然系统视角的组织理论(Scott,2007)的铺展,目前对治理理论影响最大的是卢曼功能-结构主义系统论(Luhmann,1964/1984)——库伊曼社会动态系统治理(Kooiman,1993/2003)和梅茨将治理归结为自治的调整和控制机制(Mayntz,1993/2004)等均受卢曼自我复制思想启发。这条系统社会观的主线还勾连着罗茨(Rhodes ,1996)自组织网络公共行为的程序性新形式,希克斯(Hicks,2002)整体治理,奥斯本(Osborn ,2010)和摩根(Morgan ,2015)之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新公共治理。泰思曼等将复杂系统理论对治理观的影响归结为非线性动力学、自组织和合作进化(Teisman &Buuren & Gerrits,2009),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复杂性研究与治理理论的关系,不足之处在于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而忽视动态稳定和本征机制等系统论精义,偏重分化和自组织,将自由主义理想化。
第二条干流是在经济和政治学界影响很大的理性选择学派,其间接源头是深受帕累托《普通社会学》和亨德森内稳态系统观影响,受帕森斯社会行动研究影响的巴纳德(Barnard,1938),其核心思想是西蒙自适应系统观。西蒙受巴纳德启发提出有限理性满意决策与选择理论(1945/1997),这一理性系统视角被斯科特(2007)称为组织理论基石;其后继者马奇和奥尔森《制度新探》(March & Olsen ,1989)在借鉴威廉姆森(1985)交易成本学的基础上,对复杂决策过程所做的制度主义阐释,是治理理论兴起的重要标志;威廉姆森《治理机制》(Williamson ,1995)深化、细化了治理理论研究。奥斯特罗姆(Ostrom,1990)关于集体行动制度的实证分析和彼得斯(2001)的弹性化交互治理机制亦属这一治理方法论行列。
以上两大干流均以帕森斯和巴纳德社会系统理论发端,交叠发展演变,最终都落脚到新制度主义的机制研究。抓住社会系统理论及其派生的理性选择理论这两条主线,我们就从社会观和方法论上基本厘清了治理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脉络,并且能够将组织理论、集体行动理论、新制度主义、商谈理论、网络政策、合作治理和其他理论勾连而成治理理论的整体体系。社会系统理论,是理解治理及其制度的关键,是治理最主要的、最具统合性的理论基础。
(本文简版以《治理理论研究的两种进路》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