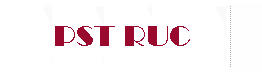摘 要:近五十年来深刻影响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潮流,即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在科学哲学中践行这种经验主义新建构的主要有新实验主义、科学实践解释学、新经验主义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四条路径,它们均具有建构主义的哲学特质,并与传统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区别巨大。经验主义新建构所引发的哲学变革,包括从理论优位转换为实践优位、对实验活动的重新定位、以及知识地方性的上位等。但在经验主义新建构中,诸如如何看待科学进步,如何看待科学的基础性和本质性,如何看待科学的现象和规律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关键词:建构主义 经验主义新建构 科学哲学
作者:刘大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100872);赵俊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科学认知活动总是离不开观察和实验,因此,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不可能不强调经验的作用。孔德的实证主义是这样,20世纪以来科学哲学的各个流派莫不如此。应当说,基于科学知识的后验(非先验)特征,经验主义容易被看作一切科学哲学的底色。然而,如何在某个科学哲学流派中进行经验主义的建构,实际的演变进程各个不同。人们比较熟悉的有以卡尔纳普、亨普尔和波普尔等为代表的逻辑主义建构方式,有以库恩、拉卡托斯、劳丹等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建构方式。此外,与之不同,还有什么特别有影响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呢?本文试图根据近50年间科学哲学的重要进展,讨论我们称之为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
一、科学哲学经验主义新建构的主要路径
与逻辑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建构方式相比较,当代一些科学哲学流派的不同在于:具有某种建构主义的特征,并采用新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性,突出科学实践活动的建构主义本质。当然,这种经验主义新建构可能有形形色色的路径,就现有材料的分析而言,在过去五十年,主要的路径是:新实验主义路径、科学实践解释学路径、新经验主义路径、科学知识社会学路径。 它们让当今的科学图景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
(一)新实验主义路径
新实验主义是运用建构主义的理念来建构一种新的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重要路径之一。与传统科学哲学过分看重理论和观察相比,新实验主义强调实验在科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独立地位。
强调从实验中为科学寻找一个相对可靠基础的趋势,通常被称为“新实验主义”(New Experimentalism),有时也被称为“科学实验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Experimentation)。“新实验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伊恩·哈金(Ian Hacking)、德博拉·梅奥(Deborah G. Mayo)等。哈金是新实验主义的开创者,梅奥为之进行了精致的哲学辩护。新经验主义的主要论题是:实验的物质实现、实验和因果关系、科学-技术关系、实验中理论的角色、建模和(计算机)实验、使用仪器的科学和哲学意义, 其讨论以实验的建构方式为中心。
在《表征与干预》中,哈金指出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用于证实理论的观察只是实验活动的一部分,而实验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实验有其自己的生命”。由此哈金开启了科学哲学的新实验主义进路:实验可以独立于理论为其自身的合理性辩护,并成为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对获取实验数据与实验知识的真实过程的分析,为探讨科学中的证据、推理等问题开创了新方向。新实验主义者认为,法拉第电动机和赫兹发现电磁波等案例表明,实验并不总是以检验理论为目的,也不一定依赖理论,实验者可以在独立于高层次理论的情况下开展受控实验,并通过实验本身证明实验效应或其所产生的新现象的存在。
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梅奥等通过对科学实验案例的剖析展开了对实验的科学哲学研究。梅奥指出,包括归纳逻辑与主观贝叶斯主义在内的确证理论都以理论为主导,实际上是对科学推理的事后重建,新实验主义则聚焦于标准误差分析等真实实验层面所使用的局部统计方法。由此,她提出了“通过错误论证”或“从错误中学习”的论证模式。“通过错误论证”的要义在于:对于一个假设H,没有找到某个可能的错误,就意味着对H的检验。这一模式强调,经过严格的错误排查之后,可以证明错误已经消除,并以此作为待检验主张成立的证据。更进一步而言,只有当一个主张经受住实验的严格检验——该主张各种可能错误的情况得到研究并被排除之后,才能说它为实验所支持或证明。在具体的实验中,据此论证模式,只有在查明一个主张可能为假的各种情况下某现象或结果极不可能出现,才能指出该现象或结果使这一主张得到了严格的检验并因此得到确证。
(二)科学实践解释学路径
科学实践解释学,也是运用建构主义来建构新的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一种重要路径。在充分吸收欧洲大陆的解释学传统和英美的分析哲学传统的基础之上,它对科学实践进行了更为丰富和细致的讨论。
美国新一代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是科学实践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Scientific Practice)的主要代表,他对“实践”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强调实践优位,认为科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科学实践具有权力维度。
首先,劳斯赋予“实践”更基础的概念地位,即一般意义的科学实践。在他的眼中,所有科学活动都是实践,这包括话语实践、科学实践、实验实践和实验室实践。与哈金等一样,劳斯对实验实践尤其关注,他认为实验实践是真正体现科学知识的地方性、情境性和反现代性特征的活动。在这里,实践不再是传统科学中与理论对立的概念,而是更为基础性或者更为底层的概念。劳斯赋予“实践”更基本的意义,以至于它将理论研究视为一种宽泛的活动而纳入到实践领域中去了。
其次,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他坚持实践优位,认为“实践有其独立于理论的生命”。传统科学哲学将理论摆在优先地位,“理论解释学是一种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实验和观察附属于理论,只有在理论的情景中才有意义,因此它们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仅仅发挥一种工具性的作用。然而,劳斯认为,实验设计虽然部分服从某种模糊的理论,但更多地是受实践本身的调整,也正是在实验的调整中,模糊的理论模型得以精确化或者具象化。实验能够建构现象,以及科学家对建构赖以进行的实验室工具性情境的理解,是很难被纳入到理论优位的科学发展图景中的。
再次,在对科学实践的分析基础之上,劳斯认为科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传统科学观认为,在实验或其他方式中形成的某种理论,一旦形成就具有脱离具体情境的普遍有效性,而这些普遍理论的具体应用才是地方性知识。显然,这种知识观建立的基础是表象主义的理论,而这是劳斯所不赞成的。劳斯认为,我们在实践中获得的首先是地方性知识,经过标准化,将这种知识由一个地方转译到另一个地方,从而形成普遍性知识。地方性知识经过标准化(使用条件的宽泛化)而成为一种形式概念的普遍知识,若要想在另一个地方应用这种知识,必须重新基于普遍知识情境化的条件,才能获得其在该地方的可理解性。
最后,传统科学哲学往往不谈论权力,而劳斯却认为科学实践具有权力维度。劳斯在对实践概念的分析中指出:“实践因此只在反对抵抗和差别中得到维系并因此总是联系着权力关系。”那么他眼中的权力是什么意思呢?他认为权力是某种场景和型塑,而不是其中的事物或关系。当他说实践包含权力关系、产生权力效果和运用权力时,是说实践以某种方式型塑或限制了特定情境中人的可能行动领域。在实践的权力之网中,各个行动者都会被塑造、改变、镇压或控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实践。
(三)新经验主义路径
新经验主义(New Empiricism)作为建构主义的一种经验主义建构方式,是与新实验主义几乎同时出现的一种科学哲学流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南希·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正如卡尔·霍弗(Carl Hoefer)在介绍卡特赖特的科学哲学时指出的那样,“新经验主义”之所“新”在于它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遵循的不是休谟和卡尔纳普,而是纽拉特和密尔的路径;它关心的不是怀疑主义、还原论或者划界问题,而是实际中的科学如何获得成功,以及为了理解那种成功需要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上的假设;它不排斥形而上学,并主动寻求科学成功的形而上学原因。
卡特赖特在其著作中为人们描绘出了一幅定律拼凑、反基础主义、反普遍主义和坚持多元主义实在论的斑杂的世界图景。
首先,她认为物理定律不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为什么物理定律不具有客观性呢?她认为,这是因为它只对模型为真,而不对世界为真。她将定律划分为:基本物理定律、不太基本的方程式、高层次现象定律、具体因果律或因果原理。在所有层次的定律中,只有因果律和某些现象律可以是真的。在卡特赖特看来,我们对客体的认识过程,即理论对客体的切实反映实际上是一个从基本规律到模型,再从模型到现象规律的过程。现象定律对于客观对象有一个真不真的问题,然而模型只是为了理论的形式美或计算的便利而人为地建构出来的,所以基本定律只对模型的客体为真。为什么自然科学的定律不具有普遍性呢?她认为那只是用“律则机器”(nomological machine)构造出来的,在此范围之外并不适用。有了律则机器,那么就意味着在其他情况均相同时,定律才是真的。然而,卡特赖特认为将律则机器所包括的所有条件拼凑在一起是不容易的,一般只能在实验中才能凑齐。所以,自然科学的基本规律是具有地方性的(主要在实验室范围之内),超过这个界限,基本定律便失去了效力。
其次,卡特赖特反对科学的统一,倡导一种多元主义的科学观。她认为科学中的各个学科本来就是不统一的、不能整合的,这是斑杂破碎世界的一个根本特征,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除了研究对象是同一个物质世界,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之外, 并没有系统、固定的联系。人们为了解决问题的方便而人为地将任何两门科学捆在一起的做法其实是很荒谬的,那个我们所谓的大系统只是一个大的科学谎言而已。
(四)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路径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尤其是后SSK研究更关注科学活动的实践过程和人类学方法,此类经验主义的建构方式,带有典型的建构主义特点。
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强纲领SSK主要注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强调权力和利益等因素在科学知识建构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几乎完全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因而,从整体上来说,强纲领SSK虽然也是科学哲学的经验主义新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极端立场,后来受到共同体内部的检讨和批判,被所谓弱纲领SSK(即后SSK)所修正。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SSK内部通过演变,整体上进入后SSK的研究阶段,呈现出一种多元主义的建构立场。在后SSK 阶段,一方面,“社会的”因素已经没有实质含义和垄断性的解释力,而其他非社会因素却拥有了更大的理论解释空间;另一方面,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转向“科学实践”的分析。后SSK进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科学在行动》和《实践的冲撞》是后SSK的代表性著作。
拉图尓在《科学在行动》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 in making),而不是那种由科学家或哲学家给出的、关于科学包括什么成分的预设定义。在包括资助者、盟友、雇主、信任者、赞助者和顾客等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在内的“技术化科学”之中,每一种要素都是一个行动者,他们形成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就是在由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相互作用的网络中,科学才能得以展开。在这一活动中,任何一方都是行动者(actor)和转移者(mediator),在面对科学决定或科学争端时,都没有优先权。总之,他所说的技术一般是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不仅指涉着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更揭示了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
受拉图尔的影响,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形象。他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的实践冲撞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由隐藏的规律控制,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当中;各种事物并非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因此,我们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进行较量的核心。”皮克林的“实践冲撞”理论摆脱了人与物的二元论思维,强调各种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纠缠,既突显建构主义的特点,又具有典型的后人类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特征。
二、科学哲学经验主义新建构的哲学特质
新实验主义、科学实践解释学、新经验主义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尤其是后SSK),作为科学哲学经验主义新建构的四种路径,有什么共同的哲学特质呢?
(一)时代特质
上述四条路径,名称来源各不相同,具体到某个科学哲学家属于哪个学派或路径,可能会有争议,不同学者的风格和侧重也互相区别。但是,它们都有同样的时代背景和相似的哲学背景。无论从实践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来看,当代科学和技术都已经交织成一种被称为“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的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科学的进步依赖于技术的进步,离不开高精尖的实验仪器设备和现代的组织管理;反之,高科技的实验仪器和设备技术进步,也十分依赖于科学研究的推进。 相应地,包括以上四种路径的科学哲学都蕴含着某种实践转向,即发生着从着眼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着眼于“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转变。这就是科技一体化的时代背景和实践转向的哲学背景。实践转向中的科学哲学强调我们应该研究“实践中的科学”或“行动中的科学”,即“科学实际上是怎么样的”,而不是研究“想象中的科学”,即“科学应该是怎么样的”。它们致力于从哲学上探讨如何在实践中建构相应的科学,于是,建构主义的各个不同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应运而生。
有研究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的科学哲学处于“战国时代”,各种新的哲学思潮不断涌现,正统科学哲学的影响依然存在。面对这样的局面,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不禁要思考:科学哲学目前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以往的科学哲学存在的问题,目前的科学哲学都解决了吗?科学哲学该走向何方? 2001年时吴彤曾写道:“一个有别于以往科学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或历史主义和实在论形态的新的科学哲学形态还没有形成。但是,这个科学哲学的新形态在后现代哲学的演化中多少出现了一些萌芽性、动态性的、不十分确定的变化和发展。”如今看来,一种不同于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建构方式的科学哲学,即我们称之为建构主义的科学哲学其实一直都在发生着,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而已。
进而言之,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新建构作为一种新的建构方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层面有与传统经验主义明显不同的特质。
(二)本体论的特质
与传统经验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是,经验主义的新建构在本体论上反对普遍主义、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
新实验主义者在对“观察或实验渗透理论”加以质疑的同时,隐含着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他们认为:若要判定观察/实验和理论孰先孰后,必须结合具体的科学实践和语境,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新实验主义就必须在基础上是反本质主义的,是语境主义的”。 科学实践解释学的主将劳斯也认为:“普遍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理论偏见的产物,他们在我们的文化中塑造了传统的科学形象”, 但是,“科学的文化研究拒绝承认科学有任何本质或者一个单一的本质目标”。 卡特赖特则对基础主义狠加批判,她说:“有一种倾向认为,所有事实必定属于一个宏大图式;而且,在这一图式中,第一个范畴的事实具有特殊和特权地位。它们是自然应该运作的方式的范例。其他的必须弄得符合它们。我认为,这种基础论教条,正是我们必须反对的”,[18]她呼吁拒绝基础论,认为实在很可能只是定律的拼凑。[19]卡特赖特坚持 “形而上学律则多元论”(metaphysical nomological pluralism),她的教义是: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 of laws),自然界在不同领域中由不同的定律系统(不必以系统的或齐一的方式彼此联系)支配。[20]皮克林在批判传统本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生成本体论,即冲撞本体论或辩证本体论的观点,他认为世界在永无止境地流动与生成,人类置身于其中,但绝不是受控于其中。
总之,经验主义新建构不认可人们是外在于世界进而去表征世界,而是强烈认定人们本身就处在世界之中,与世界不断互动。
(三)认识论的特质
与传统经验主义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是,经验主义的新建构在厘清各种概念与纷争的基础之上,试图在认识论上通过批判性的分析打破因二分所造成的认识壁垒。
新实验主义认为观察/实验与理论二者不是截然对立或分离的,而是不断互动和相互联系的,“有些深奥的实验完全由理论生成。有些伟大的理论来源于前理论的实验。”新实验主义一方面试图调和逻辑实证主义的“观察/实验先于理论”与以汉森为先导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观察/实验负载理论”观点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又以“思辨”、“计算”和“实验”的三分法取代观察/实验与理论的截然二分,企图弥合因二分而造成的界限。
科学知识社会学(尤其后SSK)根本否认自然/社会二分谱系的存在。拉图尔认为:“在科学和技术的实践中,自然和社会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实践就是科学和社会的居所,二者之间的空间在持续地建构、解体和再建构。我们非常自信地赋予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特性,恰恰就是实践过程的结果,而不能视为对实践过程的解释。”[23] 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理论,关注的也是自然、仪器与社会之间机遇性相聚集的空间或场所,即物质-概念-社会的聚集体。
总之,经验主义的新建构在认识论上反对传统的二分,即反对观察/实验与理论,实在论与工具论、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科学与社会、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等二分。建构主义的流行清楚地表明,在当下的科学实践中,试图把理论的、历史的或社会的因素从科学活动中撇除出去,从而得出所谓的纯粹科学真理,再将之运用于解释自然和世界的传统思维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
(四)方法论的特质
与传统经验主义的又一个重大区别是,经验主义的新建构在方法论上反对还原主义,坚持整体主义。
哈金在反对理论实体时曾经对“还原主义”进行批判,他认为:“逻辑实证论者从而兴起了伟大的还原论纲领,他们希望通过逻辑,可以把所有包含理论实体的陈述,都‘还原’为不指称此类实体的陈述。这一计划的失败,甚至比可证实原则的失败还要惨。”劳斯不仅批判了强纲领的SSK的还原主义思维方式,认为其研究视角也是一种还原,它“把科学还原为政治或社会建构,就像把它限制在认识论领域一样错误”;而且在说明科学知识的地方性特质时强调其不可还原性,“科学知识的经验品格是不可还原的经验指涉关系在地方性建构中的产物,而不是对适用于任何地方性情境之抽象的普遍规律的发现”。
卡特赖特也反对还原主义,她认为“现在我自己的研究关注的主要不是经济学或物理学或是其他单一学科,而是关注如何从作为整体的科学知识中得到最多。我们如何最好地把不同领域的不同层面、不同种类的知识放到一起,来解决不属于任何单一理论单一领域的现实世界问题。”[27]正如迈克尔·埃斯菲德(Michael Esfeld)对她的总体评价:卡特赖特以反对基础主义而闻名,基础主义是说自然规律在原则上可以还原为某个物理理论的具体规律或者随附于一套基本定律。在她看来,对自然的描述在原则上是不能还原为一个基础理论的。
后SSK的反还原主义立场和劳斯类似,直接地建立在对强纲领的SSK批评的基础之上。皮克林认为强纲领的SSK内部所展现的物质世界在整体上还保留着还原论的外衣,其学科图景具有典型的还原论特征;后SSK则脱掉了这层外衣,其科学图景也转换为具有整体主义视角的各种异质文化要素相互冲撞的图景。
总之,科学哲学的经验主义新建构具有强调科学的技术化和实践转向的时代特质,反对普遍主义、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的本体论特质,反对传统二分法的认识论特质和反对还原主义的方法论特质。实际上,这些特质是对传统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即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的解构和提升,也是区别于它们的最为明显且最为基本的特征。它代表着对科学的哲学思考总体上进入了皮克林所谓的“后现代”阶段——在科学实践中,对泾渭分明的学科研究中的思维方式、学科界限进行质疑和挑战。[29]
三、经验主义新建构所展开的哲学变革
经验主义的新建构对传统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质疑和挑战引发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使得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成为潮流。首先,变革改变了传统经验主义理论优位的科学观,以实践优位的科学观取而代之;其次,变革使实验活动得以重新定位,实验不再是理论的附属物,也不仅仅起到验证科学理论的作用,实验有了自己的生命;最后,变革使知识的普遍性受到质疑,更多的人接受从本性上来说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知识。
自逻辑经验主义开始,理论优位的科学观长期占据着科学哲学的讲坛,使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跛脚”的科学哲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科学哲学家开始从科学研究的实际状态出发,本着自然主义的原则,反思科学哲学的发展路径。他们质疑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主张从只重视理论却轻视甚至忽略实践的科学观中解放出来,并发展出一种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以回归科学研究的实践本质。
皮克林曾对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评价道,“对于20世纪大多数英美科学哲学来说,他们始终关注的是科学理论、科学事实以及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的关系问题。这一点不仅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主流如此,对于其当代变种也是如此。”[30] 皮克林认为“新的科学图景中的主题是实践而不是知识”[31]。哈金曾经对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质疑道:“科学哲学家们总是讨论理论与实在的表象,但是避而不谈实验、技术或运用知识来改造世界。”因此“自然科学史现在几乎总是被写成理论史。科学哲学已经变成了理论哲学,以至于否认存在先于理论的观察或实验。”劳斯对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更是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如果哲学家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狭隘的思想方面,那么我们很容易忘记科学研究实质上也是一种实践活动。
基于对传统的理论优位科学哲学的批判,哈金、卡特赖特、皮克林、劳斯等最终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一种相似的哲学立场,即主张科学哲学应该实现从理论优位到实践优位的转变。他们认为科学就本性来说是一种实践活动,如劳斯主张 “在认识论和政治上将科学看作是实践技能和行动的领域,而不仅仅只是信念与理性的领域”。科学哲学从理论优位走向实践优位这一论断至少意味着以下三层含义:其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技术手段,科学的技术化与技术的科学化逐渐明朗,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愈加紧密。其二,要更加关注实践中的科学,即科学知识的具体生产过程。这其中既有如强纲领的SSK所分析的社会利益渗透;也有如拉图尔和劳斯所分析的权力建构,由于“在现代社会,大多数新兴权力来自科学(不论是何种科学)”,所以实验室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一个权力场和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第三,研究科学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阐释其对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中重要问题的解决所产生的影响,确保其为居住在杂乱世界中的日常生活提供某种指导。
总之,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总体发展趋势的一种概括。如今它已经发展得非常壮大,并于2006年成立了“实践中的科学哲学协会”(Society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SPSP),其宗旨在于扭转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实践的忽视和科学技术哲学的社会学研究对外部世界不加关注的局面,而要沿着自然主义的路径,通过对具体情景化的科学实践中的实验、模型和测量等的研究,提倡一种基于理论、实践和世界的科学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强调实践优位固然是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对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的一种矫正,但也要防止矫枉过正,以免滑入另一种基础主义。
(二)对实验活动的新定位
罗伯特·阿克曼(Robert Ackermann)在评价20世纪科学哲学时认为,“发展于20世纪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对于观察事实给予了特别重要的基础性强调,把它作为控制理论增长的手段……实证主义对于观察事实来源于实验实践的方法却几乎不关注”。这就是说,在科学实践中,实验本是一个最为基本的科学实践活动,然而,我们对实验本身重要性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逻辑经验主义者把实验活动和结果分离开来,把作为科学知识重要来源的实验降格为证实或者证伪观察陈述的一种毫无疑问的方式。他们只考虑观察,并且假定能分辨出观察语句的真假。然而劳斯等认为,这种假设忽略了实验如何证实或证伪观察陈述的科学实践过程,[39]而“这种忽视必将导致我们对科学中实验的作用,对实验室、诊所或田野所具有的地方性的、物质性环境的意义以及这些环境所要求的技术的和实践的能知(know-how)的误解”。[40]
早在1983年,哈金就批判那种倾心于“理论优位”,而忽视实验独立地位的科学哲学。他认为,科学研究既要重视理论和表象,也要重视实验和干预,“我们表征是为了干预,我们干预也要根据表象。” 他把这种干预概括为仪器的建造、实验的计划、运行和解释,理论的说明以及与实验室部分、出版部门等的谈判。他强调科学技术与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正是在这相互作用中,形成了科学的本真形象。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不是停留于单纯的表象,而是着重于复杂的干预。
新实验主义将科学合理性的来源投射于实验活动。它强调仪器运用、错误排查、样本处理、误差分析等细节的实施使实验得以独立于理论,而且实验可以对理论进行严格的检验。这使实验不再只是对理论问题的尝试性回答,从而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即对理论产生着实际的约束、推进和触发作用,以至于可将科学进步与科学革命解释为实验知识不断累积的结果。
对实验活动的新定位是对科学发展的一种新的解释途径,同时开创了一种科学哲学发展的新可能,如此之哲学变革是对过分强调理论支配的科学观的有益矫正。
(三)知识地方性观点的上位
传统经验主义一般都持有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观,即认为科学知识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对普遍性的科学知识观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使知识地方性观点自此上位。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在不同的哲学语境中,往往有不同的指称,一般来说有三种基本含义,即“殖民化的”(与“西方的”相对应)、“前现代的”(与“现代的”相对应)和“情境化的”(与“普遍性的”相对应)。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主要是第三种含义,意思是说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情境条件, 这些特定情境包括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和由此造成的立场和视域等等。
以哈金、卡特赖特、皮克林和劳斯等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家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知识,普遍性知识只是其转移的结果。
哈金的“实验实在论”是特别强调实验室这一地方环境的,并且要看实验的效果。哈金在著作中多次以电子为例,论证到“如果你能发射它们,那么它们就是实在的”;或者根据电子的各种属性,进而能够成功地制造出新型的仪器,用以干涉自然界中的其他更具假设的自然事物,这也可以说明电子的实在性。同样,卡特赖特之所以反对普遍主义的知识观,就在于她认为我们所获得的知识都是在实验室这一特殊的地方性环境中产生的,一旦脱离了这一环境,便不再为真。而为了使用从实验室中获取的知识或保障其为真,就需要做到其他情况均相同才行。卡特赖特的这种“局域实在论”与哈金的“实验实在论”在某种程度上为“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知识”这一观点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
皮克林的操作性科学世界观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都强调知识的地方性。在这种科学图景和网络中,科学处在各种力量、各种能力、各种具体操作之中,我们使用机器捕获着物质力量,而不同的物质力量和非物质力量的冲撞过程依赖于某些具体的情境和路径,然而,后者在传统经验主义镜像反映式的科学观中被冲刷掉了。因此,皮克林坚决地表示:“我必须指出,在我的分析中不存在任何作用能够删除科学实践的情境与路径依赖,这也正是冲撞不能认同反映论的实在论的基本点。”
劳斯认为:“从根本上说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它体现在实践中,这些实践不能为了运用而被彻底抽象为理论或独立于情景的规则。”他认为,理论知识来源于以技术、实验为代表的实践活动;知识就其本身来说是具体的,依赖于特定情境的,因此,知识在首要的意义上说不是普遍性知识,而是地方性知识。普遍性知识不是科学实践追求的终极目标,只不过是地方性知识从一个地方经过标准化而非去情境化转译到另一个地方的中间环节而已。对具体情境条件的重视,对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之关系的理解,是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的应有之意。
科学哲学的经验主义新建构对传统经验主义一些固有观点和理论所提出的质疑和挑战,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科学哲学的某些偏见,化解了一些已经存在许久的争论。但同时又带来了一些新问题:第一、实践中的科学既然屏弃目的论模式,肯定演化论模式,那么,如何看待科学进步?第二、既然摒弃基础主义方法,肯定整体主义方法,那么,如何看待科学的基础性和本质性?第三、既然否定表征主义科学观,倡导自然主义科学观,那么,如何看待科学的现象和规律?
(一)目的论抑或演化论:如何看科学进步
关于科学进步,目的论和演化论(反目的论)具有不同的立场,前者预设了科学的某种既定目标;后者认为不存在这样的目的,科学的形象和目的是在实践中,与周遭世界的“冲撞”中不断生成的。传统经验主义具有某种目的论倾向,虽然有的比较隐晦。它要么以物理主义或现象主义的语言,追求科学理论与感觉经验的符合,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使理论得到经验的证实,或提高理论的确证度或概率(逻辑经验主义);要么认为科学的发展是朝向某种既定的目标不断逼近的过程,科学的目的在于提高逼真度(批判理性主义)。
对于目的论的科学进化观,库恩曾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进行批判,他认为“科学发展就像达尔文式的进化,它是一个从后面推的过程,而不是朝着某个固定的、它要逼近的目标拉的过程”。
经验主义的新建构也不认同具有目的论倾向的科学观。例如,受生物演化论和实用主义影响颇深的皮克林认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有隐藏的规律控制的,而应该认为世界的确展现为一个以开放式终结方式演化的活生生的场所——一个人与物的力量和操作在真实的时间中绝对地突现的场所,一个物质的、社会的和概念的秩序在我称之为实践的冲撞(力量的舞蹈,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的过程中持续突现的场所。”在皮克林看来,世界或知识体系不是我们预设的那样已经确定,而是不断生成的。以化学为例,他认为如果关注并突出物质性及其流转性的生成过程,我们将会看到化学物质的流动和转变,以及伴随它们的知识在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去中心的过程中涌现并生成的过程。
科学观从目的论到演化论的转变必然导致有关“真理”、“进步”等观念的变化。卡特赖特反对理论陈述背后有一个可供我们认知,但却永远无法达致的客观世界,“理论本身并不包含真理。理论帮助我们思考,但是它只是表象。”[50]哈金之所以不看重理论的真理性,是因为“真理的标准是产生出来的,不是预先存在的。”[51] 然而,劳斯并不完全拒斥进步概念,他认为需把进步置于科学实践当中来考虑,“在我看来,科学进步确实是对原有成功的积累和对过去失败的纠正。但是,如果我们不参照当下的科学实践所追求的目标,包括设备、实践以及必须与前两项一起加以考虑的作用,那么就不存在评价我们积累成功与纠正失败的能力的标准。”[52]“真理”、“进步”等概念往往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先验预设,即我们通过科学实践而形成的科学理论是对外部世界真实的描述。在卡特赖特、哈金和劳斯看来,这是有问题的。因为理论内部并不包含“真理”或“进步”,即便包含,其标准也是通过科学实践而确定的,而不是先验预设的。
看来,没有绝对的进步标准,这一点比较容易接受,但它并非等同于无所谓进步。忽视演化过程,专注于所谓目的,乃是一种独断论的预设论;但是,如果目的是没有的,演化就是一切,那么,这样的科学实践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基础主义抑或整体主义:如何看基础性和本质性
逻辑经验主义声称:每个科学领域的定律与概念都可还原为更为基础的领域,全都安排在犹如一个金字塔般的等级体系之中,其内部按照某种规则有序地排列,最顶端则是物理学。各个学科以还原主义的方法,一级一级地还原,如生物学可以还原为化学,然后化学再还原为物理学,物理学位于科学这个大系统的顶端。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基础主义的知识观表现为还原主义。
然而,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和科学哲学学科范式的转变,科学哲学家们认为基础主义不是科学唯一有效的方法论,相反,他们主张反对基础主义,从而采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卡特赖特以拒绝基础主义而出名,在她看来,自然科学的真实情况根本不是逻辑经验主义宣称的那样,金字塔系统是个大的科学谎言,存在某种基本的自然规律从而可以适用于所有地方和时间的想法,是很荒谬的。
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新建构不仅批判传统科学哲学对基础主义的迷恋,而且批判其自身内部的极端立场,如社会建构主义科学哲学中的还原主义方法论,皮克林对强纲领SSK的批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皮克林批评强纲领SSK所支撑的实践图景具有典型的学科还原特征。强纲领SSK“把科学文化仅仅表征为单一的概念网络,把实践仅仅表征为由利益建构的一个不确定性终结的筑模过程,这类表征不能很好地把握实际的实验室科学所显现出的复杂性说明……把实践描述为不确定的以及利益导向的,最多也就是捕获了问题的表面” [53],因此,强纲领SSK的实践概念是站不住脚的、理想化的和还原性的。经验主义的新建构不仅反对一般知识的还原主义,而且批判强纲领SSK的社会建构主义,这是因为后者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还原,为科学提供一种外在的说明,把真理与谬误、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差异最终归因于同一类社会要素。虽然同属科学知识社会学,但这种还原对于科学哲学的经验主义新建构来说,也是不可取的。
总之,以卡特赖特、皮克林等学者的科学哲学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新建构倾向于完全排斥基础主义,并且否认任何基础性、本质性的概念和方法。他们愿意肯定的唯有整体本身,但接着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这不是把整体本身设定为基础或本质了吗?更不用说,整体本身又是什么呢?这个作为基础和本质的整体人们又如何才能把握呢?
(三)表征主义抑或自然主义:如何看现象和规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科学哲学中兴起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方向。它把科学作为人类文化和人类实践的一种形式,主张“哲学是自然科学的延续”,提倡“在自然和科学的架构内进行哲学探究,使哲学成为科学工作的延续,而不仅仅为了哲学研究的目的给科学增加不必要的形而上学负担”。经验主义的新建构强调实践,批判传统的表征主义科学观,提倡自然主义的科学观。表征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理论是对独立于心灵的世界的描述;而自然主义的科学观则不对任何事物做先验的宣称,主张科学与哲学是在自然与科学范围之内开展的没有明显边界的连续性的研究,也就是说不关注科学知识层面的“what”,而是关注科学实践层面的“how”。
哈金区分了科学的两个目标,即表征(representing)和干预(intervening),哈金强调实验中的“干预”。卡特赖特也是如此,她认为:“我感兴趣的是干预。所以我问不同的问题:世界如何由科学变得像它应该的那样。”皮克林则将表征性语言描述(representational idiom)和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 idiom)进行比较和区分,他认为表征性语言描述是科学为寻求表征自然并产生描摹、映照和反映世界的知识活动,但这种活动使我们陷入科学是否恰当地表征了自然的恐惧之中。为了克服这种恐惧,我们应该超越表征主义的科学观,进而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科学,故而皮克林认为“如果我们要真正把握科学实践,脱离对科学的表征语言描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劳斯试图颠覆有关现象与规律的传统认知,从而否认诉诸观察的决定意义。传统经验主义认为,科学是某种表征体系,其目的在于精确的描述世界,而世界与我们所进行的表象无关。观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连结我们所表象的世界与世界本身之间的唯一通道。只有在感知经验中,世界才作用于我们,因为它限制了表象世界的可能性。在劳斯看来,情况并非如此,“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从关于世界的语言表象出发如何抵达被表象的世界本身。我们已经在实践活动中参与了世界,世界就是我们参与其中的那个东西。通达世界的问题(诉诸于观察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将不复出现。”[58]这就是说,参与的决定性,而不是世界本身及其可观察性决定规律性认知的可能性,这就是行为性判定赋于实践的本体地位。
那么,在走向自然主义科学观的征途中,劳斯和皮克林等是否完全抛弃了表征主义科学观呢?其实,并不是。他们只是不再强调其唯一性和独特性。例如,皮克林认为:“思考科学实践的物质操作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忘记科学的表征性质。科学绝不仅仅是制造各种机器。如果没有科学的观念的和表征的维度,任何人都不能声称能够对科学进行分析”。其中所作的保留是耐人寻味的。
自然主义而非表征主义的倾向至少存在两个理论困境:一是实验不可能完全不依赖理论,新实验主义无法将理论、有时是高层次理论从科学实验中排除;二是无论怎么深入剖析实验的细节,也无法在被实验严格确证的实验定律与超越这些定律的推测之间做出绝对的划分,也难以在所谓得到严格确证的实验定律与高层次理论之间分出泾渭。的确,如果彻底反对表征主义,不再关注现象及其提升为规律的可能性,那么,还会有什么科学认知呢?
结语
近百年来,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经多个阶段。总体而言,我们认为科学哲学演化中的经验主义模式的转换大致为:逻辑主义——历史主义——建构主义。逻辑主义的卓越成就以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为代表,它们通过语言分析确认了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和基础,逻辑是知识的基本架构。历史主义的建构方式,由于库恩和拉卡托斯等学者的工作,后来居上,改变了科学哲学的面貌,人们衷情于通过历史分析来揭示科学理论的演化模式。但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建构方式,并没有穷尽科学哲学的经验主义建构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后,一种新的经验主义的建构方式越来越明显,甚而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我们把这种新的科学哲学潮流称为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从整个科学哲学史的趋向来看,新潮流体现为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运用建构主义的理念和方法,形成新的经验主义的建构方式。
无论是逻辑主义的,还是历史主义的建构方式,可以说都是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它们总体上都是反思性的科学哲学,属于对科学知识在理论上或智识上的事后重构,试图给予科学合理性以某种辩护。与传统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相比,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特别强调“实践”、“干预”、“建构”。经验主义新建构的重点和关键在于“建构”。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关注的焦点不再止于科学知识或科学历史,而是具体的科学实践;科学不再被看成一种完成了的形态,而是永远处于行动中;人不仅是一个思考者(thinker),而且是行动者(doer)。在科学实践中,各种异质性的文化因素(人的、社会的、物质的等)相互作用和纠缠,共同建构着科学。这种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企图扭转对科学理论的过分关注,并通过科学实践来呈现一种非表征主义的、完整的、真实的科学图景。
“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表明:以逻辑主义——历史主义——建构主义这一线索来观照科学哲学近现代演化史,有助于清晰明了地概括科学哲学发展的脉络和内在逻辑,显示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断裂和继承;亦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科学哲学“战国时代”多种路径间的关系,进而从宏观上把握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的总体趋势。当然,“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突出下述观点:从理论优位到实践优位,科学实验有其自己的生命,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的确是对传统科学哲学主张理论优位,强调科学实验的工具性作用,倡导普遍主义知识观的一种矫正。
“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的提出,是在逻辑主义-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建构方式的基础上,对当代科学哲学的演变进行宏观思考而自觉形成的一种认知理路,但并不意味着它是诠释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唯一视角。其实,从实在论、实证论、实用论的视角,从预设主义、自然主义的视角,也都可以去尝试把握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脉络。况且,“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与实在论的、自然主义的各种视角并不是截然分割的,而是相互交叉的。只是,“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与逻辑主义的、历史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具有比较自然的现实与逻辑联系。
对科学哲学的经验主义新建构所带来的问题,本文既不可能穷尽,也没有对所提到的问题给出确切的解决方案。但能肯定,在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中,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经典问题仍然将成为讨论的对象。随着新技术和新思想的不断涌现,科学边界将继续扩展,分支科学的研究也将愈益深入,科学哲学或将呈现经典与前沿并重,微观与宏观并蓄,辩护与批判兼顾的某种审度性的发展态势。但愿这一态势将不仅引导人们更好地发展科学,而且引导科学更好地造福于人们的生活世界。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6(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科学哲学史研究”(12&ZD116)和“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阶段性成果。
“经验主义新建构”,是对建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建构方式的概括。之所以“新”,是针对人们熟悉的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建构方式而言。这种“新建构”,自然不止文中所述这四条路径,但我们主要论述这四条路径,有以下一些原因:第一,在目前的科学技术哲学界,它们受到的关注比较多。从其著作的翻译和引介,到对它们思想的研究(如吴彤、王巍、张华夏、盛晓明、成素梅等人工作),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学术背景和论域,为进一步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把握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研究素材。第二,在目前的科学哲学或科学研究视野中,虽然还存在着其他的研究路径,如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学术思潮,它们也是建构主义的,但我们认为它们所体现的更多是一种对科学的文化分析,而非对科学的哲学分析,所以本文中没有论及。
[②] 参见汉斯·拉德主编:《科学实验哲学》,吴彤、何华青、崔波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
伊恩·哈金:《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王巍、孟强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参见Deborah G. Mayo, “The New Experimentalism, Topical Hypotheses, and Learning from Error”, 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Vol.1994, Volume One: Contributed Papers (1994), p.273.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慧、孟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8页。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第74页。
约瑟夫·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戴建平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3-124页。
参见Carl Hoefer, “Introducing Nancy Cartwright’s Philoophy of Science”, in Stepham Hartmann, Carl Hoefer and Luc Bovens, ed., Nancy Cartwright’s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1-2.
关于皮克林的科学哲学,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其前期思想是属于SSK领域,以《构建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为代表;后期思想属后SSK,以《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为代表。这里着重讨论他的后期思想。
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第7页。
参见Mieke Boon, “Instru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an Kyrre Berg Olsen, Stig Andur Pedersen and Vincent F. Hendricks, ed.,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Hobok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9, p.78.
参见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24页;吴彤等:《复归科学实践——一种科学哲学的新反思》,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吴彤:《回顾与前瞻:科学前沿革命与科学哲学发展》,吴倬编:《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清华人文社科学者展望21世纪》,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397页。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第116页。
约瑟夫·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第223页。
[18] 南希·卡特赖特:《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王巍、王娜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19] 参见南希·卡特赖特:《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第40页。
[20] 南希·卡特赖特:《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第36页。
参见郝新鸿:《走向辨证的新本体轮——访问安德鲁·皮克林教授》,《哲学动态》2011年第11期。
伊恩·哈金:《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第128页。
[23] 安德鲁·皮克林:《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安德鲁·皮克林编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文、伊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伊恩·哈金:《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第40页。
约瑟夫·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第80页。
[27] 南希·卡特赖特:《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第20页。
参见Michael Esfeld, “Cartwright on Wholism”, in Stepham Hartmann, Carl Hoefer and Luc Bovens, ed., Nancy Cartwright’s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324.
[29] 参见安德鲁·皮克林:《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第6-7页。
[30] 安德鲁·皮克林:《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第3页。
[31] 安德鲁·皮克林:《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第13页。
伊恩·哈金:《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第121页。
伊恩·哈金:《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第121页。
Robert Ackermann, “The New Experimentalism” (Review), The Neglect of Experiment by Allan Franklin,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40, No. 2, 1989, p.185.
[39] W·H·牛顿-史密斯编:《科学哲学指南》,成素梅、殷杰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
[40]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序言”,第Ⅵ页。
伊恩·哈金:《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第25页。
local在不同的语境中,常常被翻译为“地方性的”、“本土性的”和“局域性的”等。
参见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
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第219-220页。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第113页。
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中文版序言”,第2-3页。o뿺现鉞ꁬ곈뿺㤘莝煪鉞籘ꁬ곘뿺㙙鉝ꁬ곈뿺籘侠鉝ꁬꁬ㔮鉝ᖀ﷽﷽﷽﷽﷽﷽﷽﷽﷽﷽﷽﷽﷽﷽煪鉞ꁬ괨뿺곬뿺ᧈ籅ᨈ﷽﷽﷽﷽﷽﷽﷽﷽
参见郝新鸿:《走向辨证的新本体轮——访问安德鲁·皮克林教授》,《哲学动态》2011年第11期。
[50] 伊恩·哈金:《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第174页。
[51] 伊恩·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安德鲁·皮克林编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文、伊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52]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第161页。
[53] 安德鲁·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5页。
段伟文:《可接受的科学:当代科学基础的反思》,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Nancy Cartwright, The Dappled World: A Study of the Boundaries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
中译本中的“representional”是错误的(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第5页),应为“representational”。
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第6页。
[58]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第152页。
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