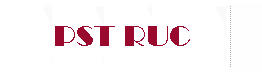——从比较的观点看
摘要:在与唯物史观、福柯、利奥塔、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比较中,分析了约瑟夫.劳斯科学实践哲学的主要理论创新,并在科学哲学史广阔背景中对其进行了理论定位。在科学实践观、实验室研究以及科学叙事论方面,劳斯均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但总体上创新性不够。劳斯的科学哲学属于当代美国的另类科学哲学,属于从分析哲学中杀出的“叛逆”。
关键词:约瑟夫.劳斯,科学实践哲学,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近年来,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的理论引起了中国学人的注意,被称为科学实践哲学。[1]劳斯思想主要包含在3本著作《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1987)[2]、《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1996)[3]和《科学实践如何重要:重提哲学的自然主义》(2006)[4]中,它们分别提出了所谓的“科学的政治哲学”、“科学的文化研究”、“哲学的自然主义”三种科学哲学研究方案。这三本书以不同的方式强调:应该把科学当作实践活动来理解。这个观点究竟意味着什么?上述三种研究方案对此进行了形上层面的说明。比如《知识与权力》指出,视科学为实践即意味着“科学之于文化和政治的不可或缺性以及政治问题之于科学的核心地位,远远超出了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所认可的程度”[5]中文版前言,1,因而科学的政治哲学不可忽视。
应该说,《知识与权力》作为劳斯成名作原创性最强,而后两本书主要是对该书主题的重复或回应,影响远远不及前者。《知识与权力》受到了福柯知识-权力理论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福柯理论向自然科学领域的全面移植。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语境中,将科学视为实践活动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那么,劳斯科学论主要的亮点、突破和价值究竟何在?在科学哲学史流变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本文试析之。
一、劳斯科学实践观的创新
劳斯指出,“我强调的是科学研究是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不仅重新描绘了世界,也重构了世界”[6]117。他并不否认科学是一种表象世界的理论,但更重视审视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何为实践?劳斯认为:“实践不仅仅是行动者的活动,而且是世界的重组,其中这些活动有意义。”[6]122“把实践设想为有意义的情境或世界的重组”[6]27。显然,劳斯的实践不是纯粹的物质性改造世界的活动,而是把主体的意义建构活动亦包含着其中。进一步地,他将其实践观展开为10个基本论点。[6]123-124概括地说,实践具有过程性(实践是一个过程)、连续性(实践往复不断)、相对性(实践模式不固定)、权力性(实践总是包含权力关系)、构成性(实践被不断建构)、动态性(实践不断在变化)、反主体性(实践塑造主体而不是相反)、情境性(实践在具体情境中展开)、普遍性(实践囊括物质实践、话语实践)和开放性(实践是自发开放的)。劳斯实践概念是话语实践、非话语实践的总和,既涉及意义,又涉及自然,这明显受到话语理论的影响。劳斯实践概念强调联系背后的模式或构造及其流变,则后结构主义色彩明显。劳斯的实践概念反对主体的至高位置,与后现代主义的趣味相通。劳斯实践概念突出权力关系,则与他对福柯知识-权力理论的接受有关。总之,劳斯的实践观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即坚持反主体、反表象、反本质、反真理、解构主义等立场。
唯物史观认为,实践是人们的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有意识的活动。与之相比,劳斯的实践观有些类似的立场,比如科学实践普遍联系性即科学实践只有在更广泛地人类实践活动中才能理解,科学实践目标即科学实践活动改变世界和人类,包括思考自然界的方式和人自身。但是,劳斯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首先,劳斯强调实践中意义、话语的地位,将其置于与物质生产活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反对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到基本原理。对此,他直接宣布:“我的观点不是唯物主义,因为唯物主义或者简单地用物质效果来辨别或解释新概念和新理论,或者认为它们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上层思想建筑。”[5]2其次,劳斯强调实践先于主体、高于主体和塑成主体,不是主体掌握实践而是相反,否认唯物史观主张的主体能动性的观点。
劳斯科学实践观的创新不限于实践概念,更重要的应该在于它所蕴含的科学哲学新进路或新理念。首先,不是强调科学在实践中的应用,不能把科学的实践意涵局限在科学应用于技术的方向上,而是强调实践技能和操作对于科学的决定性意义,强调实验室活动在科学实践中的核心位置。科学是实践和行动的领域,而不仅仅是信念和理性的领域。其次,应该从认知主体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日常实践的角度来分析科学,而不是从追问主体何以趋向于客观和真理。因此,以知识归因为中心任务的知识论必须转向社会情境分析,研究科学如何在实际情境中发生,研究科学实践的日常模式,在持续不断地运动、运用或活动中理解科学。第三,应该抛弃主体本位、表象主义的科学论,把知识的权力研究作为科学论的中心问题,尤其是科学实践中权力模式如何改造主体的问题。正是在科学实践中,权力关系得以发展和运作,因而权力是内在于自然科学,权力效应并不止于科学或科学家对政治的影响。科学实践是权力关系和权力运作的当然场所。最后,科学论要实现理论优位(theory governed)转向实践优位,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一致性理解转向地方性、异质性理解,把理解实验与实验室活动作为最重要的研究任务。从表面上看,科学论的理论优位是对科学中理论性因素优先位置的强调。从本质上看,理论优位指的是传统科学论总是试图获致某种对科学的总体化理解。科学论从理论优位转向实践优位,意味着抛弃对科学的总体化理解。与理论优位相反,实践优位强调经验、日常实践性介入、具体实践模式、社会情境、非观念的物质性或操作性因素(如仪器、操作或现象)在科学实践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实践优位从具体社会情境理解科学知识,意味着反对把科学知识看作普遍性、一致性的客观真理。
总的来说,劳斯科学哲学新进路最大的亮点——亦是实质性主张——在于主张在新的科学实践观念下把科学的实验室研究和权力模式研究作为研究的中心内容。实际上,他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全新的实验室权力模式研究理论,即以知识/权力关系为中心的实验室研究。劳斯指出,对知识、权力两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把握,传统理论是有问题的,必须要引入新的替代观点,以理解知识/权力领域被传统研究忽略或误导的某些重要方面。[7]但是,他实际上对两个概念并未提出太多创见,而是基本上接受了福柯的立场,即强调反主体主义、反表象主义、历史性、话语性、情境性。尤其是,他接受了福柯的权力内在主义(权力关系是内在于知识实践的)、权力建设性(权力对知识有建设性效果)和微观分析(重要的是对知识-权力的建构活动进行微观研究)的标志性观点。在他看来,权力外在于知识的观点是基于表象主义知识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持此观点的典型。因此,劳斯新科学哲学最大创见不在基本观念,而在于提出的新任务。与福柯相比,他将知识与权力关系分析引入到科学实践最核心的场所即实验室,开辟了福柯忽略的新研究对象。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相比,他把实验室研究集中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分析上,而不是对围绕着社会利益的诸多社会学维度的全面研究。
二、劳斯实验室研究的创新
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固然在知识观、权力观方面创新颇巨,但他应用基本理论对监狱、疯人院、医院等场所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运转机制所进行的具体分析同样非常精彩。在《规训与惩罚中》,他从源自于边沁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意象出发,对现代监狱中以规训技术为核心的知识-权力模式及其扩散进行了经验性的研究。[8]在监狱中,规训技术对人的改造主要通过三种手段来实现: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两者在检查活动中的结合。由于规训技术在培养驯服臣民方面效果显著,因而在19世纪中期广泛扩散到包括孤儿院、工人住宅区、集体宿舍、学校、收容所、救济院等社会机构中,整个社会最终变成了某种规训社会或监狱社会。
劳斯的实验室研究效仿福柯的监狱研究,试图把知识-权力分析理论移植到实验室中,形成所谓的“实验室微观社会学”。实验室微观社会学面向问题本身,而不同于劳斯所做过的大量的哲学史研究,是其理论中最具启发性的内容。劳斯理解的实验室权力运作可以大致分为三方面的内容:对自然环境的监控、对主体的规训和对社会情境的重组。
1.现象建构的权力策略
劳斯认为,实验室不仅仅是科学家操作的空间,本质上是建构“现象之微观世界”的场所。[5]106“现象之微观世界”是科学家建构出来的与理论模型对应的隔离系统。劳斯用微观世界概念来替代传统所指称的研究对象,主要想强调:微观世界并非本真的自然系统,而是人为建构的产物;它服从理论,在科学家的操纵之下。因此,对实验室内部研究要重点考察科学家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建构微观世界的。
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建构微观世界的目的是操纵它。这种建有实验室实践有三个本质特征:隔离、介入和追踪。所谓隔离,是指实验室研究的是从因果关系上被隔离的建构系统,科学研究不考虑隔离系统之外的环境。所谓介入,是指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必须要影响对象、与对象互动中,才能创造新的研究领域。所谓追踪是指,科学家在实验室中不仅观察对象,还要实施对更有力的监控。显然,微观世界的建构并不是传统观念认为的客观中立的活动。
劳斯认为,上述建构活动实际是权力运作活动,包含着某种权力策略。自然科学实践区别于人文社会科学实践,关键在于实验室实践中采取的不一样的权力策略。为微观世界的建构服务,实验室权力策略运用诸多权力技术,类似于福柯在监狱机制中发现的监视、审判、检查等权力技术。并且,实验室权力策略对于自然科学尤其是科学知识的增长至关重要。
2.主体规训的权力策略
简单地说,规训就是知识-权力运用技术手段对人的行为和肉体进行社会改造。劳斯认为,实验室无疑是一种福柯式的规训机构。实验室为什么要规训主体?他给出了三个原因:第一,实验室若不强制规训,那么实验室的运作及其扩展是不可想象的;第二,实验室建构微观世界本身就是对世界进行操纵、控制的典范,延伸到规训实践主体顺理成章;第三,实验室规训与福柯所指的规训一样,均指向通过改造主体以提高社会生产力。
为了具体分析实验室规训主体的权力策略,劳斯将实验室与福柯的监狱进行类比。他发现福柯在监狱中发现的规训技术在实验室中基本都能以不同的形式被发现。因此,他对实验室规训技术的研究主要是移植福柯,并没有提出新的策略,主要包括的权力技术有:监视、测验(检查、考评等)、书写(档案、记录、汇编等)、空间组织(隔离、划分等)、符号生产、标准化等。[5]235-239另外,劳斯与福柯一样认为,实验室的知识-权力规训伴随着如影随形的反抗,并且反抗让规训得以持续进行下去。
3.实践模式的外部扩散
实验室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实验室实践模式必然要向外扩散。传统观点认为,这种扩散实质上是科学知识的应用问题。劳斯反对这种观点。在他看来,第一,实验室实践模式扩散本质上是知识-权力模式扩散;第二,就科学知识扩散而言,其本质不是应用问题,而是从一种地方性情境到另一种地方性情境的适应过程。
实验室实践知识-权力模式向外扩散最直接的是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设备向外部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实验室特殊情境(以可计算性、构成性、控制性为特征)、操作方法、观念理念、社会关系等经过转译而不畅程度地向外扩散,对整个社会实践尤其是权力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劳斯指出,“实验室可以被看作福柯的权力之微观物理学的活动场所,这种权力最终改变了周围社会世界的面貌。”[5]129-130这种扩散运动是互动的,从其他规训机构中实验室亦学习了许多东西。因此,实验室属于现代社会知识-权力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社会个体的历史处境具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实验室实践向外扩散在一定程度重构社会情境,主要是从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增强技术系统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耦合关系,二是简化自然重组环境的复杂性,使之适应于科学实践。劳斯甚至暗示,在比较弱的意义上,类似福柯所谓的监狱社会的“实验人”(laboratory people)组成“实验室社会”也并非完全是凭空捏造,但他同样对此是坚决反对的。[5]210
劳斯将把实验室中获得的科学知识向实验之外的扩散过程视为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转变为另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过程。传统观点认为,科学知识在实验室之外的扩展,经过了去情境化成为普遍性知识,不仅适用于某个实验室,而是普遍适用。而劳斯看来,科学知识扩散并未走地方性到普遍化的路线。他认为:“地方性的实验室是科学的经验特征得以建构的地方,而这样的建构是通过实验人员的地方性、实践性的能知来实现的。实验室里产生的知识被拓展到实验室之外,这不是通过对普遍规律(在其他地方可以例证化)的概括,而是通过把处于地方性情境的实践适用到新的地方性情境来实现的。”[5]129-130因而,对科学实践的社会情境分析彻底将自然科学知识看作地方性的,并非普遍性的客观真理。劳斯认为,通过“转译”(translation),在实验室获得的地方性知识实现向外扩散从而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经过了转译,科学知识并未真正去情境化,而只是经过了标准化的过程,仍然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是经过标准化它可以适用于新的社会情境。
三、劳斯科学叙事论的创新
在《涉入科学》中,劳斯提出科学的文化研究。对科学进行文化研究,关键是把科学理解为叙事重建,从而实现科学论从传统的合法化方案建构转向跨学科的叙事重建。文化是一个囊括物质、精神和制度的非常宽泛的继承性概念。因此,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审视科学实践,可以很好地理解科学联合体的异质性、话语性和动态性。这应该是劳斯力主科学的文化研究的重要原因。总的来说,劳斯对合法化方案的反对,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劳斯认为,包括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学派、历史理性主义、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在内的所有科学哲学流派均认为,科学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固有部分,因而它们对科学的理解均坚持两个基本立场:建构科学的合法化方案,科学知识的表象主义理解。“合法性方案以如下信念为标志:科学的认识论立场和文化权威需要普遍性的变化,能提供这种辩护(或者表明其不可能性)的东西要肯定科学本身的普遍性目标,或者科学作为实践或成就的一般性本质。”[9]396显然,合法性方案坚持对科学的总体主义、基础主义理解。劳斯对此持反对立场——“首要的是,我反对对理性、指涉效果或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社会生产的总体性合法化或批判”[9]396。按照他的理解,既然科学实践是地方性,那么无论哪一种合法性方案,只要是总体性的科学论均有问题。
劳斯反对建构科学合法性方案,是因为科学实践活动的非总体化特征:异质性、动态性和斗争性。首先,科学陈述、科学实验和科学模型等在孤立的状态下没有知识意义,必须在与其他实践活动的关系中获得知识意义,对知识的理解要从知识联合体(epistemic alignments)的背景中来理解。“塑造知识的联合体包括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他们可能会使用、扩展、挑战或忽略某个人的工作,也包括与这一研究中遇到的对象和材料之间的关系”[6]171。因此,知识联合体比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要宽泛和异质的多,不仅涉及科学界的人际互动,还涉及与科学实践相关物质性的、理论性因素。其次,科学知识是科学再生产活动的要素。只有在不断的循环、应用和发展之中,科学知识在持续的科学实践才成其为知识。最后,在科学知识的再生产活动中,不同知识之间、知识与环境之间相互冲突和斗争,这对于科学实践尤其重要。正是这些冲突和斗争给科学知识再生产提供了新的机会,知识在对抗中扩展,而在和平中衰退。因此,建构抽象的科学总体化方案是无益的,重要的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考察科学实践。
劳斯主张,新的科学论应该从建构合法性方案转到自然科学的叙事重构上来。实践是世界重构,既包括非话语实践,亦包括话语实践。科学实践是一种叙事重构,叙事应该在其中占据更基本的位置。新的科学论要从叙事角度理解自然科学,通过重构叙事来把握科学实践。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的,科学叙事也是异质性的,因此,劳斯反对总体性的、以真理为名义的宏大科学叙事。传统知识论目标是建构合法性方案,正是一种宏大叙事。科学的叙事重建要抛弃宏大叙事的传统套路,强调叙事重建属于科学实践的一部分。科学实践中的叙事重建不需要总体性、普遍性论证,而是在同一情境中存在诸多差异明显的叙事版本,并且科学叙事不断在变化、增生和斗争,保持着活力状态。在科学叙事领域,存在着不断的权力斗争,因此存在着不断的重构。
显然,劳斯的上述观点与利奥塔反对大叙事、“误构”(paralogism)合法化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利奥塔认为,当代科学出现了新的趋势,可以称之为“后现代科学”。[10]116-126后现代科学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科学、知识的观念,而且包含了新的合法化模式即“误构”。利奥塔没有直接定义“误构”,而是用比较的方法进行了分析:误构不是大叙事,而是小叙事;误构不是人们的共识,而是包容歧义、歧见;误构不是效能的革新,误构不再寻找元规则。因此,误构合法化有如下特征:承认语言游戏的异质性,相互不可比较;即使承认有共识,也是局部的,可以被推翻的;所有的论证都是受到时空限制的,临时的合法化取代了永久的合法化。
四、从科学哲学史看劳斯的科学哲学
劳斯出身于美国分析哲学传统,对于分析哲学尤其是当代最新发展非常精通,但主借鉴欧陆资源,打破英美与欧陆的哲学隔膜。劳斯认为,20世纪科学哲学分裂成了分析传统与批判传统两大阵营。在英美分析传统中,哲学家们热衷于为科学制定明确的认识目标、方法及其推论形式。而在欧陆批判传统中,哲学家们往往否定自然科学的完美,考虑到了科学与其他社会兴趣和实践的联系。两种传统各有长短,又相互轻视,直至今日缺乏足够的沟通和互动。劳斯主张将两者传统调和起来,英美分析传统应该借鉴欧陆理论资源,并将自己的理论定位为“欧洲意义上的批判主义”[5]序言,III。在理论建构中,他大量海德格尔、福柯、狄尔泰等欧洲哲学家的思想,并试图将它们与分析哲学结合起来。总之,这种重视欧洲思想的立场在美国分析哲学家中是很难得的,可以和罗蒂相媲美。
劳斯的科学哲学具有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美国分析哲学的一般特征,并且表现出非常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比如,在真理问题上,他主张“真理紧缩论”,把真理视为没有意义的谓词。“对一个概念的紧缩理解指的是,认为这个概念没有充分的理论完整性或前理论统一体,来支持将其实例进行实体性的普遍化。因此,一个紧缩式的说明意味着,‘知识’是一个有用的、科学的术语,但它只划分了一个名义上的类。”[6]165真理紧缩论并不是认为“真”是某种性质,断言“真”既没有载体,也不描述命题。“理解我们以及他人接受了什么,要求与世界及关于什么是真的之间进行不断的互动。”[6]200因此,在劳斯看来,真理是在理解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涌现的,由实践检验、为实践服务。再比如劳斯提出的哲学自然主义。他认为,自然主义哲学家(如杜威、罗蒂、奎因)以及戴维森批判认识论中的先验规范性,反对脱离实践的基础主义,但是他们的问题是把自然视为完全与主体无关的客观主义立场,因此哲学自然主义试图主张一种更为综合的立场:一方面,反对超越于科学实践之上的哲学基础,反对把专断的先验规范性强加于科学实践之上;另一方面,既然只能在科学实践之中发生对自然的因果互动,因而不存在无规范、与主体无关的自然。[4]11-12显然,哲学自然主义继承了实用主义传统,并试图用科学实践的观念从根本上解构先验-经验、自然-文化两组经典二元对立,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从某个侧面,劳斯思想可以视为美国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互融合之后的产物,这一点亦与罗蒂思想类似。
从科学哲学的流派来看,劳斯当属于美国的另类科学哲学家。大致来说,另类科学哲学主要分为三类: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比如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杀出,之后走到逻辑实证主义反面的“叛逆”,比如费耶阿本德、罗蒂等;3)借鉴另类思想的SSK、后SSK以及激进的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后殖民地主义科学哲学。[11]25-26另类科学哲学思潮并非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对科学的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其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以及对科学技术价值的强烈质疑。劳斯属于另类科学哲学的第二类即分析哲学的叛逆。与罗蒂一样,虽然劳斯使用的概念、术语以及论题很多都是分析哲学式的。但是,他得到的结论却是反经典科学哲学的。
总体上说,劳斯科学论的重要理论创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哲学史研究方面,以自己的立场对海德格尔、库恩、戴维森、法因等人进行某些创新性的解读。但是,他并未专门做某个人物或流派的深入研究,因而其哲学史研究虽有一些创见,总体上仍然较之专门家尚有所欠缺。他从哲学史研究中提出“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起码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相比较并不深刻。二是把前辈主要是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移植到自然科学中,形成了一种以知识的权力分析为核心的实验室研究理论。从根本上说,劳斯“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之所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实践研究,正在于他以此引出对实验室的福柯式知识-权力分析进路,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引出的是对科学技术异化和意识形态批判。
相比较而言,劳斯的第二点创新性更加明显,但是他主要是模仿福柯的理论于实验室环境中。福柯对知识的权力研究重点不在数学和自然科学,尤其忽视物理、化学等经典自然科学。劳斯的科学的政治哲学继承了福柯对于知识、权力的基本立场,将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与SSK所主张的实验室研究统合起来,将福柯的知识-权力分析方法用于劳斯自然科学实践尤其是实验室研究中,得出了与福柯监狱研究类似的结论。但是,福柯的思想对劳斯产生来极大地束缚,限制了他的创新性。在福柯知识-权力理论中,标志性的意象场所是监狱和精神病院,其中的知识-权力运行机制后来扩散到社会使之成为某种程度的监狱社会;在劳斯的理论中,标志性的意象场所是实验室,其中的知识-权力运行机制后来扩散到社会使之成为某种程度的实验室社会。当然,对于实验室社会,劳斯的论述远不如福柯对监狱社会的论述。可以说,劳斯基本是将福柯分析的监狱中知识-权力机制移植到实验室中,创新性不够。
除此之外,劳斯从“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引申出“科学实践是从地方性到另一种地方性”的观点,亦是其理论相对于科学论的一个亮点。地方性知识的观念并非劳斯首创,但斩金截铁地运用于自然科学,劳斯应该是最为突出的一位。
客观地说,类似于SSK将知识社会学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劳斯试图将福柯知识-权力理论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确二者在理论适用域上都有从人文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扩展这一突破。但是,SSK不止于提出认识论层面的形上理论,而是获得了大量的更为实证层面具体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在细致的实验室研究方面。而劳斯的研究始终停留于哲学史、认识论这样的形上层面,并未获得将其所谓科学实践理论真正付诸于某个或某类的实验室研究中。较之福柯,当然福柯的知识-权力的基础理论很重要,但他运用该理论对监狱、精神病院、性经验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的具体的、细节的研究非常丰富,构成了其知识-权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更重要的部分。换言之,重要的是不仅提出类似科学的政治哲学的纯理论,劳斯需要继续将它运用于具体科学实践的研究中。遗憾的是,在《知识与权力》之后,劳斯接下来的两本书不过是从其他角度重复该书的主题,并且研究的深度还远不如《知识与权力》。
参考文献
[1] 吴彤: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科学实践——兼评劳斯等人的科学实践观[J]. 哲学研究, 2006(6):85-91.
[2] Rouse J. Knowledge and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M].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Rouse J. Engaging Science: How to Understand Its Practices Philosophically[M].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Rouse J. How Scientific Practices Matter: Reclaiming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5] 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 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7] Rouse J. The Dynamics of Power and Knowledge in Science[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1, 88(11):658-665.
[8]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 北京:三联书店,2003.
[9] Rouse J. Engaging Science through Culture Studies[J]. Proceeding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1994, 1994(2):396-401.
[10] 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 北京:三联书店, 1999.
[11] 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On Theoretic Innovation of Joseph Rouse’s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LIU Yong-mou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Comparing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ichel Foucault, Jean-Francois Lyotard and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paper analyzes main theoretic innovation of Joseph Rouse’s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locates its position in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Joseph Rouse gets some innovations in his view of science practice, lab research and theory of science narration, but needs more innovations. His theory belongs to contemporary alternative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icularly rebel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Key words: Joseph Rouse, practi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oretic innovation